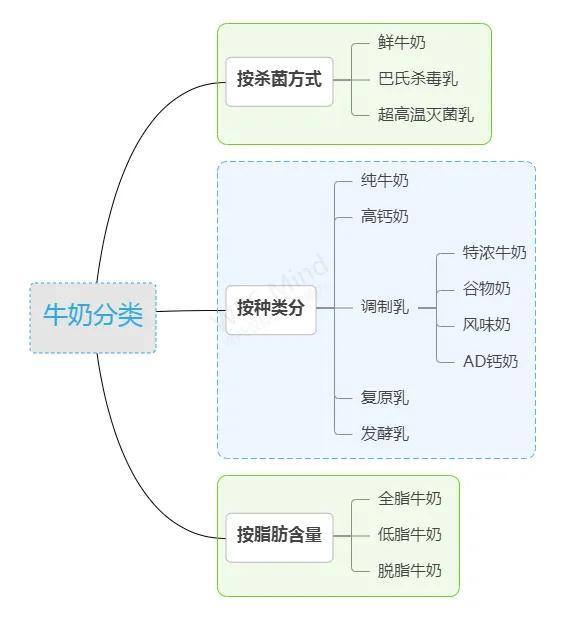聚落考古学的历程(传世文本与理论思考)
1月20日,由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民族博物馆协办的“出土文献、传世文本与理论思考——第三届幽州学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日本明治大学、东京大学、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局、中国文联、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美术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湖北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共聚一堂,以“幽州学”的过去、现状与未来这一议题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交流。由于篇幅有限,本文择取会场若干精彩片段略作介绍,以飨读者。

与会学者在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前合影
气贺泽保规&吴梦麟:“幽州学”的独特性与房山石经的拓印流传
在会议开幕式上,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致开幕词,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研究员应邀作特别演讲。两位学者从幽州地区的重要性和石刻的史料学角度分别对“幽州学”的内涵进行了阐释。
气贺泽教授长期探研魏晋隋唐时代的政治、社会与文化问题。他在开幕词中强调,本次会议是“幽州学”系列学术会议的第三届研讨会,前两届已于2015年、2016年在清华大学召开。相比前两届会议,本次会议参加人数更多,标志着“幽州学”的概念开始逐步形成。他认为,幽州地区在隋唐史研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影响唐王朝的重大历史事件——安史之乱(755—763)开始的地方。同时,幽州地区也是隋唐两京(长安、洛阳)与东北地区人员往来和物资交换的重要通道。
最近一段时期,中国的地方史研究悄然兴起,蔚为大观。但气贺泽教授指出,“幽州学”并不是简单的地方史研究。因为幽州不仅在隋唐时期占有重要的地位,同时“幽州学”研究又是一种长时段的研究,上溯魏晋,中经隋唐五代,下至辽金,其丰富内涵和重要意义并非简单的地方史研究所能容纳。
八十岁高龄的吴梦麟研究员在特别演讲中说,自己参加本次会议的主要目的,就是“看望老朋友、结识新朋友”。1956-1958年,中国佛教协会报请国务院对房山石经进行了发掘拓印,期间开启了石经山上的9个洞,对云居寺地穴中10082件石刻进行了捶拓。现全国总共有7套完整的房山石经拓片,每套3万多张,分别藏于中国佛教协会(2份)、北京图书馆(今中国国家图书馆前身,1份)、吉林大学(1份)、上海版本图书馆(1份)、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份)、北京市文物研究所(1份)。据参加拓印工作的王炳章先生讲述,当时为了拓印房山石经,曾把南京和北京两支拓工队伍集聚于云居寺。两支拓工队伍均为一时之选,技艺颇为精湛,因此7套拓片的质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
房山石经拓印完成后,除第5洞(即雷音洞)面向公众开放外,其余洞窟均用石门封闭。其中第1洞和第2洞的石门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被滚落的山石损毁,当时吴梦麟还下到洞窟中进行了观察。由于目前房山石经的研究只能依赖于拓片进行,因此拓片的整理研究工作显得十分重要。在中国文联张永强先生的协助下,吴梦麟向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申请了项目,拟对房山石经拓片目录予以重新编排,补充此前遗漏以及近些年新发现的拓片。由于当时的拓印工作由中国佛教协会与北京图书馆合作完成,因此拓片的分类是按照佛经经卷的次序进行编排的。吴梦麟认为,房山石经的发现与拓印本身就是在考古勘探、捶拓方法的指引下完成的,因此拓片目录的编排应当采用考古学的方式,以洞窟编号为序。新编排的拓片目录预计2018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房山石经虽然早在1961年就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在管理上仍属于房山区管辖。这种管理体制上的弊端给房山石经的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此外,新近发现的墓志等考古材料往往不能及时发表,供社会研究,给房山石经和“幽州学”的研究造成了困扰。吴梦麟认为,开创新事业需要有更多年轻人的参与,呼吁大家参与到保护石刻的行列中来,并且倡议考古学界应当及时整理和公布考古发掘材料。

80岁高龄的吴梦麟研究员亲自讲解文物
夏炎:“幽州学”是中古家族史“地方性”范式重建的入口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夏炎教授表示,他目前正在从事家族史的研究,幽州边郡的家族恰可作为此研究的开端,逐步切入内地。目前中古家族史的研究基本采取以地方家族为个案的方式,涉及唐以前幽州地区的研究较为稀少,主要原因还是材料太少。但“幽州”作为一个概念,早在汉代就已出现,并且作为一个边郡地带,持续影响着帝国的历史走向。因此,幽州地区的发展史可以说就是一部辽以前中国东北地区的发展史。
幽州地区是游牧农耕交界的地带,这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军事斗争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幽州学”的“幽州”,并不仅仅只是指今天的北京,而是包含河北北部、延伸至辽东的一个大概念。从时间段上讲,幽州地区的家族史研究应当从汉代开始,下延至辽代。特别是汉武帝在辽东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后,幽州与东北亚又有了关联,“幽州学”的研究也应当涉及东北亚政治地缘格局的相关议题。在夏炎看来,“幽州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它涉及不同的历史断代和原本相异的领域,需要学者们联合通力研究。
夏炎认为,幽州地区大致可以分为核心区与边郡两个部分。其中核心区就是今天的北京,即历史上的涿郡或范阳郡;边郡则是指幽州北部地区代郡、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六郡。核心区与边郡在帝国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政府的施政方针存在较大的差异,影响并形塑着当地的人群发展与民族变迁。
夏炎试图寻找几个边郡家族的兴衰轨迹,观察他们与国家、社会的互动关系,以此作为解释中古中国家族兴衰的入口。如北魏迁都平城之后,上谷被列入都畿的地域范围,上谷地区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导致不少人开始攀附、冒姓上谷侯氏家族,与之相邻的诸郡也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但他也表示,这项研究难度较大,两汉魏晋北朝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以正史为主,辅以石刻、墓志等材料。正史中所记载的郡望与家族并不一定相关,因此这项研究重点突出“地方性”的概念,区别于以往主要集中于仕宦、婚姻与文化的研究,既不同于日本学界的“豪族共同体”理论,亦有别于从北方造像记中寻找村民生活世界的探索,呈现出由各类人群共同构成的复合型中古家族史的面貌。
侯海洋:寻找消失的延洪寺
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侯海洋在主题报告环节,初步梳理出北京延洪寺的发展变迁情况。以往的佛教史研究,多集中于某个地区的寺院群体,较少关注单个寺院的沿革与变迁。这座在今日已经荡然无存的佛教寺院——延洪寺,存在于唐贞元年间至元代末年,大致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闹市口南街园宏胡同一带。这座寺院最初由德宗贞元年间节度使刘济所建,初名“天成院”,本为延续洪州禅宗马祖道一系统的庙宇。
通过对《元一统志》卷一所收《唐故幽州延洪寺禅伯遵公遗行碑》的细致考订,侯海洋认为碑中所记“奏置延洪寺”的“清河张公”应为张允伸,关于所谓的“禅伯遵公”,虽不能确认为何人,但应是晚唐幽州地区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唐懿宗咸通初年,此人从今湖北襄阳远赴幽州延洪寺弘法,而襄阳正是洪州禅的主要传播地。侯氏怀疑更改后的寺名“延洪”二字,即含有延续、发展“洪州禅”的意味。若是,则延洪寺无疑是当时幽州城内弘扬南禅佛法的根据地。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延洪寺倒废。唐僖宗光启三年(887),又得到兴复。
辽金时期,延洪寺被誉为当时南京城中的“甲刹”,地位显赫。这一时期的延洪寺,在刻经与支持其他寺院的佛教事业方面多有建树。其中所刻经典主要是《大智度论》和《瑜伽师地论》。在房山石经题记中,至少3次出现了延洪寺的名字,说明延洪寺在当时房山刻经活动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从1991年天宁寺塔发现《大辽天王寺建舍利塔记》、20世纪70年代河北固安金代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舍利石函等考古发掘材料来看,延洪寺还大量帮助其他佛教寺院建造舍利塔以及开展传戒工作。从元人危素所作《大元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的内容来看,这一时期幽州地区的禅宗势力已经被律宗和净土宗所取代。
蒙元时期,延洪寺得到迦什叶儿(今克什米尔地区)僧侣那摩国师的修缮。至元末该寺的规模达到了顶峰。侯海洋利用2007年北京房山文管所新发现《大都大延洪寺栗园碑》、韩国发现的《至正条格》残本、《大元混一方舆胜览》、亦黑迷失《一百大寺看经碑》等材料,对延洪寺的地位与寺产规模略作蠡测。最后,他还呼吁文物部门应当恢复唐辽古刹延洪寺的旧观。
综观本次会议宣读的论文,所涉范围基本以“幽州学”为中心,重点关注幽州地区的边郡家族、佛教寺庙、墓志搜集与整理、胡人族属与身世、边地节度使等议题;同时又保持一种开放的格局,上溯下联,其中既有关于战国秦汉之际燕北长城的探讨,也有以石刻史料填补唐万年、长安县乡里村研究空白之作,更有以幽州之战为核心,借此观察五代初期北方军政格局变迁的思考。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会议中场休息的间隙,承蒙民族博物馆馆长张铭心教授慨允,与会师生得以在会场亲自观摩民族博物馆收藏的吐鲁番出土唐代“貌阅”文书和明清契约文书。其中唐代“貌阅”文书为2010年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博物馆入藏十余件吐鲁番地区出土唐代文书中的一件,主要内容为交河县要求盐城民众在指定日期接受县令貌阅的帖文。据研究者撰文介绍(张荣强、张慧芬《新疆吐鲁番新出唐代貌阅文书》,《文物》2016年第6期,页80—89),该文书由两片纸粘接而成,纸高28.5、宽67.5厘米,首尾基本完整。正面钤盖四方朱印,末尾有县令的签名,粘接缝背面也有押署、盖印的痕迹。这是可能是现存唯一一件有关唐代貌阅的官方文书。如此近距离观摩千年前文书实物的机会实属难得,也把现场会议的气氛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与会学者观摩民族博物馆藏吐鲁番文书
展望:“幽州学”的学科建设与理论思考
在闭幕式上,各位学者畅抒己见,先后进行了发言和总结。
会议的组织者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蒋爱花副教授用简洁明快的语言对各位学者的主题报告进行了点评。南开大学夏炎教授则从“幽州学”的组织架构、资金支持、学科定位、研究方向、资料出版等诸多方面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和建议。陕西师范大学胡耀飞副研究员则认为,唐代幽州和长安关联密切,提议“幽州学”的研究队伍以后可到西安进行交流与访问。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吴梦麟研究员、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王铭副教授则对“幽州学”的时间与地域概念进行了界定。日本明治大学气贺泽保规教授则提醒大家更多关注安史之乱的另外一位首领史思明、幽州地区佛教史、安史之乱以后幽州节度使、幽州历史地理等目前尚未被充分关注的议题,同时期望看到更多年轻学子的研究成果。
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最后作理论总结。首先,他认为“幽州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应当是区位性的而非全局性的。“幽州学”的研究,应当以幽州为核心,形成一个区域,通过以点带面的方式形成对幽州地区的结构性认识。在中国古代王朝国家体制的支配下,只有长安等极个别都城具有国家整体建构的意义和价值,可以借助于长安这一个地区来观察全国的整体面貌,因此“长安学”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的特点。王朝国家本身具有的不均质化的架构,决定了长安和幽州在帝国政治格局中必然具有“首”和“辅”的地位差异。但幽州地区又具有区位特殊性。唐以前中国国家建设的重心在西北关中,唐以后逐步转移到东北幽燕,幽州既是北方游牧群体对中原王朝造成剧烈震荡、首当其冲的地区,也是唐朝灭亡以后重新建构统一王朝国家的“起点”。中国古代王朝国家前期与后期建构之间的特殊性,在幽州地区得以充分呈现出来。早期从草原兴起的政权是渗透性的,偏好于中原地区的物质和财富,不会对土地产生兴趣;而后期从东北崛起的政权则是征服性的,它不仅想要获得中原地区的物质和财富,同时也开始觊觎内地的土地。因此,“幽州学”研究的基本思路应当是游移性和动态性的。
其次,“幽州学”的研究能够带来一种“范式”的转换,作为对国际学术界说法的回应。目前学界有3种比较固定的观察视角:第一种是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视角,幽州地区处于帝国的边缘;第二种是来自英语世界的、以北方欧亚草原为核心的视角,幽州处于欧亚大陆东部草原与农耕的过渡地带;第三种是从东北地区本身来观察的视角。在三种视角中,中原视角和草原视角都可以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观察角度,但东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和区域的局限,导致这一地区无法建立大规模的国家政权组织,只能向周边的中原或草原进行开拓。在“幽州学”的观察视角方面,法国学者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LA MÉDITERRANÉE et le monde méditerranéen à I’époque de Philippe Ⅱ)与中国学者张广达《从安史之乱到澶渊之盟》(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等,2008)这两部论著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前者的建构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历史记载本身的意义,通过对“地中海世界”概念的提出,布罗代尔超越了王朝国家的桎梏,从文明系统的角度进行了新的建构。而张广达先生的论文,通过观察不同文化体与政治体之间的位移,勾勒出河北地区文化分移与政治分移相联结的过程。我们应该在继承古今中外学者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幽州学”的新“范式”,注重概念内涵中学理的持续性,注重解决实质性的问题。
最后,随着新“范式”的确立,兼容的内涵越多,研究方法和手段自然也要随之扩充。第一当然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以材料为基础,注重精细性的、描述性的研究;第二是考古学,以考古材料补充文献材料的不足;第三是历史地理学,注重地缘政治格局问题,这一方面今后应当加强;第四,目前还特别缺少人类学、民族学方面的研究,人类学、民族学注重考察特定地区特定人群的活动,而幽州地区恰好是一个各种人群不断变换、交互活动的主要区域,因此这一方面学者的参与应是未来“幽州学”研究不可缺少的。此外,李鸿宾还建议,不仅要吸纳日本学者、年轻学者,还要考虑邀请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学者参与进来,形成一种兼容并包、开放合作的格局。
21日,与会代表还在北京市云居寺张爱民先生的带领下,前往河北省涿州市博物馆、辽代双塔、北京房山金陵遗址、十字寺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

在涿州市博物馆前合影留念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