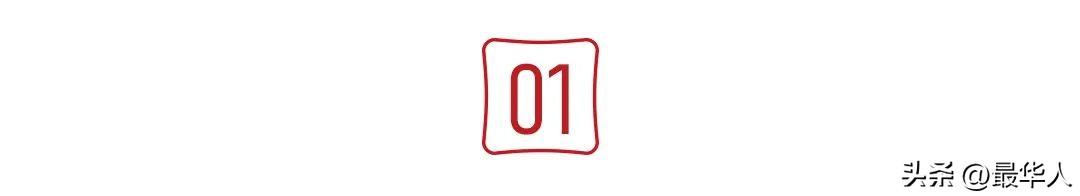第五代导演的共同特点及代表人物 回望21世纪初第五代导演的
孔德罡
时隔十五年,陈凯歌导演电影《无极》因为综艺节目《演员请就位》再次来到大众视野时,曾经熟悉的喧嚣争议恍惚间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事情。当陈凯歌再次表达对《无极》的怀念和对遭遇了他所谓的“不公正批评”的不满时,大众传媒的反响和评价已经不再直接,而是更加诉诸于对21世纪初这个还没过去多久的时代的某种“复古未来主义”——如今在舆论场上占据主流的一代好像已经没有多少人看过《无极》了,似乎也很难理解区区一部电影霸占当时全国文化话题数年的魔幻场景。面对陈凯歌和李诚儒的争论,我们都似乎在面对一部遥远的,已经被人忘却的电影,重新树立坐标系来看待《无极》和围绕着这部作品所带来的争论:重看《无极》或者“补课”《无极》成为了一种复古行为的操演。

陈凯歌参加《演员请就位》
除却舆论界对陈凯歌一贯的宽容,对《无极》重新评价的呼声实际上已经涌动了很久:以此为注脚的思潮,是对于21世纪初“第五代导演”的“古装商业大片”的重新审视。张艺谋《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陈凯歌《无极》,冯小刚《夜宴》,何平《天地英雄》等作品,它们被定性为“商业堕落”“烂片”,似乎已然被主流观众所遗忘——而正因为这些对于当今观众来说较为“先验”的刻板印象,成为作品得以重新评价的前提:主导这些作品的“第五代导演”们纷纷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低调”的状态纷纷“归来”,更加以“德高望重”而非“木秀于林”的身份存活在电影界的他们,以逐渐提升的风评,促使曾经的“黑历史”得到赎洗的机遇。十余年前流传下来的负面意见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和低平的起点,似乎更有利于观众客观而善意地看待这个曾经蜂拥而至,众声喧哗的古装大片时代。
实际上,在《战狼2》《流浪地球》《哪吒:魔童降世》等商业电影真正为“国产商业大片”做出定义,中国电影市场逐渐发展为全球前列的电影商业市场,观众对于艺术电影、作者电影和商业电影的区分逐渐明晰,对商业电影的叙事套路和拍摄模式开始熟悉之后,21世纪初第五代导演的“商业尝试”实际上越发暴露出其本质并非商业电影的一面,这也让十多年前对这些电影的批判中最重要的核心论据轰然倒塌。票房、商业价值、明星这些“速朽”的因素已经随着时代散去,这些作品终究可以以电影本身来面对后来的审视者,它们展现的“第五代”导演的“作者特质”最终成为得以留存的核心价值。
我们能够重新看待《无极》了吗?
实不相瞒,笔者也在近期重新观看了《无极》——我们对陈凯歌对《无极》所招致的批判和“恶搞”的愤恨不平是可以报以理解态度的,因为在2005年喧嚣的舆论场上,整个中文影评环境对《无极》都相对缺乏较为严肃和实质的艺术批评。关注的失焦从电影最初上映的风波就开始了,并且发展到混乱而冗杂的极端程度:导演、中文互联网古早时期网络红人胡戈所剪辑的恶搞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几乎垄断了人们对《无极》的唯一印象,陈凯歌向法院起诉胡戈,要求维护个人名誉和其被认为是“失态”的发言不仅是轰动的娱乐新闻,也成为《无极》作为一部电影本身,受关注的焦点完全偏离的隐喻。陈凯歌反复强调《无极》是中国“第一部奇幻电影”,是一种“东方新奇幻”的美学尝试,而对陈凯歌的表态,中文舆论场是普遍忽视甚至嘲讽的——这一态度的先验判断立场在于,《无极》在商业电影评判框架下的孱弱和失败是一种颠扑不破的确论,那么如果基础不牢,一切美学或者艺术理念的探讨似乎都是空中楼阁。

《无极》海报
以面向大众理解和大众可接受的审美诉求的商业标准判断,《无极》显然在很多维度都超出了当时乃至现在观众所能接受和欣赏的范围。《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的诞生和走红的起因也许并非是看完电影的观众将剧情概括为“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而是电影中大量怪诞、奇异、超出常识范围和设定与场景,从电影开始的初见阶段就给予观众强烈的陌生化和不适感。过分日式和鲜艳的“鲜花铠甲”、张东健与无数牦牛奔跑时令人出戏的特效、“满神”奇异的发型和怪诞的表情管理、被戏称为“圆环套圆环”的宫殿建筑设计、手里拿着一个“大拇指”的谢霆锋、披着一身黑衣装神弄鬼在天空中旋转三百六十度还自称“我是穿黑衣的人”的刘烨、以及集合了大陆、港台、日韩各地的糟糕中文口音,和显然是导演要求的,刻意情绪化、怪诞而间离的表演形式——若以大众审美的观点来看待《无极》,那么这部电影的每一秒钟近乎都是喜剧般的灾难,正襟危坐、一本正经的讲述历程中的每个瞬间都带着滑稽与故弄玄虚:《无极》的“豆瓣短评”中赫然有一条写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不是烂片了?”,这可能就是这部电影无论在任何时代,似乎都超出了大众乃至亚文化审美范围的注脚: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主流文化是《无极》中所展现的美学、叙事和表演风格的审美环境是如何的。
任何一个熟悉商业电影编剧模式、言必称麦基《剧本》的电影爱好者都可以为《无极》把脉出一张症状清单,但也许最根本的问题在于,陈凯歌在《无极》中多层次地暴露了艺术构想与实际执行的割裂——或者说,影片作为载体无法承载陈凯歌的构思。首先,陈凯歌和其编剧团队设定了一个几乎完全架空的奇幻可能世界,这个世界甚至在基本的运转逻辑上都与现实世界有所差异。这种根基完全建立在幻想之上的世界构建,既使得观众很难运用在现实世界中的经验通过演绎思维进行“常理推断”,也迫使创作者在解释世界观、阐释世界构成等方面耗费了大量的、影片内容无法承载的精力和片长——雪上加霜的是,陈凯歌在耗费影片时长对世界观进行阐释的时候,他叙述的风格却又是“写意”而点到即止的,这让这个完全架空的虚拟世界几乎不可能为初见的观众所理解,而只能以突兀的状态被“抛到”观众面前。也就是说,2个小时的影片片长,是无法承载一个完全架空的世界观的,影片情节固然在世界构建逻辑上是“自洽”的,但无法阻止观众以“常理”得出的荒谬观感,这首先将一部分观众直接拒之门外。
其次,陈凯歌团队为这个世界观所写作的故事和蕴含的思辨是写意而寓言式的,却又很难与设定出来的宏大史诗背景所贴合——陈凯歌可以自认在一个写意的世界观里讲述一个飘在空中的寓言故事是自洽的,但是观众在面对较为陌生而新奇的世界观时,最初的反应必然是用现实世界的运转逻辑去理解:也就是说,接受了《无极》初看奇异怪诞的世界观、愿意观看下去的观众,他们的接受基础是一种“实在”的态度,他们压制住对陌生事物的疑惑,将其中一切写意的部分都内化为“存在即合理”的认同,他们在内心自我构建了一种“史诗感”。在这样一层艰辛的认同之后,迎接来的却是一个并未贴合人情、利益等基本情节冲突模式的玄妙寓言故事,这再次造成了对观众期待意图的背叛。《无极》提供的是“写意的世界 写意的叙事”,商业电影的观众最初的期待是“实在的世界 实在的故事”,而经历了一层强行的认同历程的观众遭遇到的却是“我相信的实在世界 写意的叙事”,这层冲突恐怕比最初的怪诞观感更难以解决。
而最后,“给棺材钉上最后一层钉”的,则是追随“写意的叙事”和“怪诞奇异的世界观美学”这两层维度,在艺术创作逻辑上必然导向的人物刻画的间离性。陈凯歌的处理也许并非刻意为之,而是在他构建的美学逻辑里的顺理成章。因此,面对大陆、港台、日韩这五种不同的中文口音,他大胆地选择不使用配音而是任由演员给出原声;演员采取一种情绪先行,极端而癫狂的舞台剧表演方式,与真实传统的模仿式表演划开距离;无论是表演、台词甚至是人物造型设计,都始终存在“拉人出戏”的间离式设计,始终贯彻“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美学思路……需要赞叹的是整个团队的执行力和最终美学效果的高度一致,但最终造成的结果是,影片越能够在美学上贯彻陈凯歌的艺术构思,越在各个领域和层面都达到与美学设想的高度统一,越距离一部符合大众审美需求的商业电影背道而驰。是的,探讨《无极》是否是一部成功/失败的电影,关键在于评判的标准。它作为商业电影毫无疑问是失败的,与一切商业电影和大众审美法则相悖;但它可能同时毫无异议的是一部作者色彩极其浓厚的作者电影,尽管如何评价还见仁见智,但可以确定的是,影片的每一帧都贯彻了导演的终极意志,并没有被商业逻辑和其他因素所模糊,是对导演艺术和创作思路进行剖析的极好范例。
其实,我们并不单单可以说《无极》具备代表性,因为影片身上几乎存在着21世纪初中国第五代导演的“古装商业大片”的集体共性:那个时代,无论是投资商、导演、观众还是评论界,都认为大投资、电影明星和动作场面就意味着“商业”,初次接触商业电影制作的“第五代”导演们并非像他们的好莱坞同行那样,将大投资看作精细的预算表格和严格把控观众情绪的公式化剧本写作,而是将其看作百倍、千倍放大自身作者风格特性的机遇和手段。多年之后,当我们都明白这些电影并非“商业电影”,当初舆论界对“第五代导演”“失去思辨,失去深度,拥抱商业和庸俗”的批判可能是一种前现代的臆想,导致这些影片遭遇大众恶评的原因恰好是导演们过度地展现自身的作者风格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些作品是难得而珍贵的——纵观百年多世界各国的电影历史,我们很少能够看到作者电影能在如此的预算和创作自由下的实现。
为张艺谋“平反”是可能的吗?
讨论21世纪初“第五代导演”的古装商业大片浪潮,我们自然不可能略过张艺谋这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直以来,张艺谋21世纪初的转型和尝试所具备的开创性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英雄》其实只是追随李安《卧虎藏龙》成功后的跟风之作,古装商业大片浪潮的起因应该是《卧虎藏龙》而非《英雄》;有人认为陈凯歌1998年的《荆轲刺秦王》才是中国古装商业大片的开端,包括因为《英雄》而成为中国影视重要取景地的横店秦王宫,也最早是为陈凯歌《荆轲刺秦王》所搭建的实景。但是无可争辩的是,相较于其他第五代导演对于古装商业大片路线的浅尝辄止、分散实践,甚至一次失败后即行远离,张艺谋则是坚定不移地用《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这个“武侠三部曲”,乃至多年后的纯好莱坞商业电影制作《长城》,依然坚持既定路线的《影》等作品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古装商业大片实践,也许因此他谤满天下,但毫无疑问是这一路线的根本代言人:而相较于陈凯歌更多地是在运用商业投资主动地实现作者风格,张艺谋可能主观上是对自我作者风格试图进行抑制,试图探索商业电影的正确拍摄模式的——尽管结果殊途同归,他的“武侠三部曲”留存给我们的,可能只是他强烈的个人作者特性。
当提到对“第五代导演”21世纪初古装商业大片的“平反”声音,90%都是有关《英雄》:这部电影在上映伊始遭遇的差评来自大众审美和舆论批评界的两个维度。来自大众的维度依然集中在了电影叙事手法的非商业性上:张艺谋及其团队参考《罗生门》构建了一个简短但是由不同视角进行叙述的寓言式故事,同样因为美学上对写意的诉求导致文本空洞而孱弱,影片矛盾冲突较为虚空,这令期待看到饱满、刺激而抓人的商业电影叙事的观众感到不满足。不过相较后来的《无极》,《英雄》的世界观构建立足于已经存在多年的中国写意画传统,因此它“写意世界观 写意的叙事”的美学逻辑是能够被观众所理解的,也能够充分地揭露影片在商业制作的包裹下所蕴含的作者电影特性:大多数来自观众的差评认为影片“不够带劲”,观众可以准确把握住导演对商业片拍摄技法的不熟悉和生涩,感知到影片依然存在于作者电影的范畴而并非如宣传所言那样人人皆宜。

《英雄》海报
有趣的是,当时舆论批评界对张艺谋的“围剿”,颇有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意味。对于张艺谋“反武侠”、“谄媚体制”的意识形态批评,以及“献媚商业,自甘堕落”的“纯艺术”性质的批判,完全淹没了对于作品本身的客观评价。实际上,当时的大多数评论者对《英雄》蕴含的作者特性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才能够迅速把握住张艺谋对传统武侠个人自由主义理念的推翻和解构,能够意识到影片中秦军高度规整和可怖的“法西斯美学”所带来的美学震撼力意味着作者内心从对体制的反抗走向和解。但与此同时,正是出于对这种意识形态的无法接受,又因为客观原因不能直接地对影片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一是因为话题的敏感性,二也是因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本身反对进行意识形态批评的形象构建),因此才故意模糊焦点,将批判的重心放在“从事商业电影这一行为的堕落”之上。这一批判话语在2006年《满城尽带黄金甲》与贾樟柯导演《三峡好人》同天上映时进行了最彻底的操演,贾樟柯一句“在黄金的时代,谁关心好人”直观地将两部电影的性质做了先验规定——但这其实是主观地在打压《满城尽带黄金甲》作为作者电影的某些特质,而在十余年后回顾,可能也仅仅是一种过时的前现代“田园牧歌”言论。
《满城尽带黄金甲》是张艺谋职业生涯中恐怕不可能“平反”,但的确值得一说的作品。在3.5亿人民币投资、雕梁画栋的宫殿设计、人海战术、宫女参考法国服饰的暴露设计、周润发、巩俐、周杰伦等明星的耀眼包装下,《黄金甲》当然被当作是当时中国商业电影最重要的尝试,也自然是国产古装大片堕落失败的代表作。但是与此同时恐怕又很难否认,《满城尽带黄金甲》类似《无极》一样,是张艺谋作为导演个人作者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有关菊花、药、黄金饰品的大量特写镜头隐喻,每个时辰打更报幕的高度规整的仪式感,冷漠无情、病态扭曲的台词与人物,阴沉黑暗的配乐与最后反抗无望、只能走向集体毁灭的绝望结局,都几乎是张艺谋历年来作品内核的集中放大展现。《黄金甲》美学上严肃地贯彻了视觉和精神上对观众的双重压迫,这使得观众难以接受“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美学反讽,而只能单纯地感知到“生理不适”,最终影片留给大众的普遍印象只剩下无意义的奢侈,过度用色的视觉强奸,甚至贩卖女色的低级趣味——然而,如果不去忽略影片中周杰伦饰演的二太子一刀砍翻王旗、对女性受迫害并绝望反抗的讴歌、叛乱失败广场满地鲜血,迅速被洗刷并铺上菊花五分钟后歌舞升平的场面,《黄金甲》可能是当代中国电影对于封建政治黑暗历史最极端的明喻和直露:对此导演本身的态度也许舆论界大有商榷争议之处,但《黄金甲》对于张艺谋作者风格的呈现与研究颇有价值——张艺谋其实是一个审美小众的导演,他的艺术追求带有固有的偏执性和极端性,21世纪初的他对大众心理和大众审美的把握是并不擅长的,而被放置在直接面向大众的商业电影位置上时,他所遭遇的批判和不满终究是有理可循的:这个论断对其他的“第五代导演”同理。
张艺谋的“泛欧美”与陈凯歌的“泛东亚”:两种新东方主义
随着21世纪第二个十年国产商业电影开始涌现出真正贴合大众要求的范例,创造出不少真正意义上大众支撑的票房神话之后,“第五代导演”终于逐渐离开了这个他们并不贴合的位置,得以回归到电影作者这一本质的身份位置上,而这也是当今对他们十多年前的商业大片尝试有“平反”之声的潜藏原因。而历经多年的实践和经验汲取,张艺谋的《影》、陈凯歌的《妖猫传》,几乎同时向大众展现了在他们熟悉商业电影叙事方式和拍摄逻辑之后,重新拍摄出来,更加“观众友好”的“古装商业大片”——不过遗憾的是,尽管这两部作品在大众评价上都使导演得以“翻身”,但影片的票房与关注度早已无法掀起当年的风浪,同时这两部精心打磨的商业制作同时也失去了创作者的“棱角”:让陈凯歌和张艺谋这样的作者掌握商业电影的技法其实本质上是没有意义的——对艺术史和电影史来说,平庸的作品甚至还不如十年前那些纵情尽欲,肆意妄为的“烂片”。
本质上说,这种可以被概括为21世纪初中国独有的“商业东方主义”的艺术尝试已经过时了:在中国面临“国际化”的重要时间节点,“第五代导演”从八十年代的日本,准确说从八十年代黑泽明的《蜘蛛巢城》《乱》两部“日本战国莎士比亚”中得到了灵感,试图以一种“自我东方主义”的视角向世界阐释一种走向国际化的中国形象。张艺谋和陈凯歌采取了不同的美学路径,这与他们二人的个人美学诉求息息相关。在面对如何向全世界展现东方文化和东方形象的关键问题上,二人在叙事范畴都不得不被美学诉求所吞噬,选择了弱化思维与文字文本,而诉诸感官、情绪和后现代式“文本”——由此,他们给出了自己的中国现代美学阐释。

张艺谋
张艺谋寻求的是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结合,将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以西方艺术的建构逻辑去重新讲述:《英雄》中宛若法西斯军队般的秦军大阵,《十面埋伏》中乌克兰花海里的漫天大雪,《黄金甲》中攻城战镜头对爱森斯坦《十月》攻打冬宫的镜头的复刻,《长城》中的五色盔甲和“饕餮”的怪兽化处理,《影》中对于黑白光影近乎表现主义的操演,以及被世界广泛接受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都展现出一种“西学为体,中学为用”的颠覆性重述,这种重述的话语逻辑本质是西方视角的,是一种主动地自我凝视和自我构建——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艺谋对黑泽明的模仿绝不仅仅是《十面埋伏》里对《蜘蛛巢城》骑马戏的戏仿,绝不仅仅是《影》对《影子武士》的致敬,而根本是21世纪的中国对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的一种模仿:对于“国际化”的一种臣服和加入。
然而陈凯歌则后退一步,他当然不可能固守中国传统范畴,同样作为一个美学破坏者的他,寻求的是东亚文化圈的同构,寻求的是与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因素所融合的“新东方”。陈凯歌在《无极》中对黑泽明《乱》战争场面的复刻、对于各国中文口音的主观包容、包括中国文化的“桃花”与日本文化“樱花”的一种共构,两国共同的对于“鸟”意象的迷恋,以及在《妖猫传》以中日合作的方式,从日本人的视角来凝视大唐盛世,借助东亚文化圈既是他者又是自我的二重身份来凝视自我——陈凯歌的话语逻辑则是“亚洲人”的,他试图将21世纪的中国重新以唐代的东亚文化圈的位置和身份进行重建,实现一种对待“国际化”的地区化先行的思路。由此,我们最终可以解释,虽然思路不同,但他们都在追求一种美学的纯粹道路——由此,他们的珍贵在于他们美学探索的极端和极致:一种殊途同归的,对自我风格“法西斯”式的拉扯与推进。
陈凯歌曾经愤懑地说,“十年后你们会重新理解《无极》”,这句话也许并不一定100%适用于《无极》,但一定适用于这场21世纪的国产古装大片浪潮:剥开商业的迷雾,我们看得到某种已然消散,却始终为人所怀念的理想时代精神,抑或说,是一种“时代的眼泪”——我们已经来到对“国际化”有全新理解的新时代,无论是以“泛欧美”的态度加入和臣服国际化,还是以“泛东亚”的地区化先行思路,随着这些古装大片被观众所遗忘,也都随之过时了。我们的回望和探索,都变成了一种“复古未来主义”:我们在讨论一种可能发生,但最终未能发生的未来,“第五代导演”们的迷茫,思索与实践最终以他们个人的作者风格被写入电影史,而我们如何应对即将到来的另一种形态的“国际化”,所谓的“东方新美学”该如何建构,这些都将被抛给不可知的未来。
责任编辑:朱凡
校对:徐亦嘉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