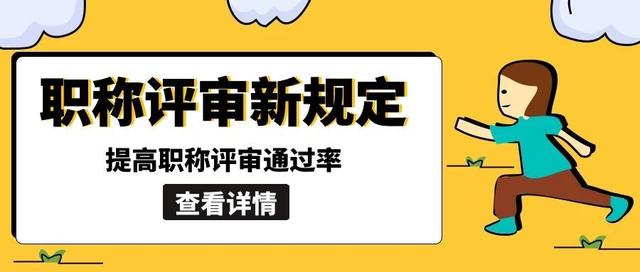许振东欲的双向呈示 许振东欲的双向呈示
一
一般认为,《金瓶梅》诞生于16世纪末叶,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长篇世情小说。
这部作品不仅以缜密细腻、宏丽铺张的艺术手法,显示了我国文人独立创作小说能力的日臻成熟,而且以丰富奇异的思想意蕴,成为我们民族审视自身发展历程的文化瑰宝。
《金瓶梅》历来以“奇”称胜。如作品一问世,马上即因能给人“奇快”和“惊喜”1而迅速流布。
入清,顺治刊本的《续金瓶梅》卷首,西湖钓叟序云:“今天下小说如林,独推三大奇书,曰《三国》、《西游记》、《金瓶梅》。”2
李渔《三国演义序》载:“尝闻吴郡冯子犹(即冯梦龙)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3
至康熙年间的著名文士张竹坡,则更欣喜于作品的奇文妙思,冠作品为“第一奇书”,并写下了洋洋数万字的评语。
在中国文学史上,《金瓶梅》的独特风貌,格外引人注目。

《金瓶梅词话》
本文所谓“欲”,是指人与生俱来的各种原始欲求。《金瓶梅》正是对这种“欲”的艺术呈示。
我认为,作品在充分膨胀普通人的欲望过程中,体现出双向呈示的特色,即一方面极力对外物世界进行炫示,详尽描述各种原始欲求的满足过程,张扬欲的暴烈、强劲与无所不在;
另一方面,又揭露讽刺欲所牵引下的人的各种骚姿丑态,暴露纵欲给人生所带来的幻灭和对社会世态的严重浸染。
前者体现出作者对纵欲的不尽欣赏与渴望,旨在“纵”或“泄”;后者则潜伏着对纵欲的恐惧与否定,旨在“节”或“禁”。
这种对“欲”进行双向呈示的特色,正是《金瓶梅》所独具的奇书品格。
它是超凡世界与凡俗世界交互作用的结果,它的产生是对我国文化精神与文人品格正面和负面特征的双重透视。
作为我国文化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小说领域一直萦绕着两个较大的原始意象,或称原型系统。
一个是空明澄澈、高洁清峻的诗化境界(以下简称空澄之境)。
它极似西方宗教体系中的彼岸世界,是传统文人清高峻洁的人格和饱满激昂的浪漫主义情愫的产物,具有极强的乌托邦色彩。
它既是人们殷殷追求的圣境,又是大家时时可以退守的精神家园。它既提供针砭浊世的恒定参数,也为处于歧路或绝境中的人不断提供进行逍遥或抵御的精神空间与后援。
这个原型系统的代表性符码常为神童仙翁、赤子痴娃,或琴棋书画、松兰梅竹,或幽涧浅溪、闲云野鹤等。与空澄之境相对,中国古典小说还存在着一个污浊糜烂、淫邪丑恶的境界(以下简称浊糜之境)。
这里涌动着赤裸裸的欲望,充满了飘忽迷离、摇人心旌的外物。它是人的原始欲求的高度凝聚与浓缩,是宣泄自身郁闷与欲望的假想性空间。
这个原型系统的代表性符码常为浊夫俗子、贪官污吏,或淫夫荡妇、酒鬼财迷,或与食色相关的无数物象等。
如果说空澄之境代表着至善、至美、至真、至清,是对生活的诗化蒸馏;那么,浊糜之境则代表着至恶、至丑、至假、至浊,是对生活的夸大性丑化。
可以说,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无不是对上面两个原型系统的不断激活。
这两个系统的紧密融合与不断冲突即生发出作品的意义层面和主题。

《红楼梦》
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指出,《红楼梦》创造了两个鲜明的世界:一个是乌托邦的世界,即大观园的世界;一个是现实的世界,即大观园以外的世界。
这两个世界的分别即在“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等
它们是贯穿全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就等于抓住了作品的中心意义。4
与余英时先生所提出的两个世界相对,我认为《金瓶梅》也存在类似的两个世界,它们分别可名之为凡俗世界和超凡世界。
具体而言,《金瓶梅》的凡俗世界处于小说的显性层面,它几乎涵盖了作品所有的现实空间和人物,并为俗浊的原始欲求所笼罩。
作品的这个世界,类似于《红楼梦》的大观园以外的世界,它以西门庆为中心,体现着“浊”、“淫”、“假”等特色。
《金瓶梅》的意义世界,是否全然恶浊淫邪呢?回答是否定的。与凡俗世界相对,《金瓶梅》还存在另一世界,本文称之为超凡世界。
这个世界处于作品的隐性层面,在作品所描写的现实空间和人物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它是与凡俗世界恶浊淫邪等特质不相容的异质成分的组合,虽有与大观园相近的“清”、“情”、“真”等共性,但未形成类似于大观园的鲜明自立的独特空间或区域。
本文认为,《金瓶梅》的凡俗世界,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构成:
(一)极度膨胀的酒、色、财、气“四毒”;
(二)热闹喧嚣的场面;
(三)普遍动物化的人物圈层。《金瓶梅》的超凡世界融汇在对凡俗世界的叙述与描绘中,或通过作者的一些干预叙述的文字得到凸现。
它虽然被包含在凡俗世界中,但并未被凡俗世界所同化、埋没,而是通过不同方式的意义渗透,极大地影响着作品的主题。
余英时先生的“两个世界”说,实际上揭示出不断生发我国文学作品意义的两大原型系统:空澄之境和浊糜之境。
《金瓶梅》的两个世界,高度凝聚着两种不同价值体系内的人生理想和人格追求。
作为贯穿全书的主线,它们不断地相互融合与冲突,从而构成了决定作品主题的叙事复调。
这种叙事复调,体现着“纵欲”与“节欲”的两相龃龉,记录了民族文化传统与感性的现实生活、求快乐原则与求至善原则等问题在人心灵碾过的痕迹,融注着作者叩寻人生真谛的深深感喟。
因《金瓶梅》对凡俗世界的表现又处于作品的显性层面;所以,以前的《金瓶梅》研究,对凡俗世界的分析、评价较多,而很少注意超凡世界的存在与意义渗透。
《金瓶梅》的中心意义,只能存在于凡俗世界与超凡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对任何一世界的过分强调、或忽视,都会导致结论的失当。

《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诠释》
二
中国文化始终重温柔敦厚的诗教,讲求隐秀含玉、优柔感讽。由此,在小说领域,对空澄之境(原型系统)激活的强度、频率,都要远远高于浊糜之境。
在具体文本中,建立在浊糜之境之上的世界,多是被批判、否定的对象。对它们的展示,一般只是从反衬空澄之境真善美特性的角度进行,而很少从正面做直接的描述。
然而,《金瓶梅》的问世,却冲断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这种惯例。
《金瓶梅》是我国文学史上把淫邪丑恶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的一部作品。
对《金瓶梅》这种独特的美学风貌,古今有非常多的表述。
如与万历本一同行世的廿公《金瓶梅跋》曰:“《金瓶梅》为世庙时一钜公寓言,盖有所刺也,然曲尽人间丑态。”5
五四文化巨人鲁迅先生认为作品“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当代学者黄霖更具体指出《金瓶梅》是暴露文学的杰构,“它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善美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6
宁宗一先生更因作品的主色调是黑色的,而直接称《金瓶梅》是中国“独一无二的黑色小说”。7
的确,作品首先为我们展示出的是一个如此的世界:阻扼不住的“欲”的烈焰到处奔突,被掏空了理性的“人”,极强地为“欲”所牵引,他们疯狂地沉浮于酒色财气的浊浪中,人与动物相隔离的篱栅遭到了无情的践踏。
整个世界几乎变成了动物的乐园。这个世界即是本文所说的凡俗世界。
构建《金瓶梅》的凡俗世界,实际上是一种故入迷境的狂欢,体现着对解放人欲的深深企盼。
古希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柏拉图曾说:“我们须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两种指导的原则或行为的动机,我们随时都受它们控制,一个是天生的求快感的欲望,另一个是习得的求至善的希冀。”8
这段话从根本上揭示了人类行为的普遍性。
《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至今仍是个不解之谜。据有人统计,作者的候选人今已多达六十多个。9
不管众说如何千差万别,距作者时代最近的“嘉靖间大名士说”,则是大多数人进行研究论证的起点。
中国古代士大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一方面重气节,讲行止;另一方面又流连诗酒,放任不羁。特别是当他们屈居下僚、郁闷不得志的时候,后者又常常成为前者的具体行为体现。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我国文人历来有“来有不平则鸣”的创作传统。这种“鸣”包括四种方式:
1、建构美好的世界,寄寓圣洁理想;
2、全面展示、倾吐自我的才华与心胸,以换取他人的理解与注意;
3、悲愤骂世,发泄不满;
4、游戏自娱,以娱化悲。这些以宣泄情感来消解内心“块垒”的方式,实质上都是“求快感的欲望”的外在表现。
《金瓶梅》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古代极为黑暗的明中后期。
当时的士大夫多已失去憧憬未来和展示自我的信心与力量,他们以“出于名教之外”自封,耽于酒色,行为失检。如著名文人屠隆、臧懋循因“淫纵”事罢官,仍然“不问瓶粟罄而张声妓娱客,穷日夜。”10
大文学家汤显祖虽志洁行芳,却对屠隆等式的行为全无贬意,反而作诗称颂,曰:“如此风流自可人,礼法之人闲见嗔” 11,“古来才子多娇纵,直取歌篇足弹颂。”12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在小说这种通俗文学体例中的不平之“鸣”, 则为3和4。
这样,对凝聚与浓缩着人欲的浊糜之境的大力激活,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当代俄苏形式主义者认为,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的制作方法。13
作为一部艺术品,《金瓶梅》是以构建一个独特的审美空间——凡俗世界,来体验放纵欲望的狂欢的。
《金瓶梅》的凡俗世界,是对浊糜之境的充分生活化、立体化、扩大化。
在具体创作中,最能体现泄欲倾向的,是作品戏拟手法的运用,戏拟是指以游戏的心态,对生活进行夸张或变形化的模仿与摹写,从而获得在现实中不能实现的情欲满足。
就作品的凡俗世界,作者通过对酒色财气四事、场面的热闹喧嚣和人物的动物性的戏拟化描写,既为自身,也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泄欲的充分空间和通道。
西门庆是这个世界的中心人物。在塑造这个形象的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大力铺张渲染他作为官、商、霸的显赫、豪奢、淫纵,并对围绕他的酒、色、财、气之事进行细腻全面的描绘,如对西门庆“日日花前宴,宵宵伴玉娥”(第二十七回)生活的津津乐道,和对他慷慨好施行为的凸现等;
另一方面,又常常穿插进夸张变形化的游戏调笑之笔,对西门庆及其周围人物的动物性特征,进行最大限度的展露。
如描写西门庆性行为的大量韵文丑化以潘金莲为代表的淫妇群和以应伯爵为代表的食客群,对他们的无厌贪求和百般承奉进行扩大化展示等。
前者,作者以西门庆这样一个独特角色为替身,实现了放纵人欲的狂欢,后者,作者又在将角色动物化的过程中,进一步使这种狂欢得以更大限度地纵深和续延。总之,它们都是人欲的强烈喷射。

《金瓶梅论集》
三
作为对空澄之境的再次激活,《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我国传统道德理性的散逸与投射。
它融注着净化人心的梦幻,体现着节欲、甚至禁欲的色彩。因文化传统的不同,我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原型观念。
西方的原型观念,建立在对人某些共同潜在心理与情感的认同基础上。在他们的艺术创作过程中,通过对原型的不断激活,那些久被压抑或忘却的无意识内容(包括个人的原始欲求)能够正常地倾泄出来。
我国古代长期以道德教化替代西方宗教的灵魂拯救职能,社会意识形态的所有门类,几乎都紧紧围绕着“怎样做人”的终极指归,具有人格伦理学的特色。
从这个角度看,建立在好坏、善恶、美丑等道德观念上的空澄之境和浊糜之境,即可分别被看作是圣人、恶人两种不同人格风范的终极之境。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典小说的成功之作,没有一部绝对以空澄之境或浊糜之境来单独构建作品的意义层。
空澄之境是人“求至善”的理想境界,体现着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理性,但它不具有导泄个人原始欲求的功能;
浊糜之境凝聚浓缩着人的种种原始欲求,这些原始欲求在传统道德性看来,是至恶、至丑的,它们只能通过对空澄之境的激活来倾泄出来。
所以,在《金瓶梅》中,对浊度之境的激活,必然连带激活空澄之境,从而与我国传统道徳理性发生关联。
但是,如果仅仅把超凡世界看作“是作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避免统治阶级的迫害和争取读者所不得不采取的一种‘保护色'”14,我以为是不全面的。
任何文学创作都存在一种先在的前结构进行“神秘参与”,这也就是我国文论所常指的“意在笔先”,它是一部作品先在的和潜在的驱动力。
在《金瓶梅》中,进行“神秘参与”的“意”,主要是当时仍盛行的宋明理学。“理学” 亦称“道学”,是自宋周敦颐、程颢、程颐至朱熹等所创立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某些内容的一种思想体系。
著名理学大师朱熹曾说:“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子语录》)
这可看作是对理学宗旨最为简明的概括。在理学家看来,天下只有一个“理”。
它先天而存,直接决定着人的命数及人们之间的尊卑关系。在此基础上,宋明理学提出“三纲五常”等许多道德准则,并把它们视为对永恒不变、至高无上的“天理”的显现,要求人们必须绝对遵守。
实际上,这种思想是要求人们安于现状,不要有超出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或自身命份的要求,从而固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内心的清净平和,并戒除个人的原始欲求。
作为一种统治我国社会很长时间的官方思想,宋明理学在不知不觉中支配着人们的意识与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创作既是对作者自身生命体验进行表述的—种“自说”,也是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他说”。

《朱子语录》
作家总在不同程度承担着为民族文化传统代言的使命。
我国古代文人多具有极强的忧患意识和使命感,他们常把为文的说教功能放在特别重要的位置,无论《金瓶梅》的作者为谁,他都无法摆脱传统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和文人这种固有品性的影啊。
《金瓶梅》所描写的凡俗世界,同时也是对作者所生活的社会现实的艺术再现。
作者对人心为物欲所覆没,人们都不安于自己的命份,并拼命追逐争斗,从而引起人性、家庭、社会的日益恶浊和混乱的现实深表不满,于是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
作品在对凡俗世界的淫邪丑恶进行揭露的同时,真切地展示了作者在纲常沦落后的焦灼无措,与临近末日般的癫狂。
面对现世的恶浊与无望,作者把自己殷殷的渴盼与梦幻转为对超凡世界的深深呼唤。
就实质而言,建立在空澄之境基础上的《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以宋明理学的道德观念编织而成的。
如对作品主旨具有标示作用的《四季词》曰:
“
阀苑瀛洲,金谷琼楼,算不如茅舍清幽。野花绣地,贫也风流。也宜春,也宜夏,也宜秋。酒熟堪酪,客至须留,更无荣无辱无忧。退闲一步,着甚来由,但倦时眠,渴时饮,醉时讴。
短短横墙,矮矮疏窗。仡楂儿小小池塘。高低叠峰,绿水边傍。也有些风,有些月,有些凉。日用家常,竹几藤床。靠眼前水色天光。客来无酒,清话何妨。但细烹茶,热烘盏,浅浇汤。
水竹之居,吾爱吾庐。石磷床砌阶除。轩窗随意,小巧规模。却也清幽,也潇洒,也宽舒。懒散无拘,此等何如?倚阑干临水观鱼。风花雪月,赢得工夫。好炷些香,说些话,读些书。
净扫尘埃,惜耳苍苔,任门前红叶铺阶。也堪图画,还也奇哉。有数竹松,数竿竹,数枝梅。花木栽培,取次教开,明事于自安排。知他富贵几时来。且优游,且随分,且开怀。
”
词中所表现出的画面和意趣,与凡俗世界有绝然的不同。
这里有清幽的茅舍、短短的横墙、矮矮的疏窗,以及磷磷石阶、殷殷苍苔。
这里的人们以松竹为知己,以山水风月为挚友。他们依时而动,顺化自然;既不奢求于外物,又无任何荣辱烦忧。
这种空静澄澈、淡泊高雅的境界,即是本文所谓超凡世界的极好写照。
它是对理学所宣讲的泯灭自我、天地人三者相融相通的入圣之境的真实描绘。
在具体叙述过程中,超凡世界所包容的人物形象,多是孝子义士、忠臣良友,是为理学所竭力标榜的人格风范。如张竹坡云:
“
《金瓶梅》内有一李安是孝子,却还有一个王杏庵是个义士,安童是个义仆,黄通判是个益友,曾御史是个忠臣,武二郎是个豪杰悌弟,谁谓一片淫欲世界中,天命民懿为尽灭也哉!15
”
这些轻财重义、是非分明的人物,可以说就是典型的超凡形象,即未被凡俗世界所吞没的善的种子。
为了强化超凡世界的说教功能,作者还借佛道的有关教理,对现实世界进行了充分的扩延与幻化。
如第二十九回“吴神仙贵贱相人”,第一百回“普静师荐拔群冤”等,都是对处于冥冥之中的域外世界的直接显示。
这个世界,依据理学的道德准则来区分善恶,并以此来确定对他们的奖惩。
这样,在对不同人物的荣辱寿夭的叙述过程中,作者一方面形象地展示出天理的无所不在和善恶有报的观念,同时也在想象中完成了对社会现实的匡正与制衡,弥补了因理学沦落而给作者带来的心理失衡。
由此,人们指出《金瓶梅》“盖有谓也”,“盖有所刺也”,以及张竹坡曰“《金瓶梅》当名之曰奇酸志,苦孝说”等,是有其一定依据的。

《竹坡闲话》
整体来讲,《金瓶梅》的超凡世界,是对灼热情欲的节制与宁息,它明显地体现着作品与我国传统道德理性(尤其是宋明理学)的血脉关系。
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一种文学基本的内容和形式以及两者的有机统一,即一种文学基本的体貌风格,都是取决于它所从属的那种文化的。中国文学只能在中国文化的根基上成长,因而不管它的表现形态多么千变万殊,它总带有中国文化的特定色彩、特定气息。”16
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金瓶梅》。
新时期以来,随着对作品意义的重新厘定,有部分人片面强调小说的启蒙意义与近代色彩,如有文指出《金瓶梅》是“反礼教的形象画卷”,
认为全书“揭示了以‘存天理,灭人欲’为主旨的封建正统思想——程朱理学受到新思潮、新观念、新的生活方式挑战而走向式微,以‘人'的解放为目标的近代思想启蒙运动正在酝酿勃发而生。”17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金瓶梅》对欲的双向呈示,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文化精神与文人品性正面与负面特征的真实展露。
这种呈示,是我们族类长期处于压抑中的动物性本能的泄露与喷发,它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破坏性,是向动物的回归,并未指向完善与解放人性的新纪元。
当然,小说也全面展露了程朱理学的式微与破败,但通过超凡世界的渗入,作者的这种展露始终融注着浓郁的失落怅惘和痛惜不满之情。
这实质上是对重建与再兴程朱理学所发出的深深呼唤,它体现着作者要修补封建末世的美好梦想。

《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
四
对原始欲求的“纵”与“节”或“泄”与 “禁”的矛盾冲突,体现了民族文化传统(理性)与感性的现实生活(感性)、“求快乐”原则与“求至善”原则等给人心灵所带来的冲击,这种矛盾是人所无法摆脱的两难之境。
就每一个现实中人所处的这种尴尬状态,《金瓶梅》的作者也有较深刻的体味。作品在对两个世界的叙述与描绘中,始终蕴含着对人自身悲剧的深深感喟。
清张潮以为“《金瓶梅》是一部哀书”。18
张竹坡也指出“《金瓶梅》到底有一种愤懑的气象”,19“以《金瓶梅》为大哭地也”。20
我认为, 这是对《金瓶梅》意蕴最深层的把握。感喟与哀惋人生是贯穿全书的基调,它构成作品最为内在的意义层面。
《金瓶梅》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首先体现在对恶的全面暴露与展示方面。
这是对作品人物的生存状态与深层人性的全面观照与客观透视,它蕴含着作者对这个特定历史时期深重的绝望与悲观。
具体来讲,这种表现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人世之恶。
《金瓶梅》的凡俗世界,魑魅横行,群魔乱舞。传统道德理性所宣传的仁义、天理、良心等遭到无情的践踏。
从社会政治来看,这个世界,官僚贪婪暴戾,统治黑暗腐朽。如作品第三十回有一段概括性的叙述:
“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蔡四个奸党,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夤缘钻剌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烦赋兴,民穷盗起,天下骚然。”
作为这个世界的特殊产物,西门庆不过是凭借自己手中的一点儿臭钱,逐步由一介平民升至山东理刑正千户的。
成为恶霸、商人、官吏三位一体人物后的西门庆,融财势于一身,无恶不作,为所欲为。
他把害人性命当作儿戏,如害死武大、气死花子虚、逼死宋惠莲等;还常以任意摧残、凌辱他人来发泄兽欲和施展淫威。
如第二十八回西门庆撒气,直把小铁棍儿打得“鼻口流血”、“死了半日”。
第二十九回西门庆一时性起,偶尔路过的来爵媳妇,只得被拦截下来听任其摧残。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有财有势者逞纵兽欲的自由,而普通的小民百姓,从来没有任何的保障。
他们的生命,就象株株羸弱的小草,随时都会受到风霜雪雨的吹打覆压,他们根本不可能捍卫与维护自身的人格独立与尊严。

戴敦邦绘 · 蔡京
(2)人性之恶。
张竹坡指出:“悲夫,本以嗜欲故,遂迷财色,因财色故,遂成冷热,因冷热故,遂成真假。因彼之假者欲肆其趋奉,使我之真者皆遭其荼毒,所以此书独罪财色也。”21
这段话道出了作品中财色对人性的巨大侵蚀。
以西门庆为中心的五个人物圈层,几乎涵盖了作品所有的人物。
他们有的为了霸拦住西门庆而费尽心机(如潘金莲),有的与西门庆称兄道弟(如应伯爵等会中兄弟),有的甘做西门庆的干儿(如王三官儿)、干女(如李桂姐),有的甘做西门庆的外室(如王六儿、林太太)等。
为满足西门庆的财色之欲,所有这些人都对西门庆百般奉迎,使作品岀现了众多“热”的场面。
然而,一旦西门庆呜呼哀哉,众人立刻做鸟兽散。如潘金莲私通陈经济、李娇儿盗财归院、王六儿拐财远逃、应伯爵等去投靠张二官等。
在这个由“热”到“冷”,由“假” 到“真”的大转徙中,我们绝少能看到人所应具有的道德理性,只能见到动物般的自私、贪婪、无耻、狠毒。
作品反复咏叹“世间只有人心歹”(第十九回、九十四回),“堪叹人心毒似蛇”(第十八回)。
在财色的诱使与冲击下,人性更多地体现为兽性。作为五个人物圈层的核心,西门庆的人性更牢固地为财色之欲所尘封。
深受西门庆之害的宋惠莲骂得好:“你原来是个弄人的刽子手, 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要看出殡的!”(第二十六回)
在西门庆身上,人性狰狞凶恶的一面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其次,《金瓶梅》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还体现在作者对人生本身的深刻认识与反思上。
这是对人类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的哲理性探寻,它展示出人类深入反观自身时所特有的迷惘、焦虑、忧惧、恐慌等。这种展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感叹人生的曲折艰难。
面对人世与人性的极端险恶,作品深深地叹息“前程暗黑路途险,十二时中自着研”(第七十五回),人生的负累在作者看来是至为沉重的。
封建传统道德以“中庸”为至德,即要求人们的言行保持中正,不偏向任何极端,追求对立两端的统一与中和。
但这种“人道”极为抽象、模糊,它究竟在哪里?又如何才能达到呢?于此,作者表现出不尽的迷惘与困惑。
作品在第二十二回、七十三回两度出现的同一首回首诗叹道:“巧厌多劳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遭辱,勤怕贪图俭怕悭;触事不分皆笑拙,见机而作又疑奸;思量那件合人意,为人难做做人难!”
这是人类所共有的迷惘与困惑,是永远也不得解的司芬克斯之谜。作为对这首诗的形象诠释,作品的许多故事与人物都笼罩着这种迷惘与困惑。
如潘金莲的机巧好胜,为她招来的不过是西门庆的惩处;吴月娘的不满,孙雪娥的忌恨和她最后的悲惨结局;
李瓶儿在西门府变得善良坦诚,这不过使潘金莲更觉其懦弱,反而更加重了她自身的痛苦与所受的折磨;
孟玉楼、李瓶儿宽绰富有,这倒成了她们遭妒的根由;李娇儿、孙雪娥拮据贫寒,则时时又要遭人白眼与冷嘲。人究竟如何是好呢?

《金瓶梅》插图 · 潘金莲受辱
作为作品的一个主要人物,李瓶儿的一生最能体现人生的曲折与艰难。
她先是嫁给梁中书为妾,但没多久即被梁山义军冲散了。流落到东京后,李瓶儿被转嫁给花子虚。
然而,长期把拦她的却是失去性功能的花太监,其夫只一味在外边寻花问柳。
西门庆的偶然岀现,无疑为李瓶儿的生活带来了新的亮色。
可是,在花子虚早死之后,西门庆却久盼不至,她又误嫁了蒋竹山,蒋是一个“中看不中吃的腊枪头”,很不称李瓶儿之意。
没多久,他即被西门庆逼走。成为西门庆的第五房妾后,李瓶儿变得温柔贤淑、忍让随和。
尽管这样,命运对她的折磨却不就此而止。在西门府,她一方面要忍受西门庆对她不顾死活的性摧残;
另一方面,她又要承受潘金莲无比刻毒的迫害。如此,紧随着自己幼子的夭折,李瓶儿年仅二十七岁就过早地告别了人世。
如果说李瓶儿早年的坎坷,源自她品性的淫邪。那么,她后期的命运多舛又归于何呢?
从李瓶儿一生的历程中,我们能真切体味到作者对苦难人生的哀悯。
(2)痛惋人生的虚无空幻。
众所周知,《红楼梦》具有浓重的虚无空幻的思想。
然而,这种思想却是“深得《金瓶》壶奥”而来,“依稀有《金瓶梅》的投影”。22
与《红楼梦》一样,《金瓶梅》一直强烈凸现着人生如梦的母题。如作者不断咏叹“青史几场春梦” (第一回)、“功名盖世,无非大梦一场”(第七十四回)、“往事堪嗟一场梦”(第八十七回)等。
作品最后以吴月娘的梦事作结,亦有将全书所有故事都归之于梦的深意。
在《红楼梦》中,虚无空幻思想的表达多融铸为人物性格的有机部分。
而《金瓶梅》则主要是通过超凡世界的意义渗透,即分别以僧尼佛道的说教、优伶娼妓的戏文唱词和作者议论评述性的文字来体现。
作品第五十一回借薛姑子演颂《金纲科》经,对人生的虚无空幻进行全面生动的痛惋。
其曰:
“盖闻电光易灭,石火难消。落花无返树之期,逝水绝归源之路。
画堂绣阁, 命尽有若风灯;极品高官,禄绝犹如作梦。
黄金白玉,空为祸患之资;红粉轻裘,总是尘劳之费。
妻孥无百载之欢,黑暗有千重之苦。
一朝枕上,命掩黄泉。空榜扬虚假之名,黄上埋不坚之骨。
田园百顷,其终被儿女争夺,绫锦千箱,死后无寸丝之分。
青春未半,而白发来侵;贺者才闻,而吊者随至。
苦苦苦,气化清风尘归风!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
这里作者以结局的虚无空幻,将生与死两种情景的巨大反差赤裸裸地袒露出来。
其中既包含着对人生本空、时光易逝、人生无凭等的不尽哀悼与无奈,也体现着作者对无数“梦中人”不知觉醒的痛惜与嘲讽。
《金瓶梅》虚无空幻思想的表达,是与全书的故事情节紧密交融在一起的。
如西门庆生时忙忙碌碌,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而死时竟连棺材也未预备下。
他一生所追求的东西,在他命丧后也无不纷纷失去。
面对命运的这种无情嘲弄,作者叹道:“石崇当日富,难免杀身灾。又随饥饿死,钱山何用哉!今日非古比,心地不明白。只说积财好,反笑积善呆!多少有钱者,临了没棺材!”(第七十九回)
李瓶儿之死是全书较为感人的篇章,在这一段曲折有致的叙述中,作者把虚无空幻的思想表现得十分委婉浓烈。
如李瓶儿苦痛宴重阳,西门庆却令盲人申三姐唱起《四梦八空》,为李瓶儿之死预先奏响了悲音(第六十一回)。
李瓶儿身亡之时,作者深深叹道:“可惜一个美色佳人,都化作一场春梦!”(第六十二回)言虽简,而情颇深。
送殡之日,在一片哀祭的氛围中,吴道官的一段与薛姑子的经文近乎相同的悼文,直将痛惋之调推向极致。
小说第一百回的情节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在这一回里, 作者通过普静和尚的法术,让读者看到了西门庆的两个截然不同的归向。
即除了让他托生为孝哥,受“项带沉枷,不能解脱”的折磨,还让他托生于沈通家,继续享受饫甘厌肥的生活。
在这极为矛盾的两种归向中,反映着作者更深的哀痛与无奈。西门庆罪孽深重,作者从情感上绝对不允许他逃脱命运的惩罚;
但面对茫茫天宇,作者又深感人类命若游丝,根本无法摆脱或改变在冥冥之中控制着人类命运的力量。
“点点轮回唤不回,改头换面无遍数。”西门庆另一种归向的出现,实质上是作者对控制着人类命运的那种力量的屈从与折服,它进一步强化了作品的悲剧意味。
美国学者浦安迪认为:“说到底,叙事就是作者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把人类经验的本质的意义传示给他人。”23
在《金瓶梅》中,作者通过对包括超凡世界在内的整个凡俗世界的叙述,以对人欲的充分膨胀和迅速覆没,真切表达了现实人生的曲折艰难、虚无空幻和人性的险恶。
张竹坡指出:“《金瓶梅》不可零星看,如零星看便只看其淫处也。故必尽数日之内,一气看完,方知作品起伏层次,贯通气脉,为一线穿下来也。”24
此处,张竹坡所指的“贯通气脉”,我认为即是作品感喟与哀惋人生的主题。

《中国叙事学》
结 语
我国文学最鲜明的特质是释放激情,作为叙事文学体例的小说也不例外。
小说作品所叙述描绘的世界,不仅要被置于情理模式之中,而且往往成为创作主体抒发内心情感的对象。
在此意义上,小说作品中的世界一般成为整体的象征性隐喻。
整部《金瓶梅》,实质上是对我国古代长期以来被压抑的、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各种原始欲求的倾泄与抒发。
作品中的凡俗世界即是倾泄与抒发情感的对象与载体。在具体创作过程中,作者对酒色财气和场面的热闹喧嚣进行了大力的炫示和铺张;同时,对绝大多数人物也进行了充分的动物性丑化。
正是在这种超越现实的叙述与描绘中,作品蕴涵着巨大的情感张力。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都可以从中得到最大限度的情感满足。
为此,我认为《金瓶梅》的凡俗世界,是一种寄寓着浓厚纵欲色彩的乌托邦世界。
在叙述与描绘凡俗世界的过程中,以对传统道德理性进行企盼与呼唤的超凡世界处于作品的隐性层面。
它依附于凡俗世界,并以意义渗透的方式显示自身的存在。这个世界代表着传统道德理性所追求的理想人格与境界,并与冥冥之中制衡着现实人物命运的上界相通。
因此,它是另一种寄寓着丰富说教色彩的诗化世界,同样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本文以为,《金瓶梅》的意义存在于“显”——“隐”、“放”—— “止”、“夸”——“刺”、“节”——“纵”等矛盾关系之中,产生在凡俗世界与超凡世界不断冲突的过程中。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作品是一种写欲的书。
它通过对两个世界的不同展示,真切表现了欲的膨胀、宣泄过程,反映了纵欲与节欲之间的深刻矛盾,寓含了作者对人生的本质与意义的深切叩寻。
接受美学认为,文学并不是一种客观的、自在的认识对象, 而是主体接受意识的“并联物”。
作品的含义、价值与历史地位,都将随着时代、地域、接受意识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对于《金瓶梅》这样一部充满“不确定性”和“空白”的作品,更是如此。
对《金瓶梅》意义的探寻将是永久的。我真心希望本文能成为以后某种探寻的铺路石。

本文作者 许振东 教授

【注】
1、2、3、5、15 候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一版,第221页,第459页,第529页,第216页,第44页。
4 余英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323页。
6 黄霖:《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见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第111页。
7宁宗一:《小说观念的更新与〈金瓶梅〉价值》,载《南开学报),1984年第2期,第29页。
8柏拉图:《斐德罗》第237页。
9许建平:《新时期〈金瓶梅〉研究述评》,见《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第3 期,第90页。
10、11、12 转引自罗小东《在现实的反思中求永恒——〈金瓶梅〉的情感意向分析》,见《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第143页。
13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关于散文理论》,见《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一版,第964页。
14 张兵:《〈金瓶梅词话〉的“人欲”描写及其评论》见《明清小说研究》,1991年第2期,第64页。
16 董乃斌:《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第23页。
17 王启忠:《反礼教的形象画卷——〈金瓶梅〉裸露人欲的思想意义》,见《学术交流》,1989年第3期,第111页。
18、19、20、21、24 侯忠义王汝梅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版,第462页,第41页,第46页,第10页,第39页。
22 张俊:《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载胡文彬张庆善编《论金瓶梅》,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1版,第269页。
23 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第5页。
文章作者单位:廊坊师范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金瓶梅>研究》第六辑,1999,知识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