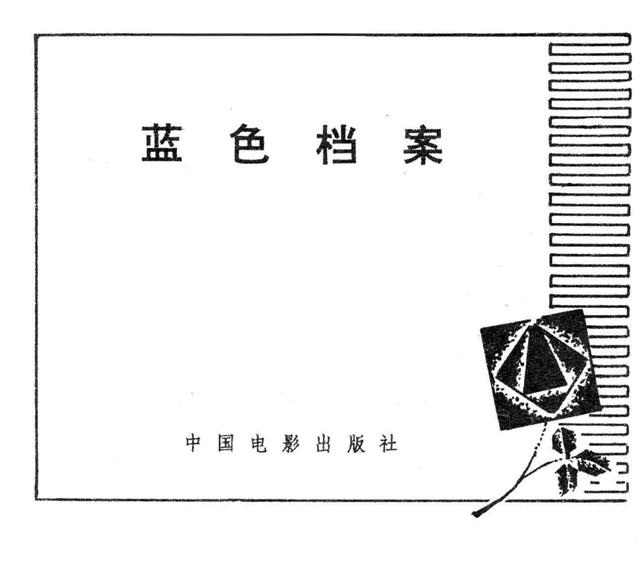多帝王争一女小说古代(因为女子一句话他争夺天下)

每天读点故事作者:镜蓝
1
熙丰十六年。
这一年发生了许多事。
比如,熙丰帝为宠爱的贵妃修建了一座锦华园,国库空虚便搜刮民脂民膏,怨声载道。
比如,起义军在同州揭竿,包上了大红的头巾,引了洋人的枪炮抵入中原腹地。
又比如,十六岁的左盈在一片敲锣打鼓声里,坐上了嫁去周将军家的花轿。
娶亲的队伍要途经喧闹的城门口。那一片治安并不稳妥,时有地痞流氓出没抢盗。有未出阁姑娘的人家早早搬离了这里,稍有些积蓄的,也都寻了更繁华的住所。
现今留在此地的,只是些做小生意的摊贩、专爱促成不正经勾当的茶馆老板娘,还有花枝招展、香粉气冲鼻的市井女人。
左家本不愿让千金经过这样一段鱼龙混杂、秩序混乱的路程,奈何周将军脑门子一热,偏要说大师测算出新娘子走这条路最是旺夫。他家大业大,在朝中权势滔天,左老爷敢怒不敢言,只得听凭他胡来。
若是周将军知晓了后来的一段故事,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自己放荡人生中众多荒唐事里最寻常不过的一件,而感到后悔?
楚帝本是凝眉,忽然想到周将军那飞扬跋扈的蠢样,禁不住闷声笑起来。
笑得像个年轻人一样。
我谨慎地敛着衣袖,静静低垂下眉眼,没有侧头瞥他。直到计算着时间都差不多了,才堪堪抬头,望向城门外空荡荡的官路。
果然立刻便遥遥听见马蹄踏响,笃脆鸣鞭声隔空打来。地面与天幕交接之际忽然出现一个小点,紧接着,极是惹眼的一人一马,携着满身风尘与骄傲,一路连连激起黄土飞扬。
身边的楚帝情不自禁动了动脚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冲上去与他一同驭马扬鞭的冲动,只是嘴唇到底忍不住微微翕动。楚帝眼睁睁地看着年轻矫健的身影从眼前打马飞驰而过,越来越惘然的神色里渐渐流露出几分歆羡。
“到底是年轻啊,真好。”
我压着裙幅的手指一顿,却是瞧也未曾瞧他,压低声音道:“跟我来。”
我与楚帝,如今皆是如魂体存在。因为我们都还没死,所以并不是惧怕白日光线的鬼魂,只是单纯的、虚弱的两道常人看不见的影子罢了。
“身轻如燕,大约就是这样的感觉了。”楚帝在我身后御空而行,声音里充满了兴奋,即便是追逐着狂奔的马也毫不吃力,“朕一辈子苦练武功,身手却也从未曾这样好。”
我默然。
眼下我们追逐的,不是别人,正是年轻时的楚帝,楚言循。
楚言循刚刚是二十岁的年纪,满腔爱国热血,说风便是雨,全凭着年轻人的冲动做事。因着不忿周将军权倾朝野、倒行逆施,便暗地里组织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帮会子弟、游侠剑士,密谋在今日的婚宴之上,闹出一番大事。
“今时今日指点江山的这帮年轻人,他们也没有想到,数十年之后竟会是他们手掌天下,挥斥方遒。”楚帝又是一番感慨。我不耐烦听这些,挥手示意他停止抒情,专心看这一场好戏。
楚言循的马疾“吁”一声停在左盈的花轿前。举臂拉开弓弦,箭头四下游移,指到何处,何处的人便抱着头蹲下大呼饶命。
他过足了大侠瘾,哈哈大笑着骂道:“乌合之众,乌合之……哎哟!”
他摸了摸剧痛的后脑勺,砉然转身,怒斥道:“哪个无耻小贼敢偷袭我?”
一片寂静无声。目光所及之处人人自危,抱住脑袋埋得更低。唯独在不远处的地面上还躺着一块碎裂的果盘。目光循着上移,花轿的绣帘还在轻轻摇曳,仿佛是刚刚有个小人儿从缝隙里头,扔了块硬家伙砸他。
他把碎瓷块掂在手里,一步步缓缓地,像靠近宿命似的,走近了花轿。
楚言循伸出手臂,即将撩起绣帘的一瞬,在场的两人两魂都屏住了呼吸,减缓了心跳,周遭仿佛一瞬便静若无人。
轿帘缓缓撩开,我下意识地望了楚帝一眼,只见他双目呆滞,嘴唇微张,紧张得手腕都在微微颤抖。
年轻男子手中红绸一闪,一道明月般皎洁的面庞乍现在绣帘后。那女孩呼吸温软,密睫低垂,十指扣在一起,红衣静坐。她与楚言循离得忒近,他甚至嗅得到那如兰似麝的呼吸轻轻洒在鼻尖上,似晚风温柔吹拂。
只怔了一瞬,他便如撞鬼一般往后惊退,一下撞上轿旁的大木箱,吃痛跌坐在地。
轿子里的美人似乎也被吓了一跳。挥手隔开晃荡不停的绣帘,犹疑地问他:“我的模样,十分吓人?”
楚言循的脸孔微微发红,意识到自己唐突了佳人,急忙撤身站起,拍拍袍袖,将手中扯落的一块红绸还给她。
左盈当下也不顾是在轿子里,正探出手去接绸带,却乍闻“唰唰”两声,两支精铁羽箭如重矛般刺穿轿厢,狠狠扎在离她半尺远的轿顶上。
饶是自诩见过大世面的楚言循,也被这两支尾羽粗大、箭头簇着冷冷寒光的箭吓得浑身一抖。左盈却只怔了片刻,随即冷下神情,仿佛下定了决心般猛然拔下嵌进轿厢里的箭支,麻利地裹进一条长长的红布里,又从果盘里抓了一把瓜子塞进荷包。
“这是军中的箭,周百平追到这儿来了。”她跳下花轿,摘了脚上高高宽宽的大红色筒靴,里面竟露出一双平底绣花鞋来。
楚言循愕然。
左盈又撕了一段繁复的裙幅,摘下叮叮当当的耳坠子。万事俱备,他才反应过来。
“你要做什么?”他禁不住问她。
左盈翻身骑上他的马,掀了个白眼:“当然是跟你跑了!要不是强抢了你的心上人,你哪儿来的理由去名正言顺地反周百平?”
“你不是周扒皮的老婆吗?怎么要帮着我?!”他一边跟着她的动作翻身上马,夹住马腹勒令飞奔,一边在激面而来的长风里大喊着发问。
“他明知道我在轿子里就敢让人放箭,何曾把左家放在眼里!既然他不把我当回事,我又何至于下作到自己贴上去?”
楚言循噎住。眨眼之后,他便奋力控紧缰绳,高呼一声:“抓紧了!”
——论射箭他不一定有多准,可或许是因为长日流亡,他在骑马一道上倒颇有些心得。
骏马骤然提速,后蹄落下的脚印几乎要赶上前蹄的脚印。左盈坐立不稳,向后栽倒在楚言循的怀抱里。
他的胸膛宽阔而厚实,只是稍稍滞了一下便稳住了身形,双臂牢牢圈住左盈的肩膀,下颌在她耳侧轻轻蹭过:“逃脱要紧,先失礼了。”
踏地声似迅疾的鼓点响在她的心上。
左盈滞住呼吸。
在某一瞬,她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好像突然有一面旗帜在心尖上迎风招展。
迎罢风雨嗅罢春,乍然便在她心间盛开鲜艳花火。
如梦如幻。
天将暗时,追兵好不容易才被摆脱。楚言循纵马奔入一片密林,藤叶交错,浓绿仿佛可以从一枝流淌到另一枝。暮意游动在树叶之上,光晕错落。碎石飞溅的速度渐渐慢下来,待视野茫茫时,马停步啮草。
楚言循率先跳下马,伸手接她下来。
她只觉得心扉滚烫,拂开他的手臂,稳稳当当跃下了马背。
楚言循忍不住笑了笑。
他牵着马走在前面,左盈没与他并肩,略向后半步跟着慢吞吞地走。
山风起得快也歇得快,只是害得她不停去抿松散的鬓角。石棱上的青苔湿冷滑腻,她穿着绣花鞋也不太便宜。
楚言循回头瞧了一眼她足下,立时停了脚步:“找个地方歇歇脚吧。”
一刻钟后,左盈端坐在铺了一层秋草的石墩上,取下发间的赤金篦子梳头,三两下重新绾好了发髻。
楚言循撑着头,拿木棍挑着燃起细焰的柴堆,嘴里叼着根草,很是放荡不羁的样子。
盯了他半天,左盈还是忍不住心中的憋屈。
“你……刚刚看到我,为什么被吓了一跳?我……很不堪入目吗?”
楚言循一怔,突然才想到女孩子最是在意仪容,这才扶着额答道:“不是……我以为肯嫁给周扒皮那个老贼的不是奇丑壮妇便是皱脸嬷嬷,却没想到你……你这样年轻好看,为什么还愿意嫁给他?”
左盈微微展开眉眼,倏然抿唇一笑,发髻上的赤金凤尾冠垂下细密的珠链,半遮了玉颜。跳跃的火焰在她面上描下生动的暗影,昏昏暧暧里勾勒得如同花钿。
“我今年二十三岁,寻常人家的姑娘,早该生儿育女了。”她面色平静,似在叙述一件与她无关的轶事,“倒是我,打小锦衣玉食,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没有哪样不是狠下过功夫,力争在所有名门闺秀里头做到最上乘,却对那么多青年才俊的求亲置之不理,迟迟不嫁人,你知道为什么吗?”
楚言循想起左老爷乐于和各路权贵结亲的秉性,便懂了几分,“左家想让你做皇妃?”
左盈颊边垂下的珠串微不可察地颤了颤。
“聪明人。”
楚言循咧开嘴笑了笑,似是想起了什么,笑意忽然便滞在了嘴角:“那……你不想进宫?”
左盈抬眸看了他一眼。
她的眼睛着实很好看——眼尾略略上挑,淡红的妆色在一日奔波之后凌乱化开,恰似红香玉软中绽开的一泓清潭,波光缓缓荡漾,竟生了几分无言的妩媚。
被她这一瞪,楚言循感觉自己的心跳快了一瞬。
左盈却笑了,“他的身份是顶尊贵的,可这乱世里谁也说不准明天会怎样——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那谁能给你?”楚言循禁不住发问。
楚帝在一旁听着,呼吸一瞬变得急促。
那一日左盈说的每一句话,他都妥妥帖帖地谨记着,密藏在胸膛里。后来这些话也在无数孤寒漫长的深夜里,支撑着他擎起灯盏,揣摩一沓沓地图与段段文字里动荡纷乱的天下形势,伴他眠在每一个难以支撑的清晨。
那些话是深刻在他记忆里的,属于左盈的一部分——
“我要的人能让我等女子不再被迫出嫁,能让世家大族解除危机,能让朝堂政事清明公正,能让万千百姓不再提着脑袋日日苟活,能给这江山带来万世昌平——”
“我要他把天下,捧到我眼前。”
两道声音说着一模一样的话,重叠着传到耳边。一个是昂首抬眸、眼神凌厉的左盈;一个是神情怅惘,眼含泪光的楚帝。
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楚言循是震惊得无以复加的。
而震惊之后,紧跟着的是狂喜。
“我就知道你并非一般女子!”他霍地站起来,吐掉嘴里叼着的狗尾巴草,激动之下险些忘了礼数,抓住她的肩头。
不知所措地收回手掌,他紧张地抿了一下唇,抬起一双湛亮的眼睛望向她。
“我打小活在沧州乡下,跟着一个落榜举人读过两年书。后来倭寇来犯,自东边入境便势如破竹——想我泱泱大国,竟毫无抵抗之力!当时我年纪尚小,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屠戮百姓、烧杀抢掠,乃至杀了教我诗文的先生……我当时便想,这乱世里,读书远不如习武有用。”
说着翻起衣袖,向上卷了卷,露出一截细长的疤痕来。
“这是沧州的流寇留下的。”他放下袖口,一字一顿,“学得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可如今的天下,没有人能够容纳这一腔的热血了。”
“那不如——就让自己,成为帝王。”
眼前的画面突然碎裂成块,一片一片向后飞去,在无尽虚空里,渐渐化为齑粉。
留在原地的是我和怔愣的楚帝。
“第一次回忆……结束了,你还有两次机会。还想看看什么?”
话毕他方才醒过神来,目光只凝在一处,瞧了良久。
我都快焦急起来,他才语气急促地开口:“我要去三十年前……阿左生子那年!”
阿左……
这个称谓猛然炸响在耳畔,我愣了愣,才问他:“当真要去?”
他目光凝重地点点头。
无可奈何地闭上眼,一声叹息随着轻轻挥下的手消散在渐渐升起的金色光幕里,空留下几圈涟漪。
2
首先迎接我们的,是阵阵嘶哑的痛呼声。
侍女进进出出,盆里的热水由清转红,楚帝的目光跟着她们走来走去,不停搓着手踱步,比产婆还要焦急。
“大人怎么还不来看看夫人?这都好几个时辰了,莫非没有人告知到那边府里?”一个年老的嬷嬷扶着案几,捶着酸痛的老腰,话语里满是疲惫。
小丫鬟急忙扶她在锦杌上坐下,她却不肯,只言夫人还在里头受苦,她不能独自安逸了去。和丫鬟纠缠了一会子,她才嘟嘟囔囔地侧身落座,只挨着坐了半边身子。
楚帝认识她。
她是左盈的乳母苏嬷嬷,左家当初为了投靠周百平,在左盈跟着楚言循离去之后把旁系的一个小姐送去做了妾室。苏嬷嬷在左家处境尴尬,又总觉得左家对不住左盈,便悄悄逃出京城找她。恰巧左盈听说了左家的事,也正要去寻她,两下里便碰在一起,自此苏嬷嬷仍旧跟在她身边。
不过楚帝对她印象深刻并非是因为此事。
称帝第三年,苏嬷嬷被他赐死。
因为她促成了左皇后与平定王韩宴的私情。
韩宴是熙丰年间与他相争的对手,后来因为永信侯势大,他们不得不结盟而战。定了天下格局的云横谷一役中,韩宴因为身受重伤而错失先机,楚言循抢先攻入京师,踏上了帝座。
时也命也,韩宴自此甘心镇守一方,受封做楚国的平定王。
楚言循对他既欣赏又忌惮。
欣赏他的豁达胸襟,忌惮他的才能出众。
这样既是重用,又是深深防备的状态维持了三年,便彻底土崩瓦解。
初称帝的他大权不稳,尚有许多有心争权的世家大族困兽犹斗。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联手抗衡之下他亦难以应付。
倒是仰仗了韩宴麾下的军队。
控马临阵、挥斥方遒的韩宴着实是俊美非凡的,倘若他是个女子,指不定也会为之心动。
这份耀眼大抵是也落入了左盈眼里。楚帝收到捷报前往探视时,只见到声称在行宫休养身体的左盈正坐在韩宴的榻前,眉眼淡然。
“一不经心又受了点伤,其实无碍的。”他胸口缠着重重纱布,说话都有些迟缓,却仍淡淡笑着,一点也不像那个杀伐果断的平定王。
她不容分说把一柄匕首递到他身侧。
“带着,防身用。”
——其实作为一军统帅,韩宴哪里缺这区区一把匕首。但这是左盈送的,他仍是珍重地收了起来,轻手轻脚放到床头的木匣里。又把自己随身佩戴的玉佩解下来递给她:“万佛寺的大师开过光的,佑人一生平安顺遂。”
——平安顺遂,其实谁都不会当真的,乱世里最不可能的事情,岂会因为一块玉佩就实现了?
不过是一份天真的念想。左盈收下时,心中微微刺痛。
而楚言循再也难以忍耐。
他携山洪之势怒气冲冲地闯进去时,左盈和韩宴并未看向他,只是周身萦绕着清浅宁静的日光,彻底刺伤了他的眼。
“韩宴!”一声近乎发狂的怒吼撞来,他的面色已是狰狞。
韩宴这才侧头看他,有些怔,然后才渐渐泛出微笑。
“陛下来了。”
楚言循顾不上理会他。
“你想要的是会把天下奉到你眼前的人,如今我百般折磨艰辛才能执掌天下,你却要——和韩宴!”
他眼睛通红,青筋在皮肤下爆绽凸起,整个人仿佛丧失了理智。随后,他抬起手臂,玄金色的袖摆微微颤抖,指尖指向了左盈。
“你是不是觉得,我不配拥有这天下,只有韩宴才配得上你?!”
逐鹿天下太多年,他的城府渐深,心境也越发波澜不惊。只有一个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左右他的情绪。
唯有左盈,只有左盈。
与左盈相关的一切,他都刻进了骨子里。
在她面前,他仿佛永远都是当年那个流亡沧州的穷小子。从初相识起,他就落于下风。
可他怎么能容忍心中供奉起来的光转而照向了他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