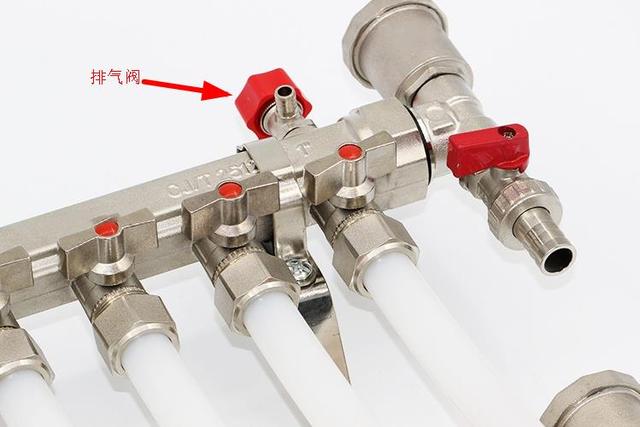辛德勇谈治学 我怎样看待版本目录学研究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11月23日上午在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举办的“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同学、各位老师:
大家好。感谢刘玉才先生的邀请,让我有机会来参加这次会议,和大家交流。
前两天刘玉才先生让我来参加这个会议的时候,嘱咐我在这里和各位谈一谈对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研究旨趣的看法。他出的这个题目,让我有些困惑,甚至很是踌躇。因为稍微关注过一点儿敝人过去所做研究的朋友都知道,通常我是不谈这类治学方法或治学理念的问题的。
为什么?
这一是因为我自己也弄不懂这些事儿,一直稀里糊涂地往前摸着石头走。所谓“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这样胡乱讲,有害无益,甚至会造成很恶劣的影响。用京油子的俚语讲,就是会把人带到沟儿里去。所以,还是少说为佳。
二是我一直认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个性化的特点。
对这种学问,往往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看法,也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做法。所谓各尊所闻,各行其是,想怎么看就怎么看,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撸袖子的是一派,光膀子的是另一派,撩裙子的也可以自成一派(古时候咱中国男人没有裤子穿,也跟苏格兰男人一样穿裙子)。谁也没有权利说只有自己的姿势才是标准姿势,自己认准的路数才是西天正道。
这类学问,通常不管由谁来做、不管你怎么做,都难以尽善其美,即若有其长,就必有其短;换句话来说,优点越突出,往往也就意味着缺点更明显。
这样一来,还有什么必要聒噪不休呢?不说也罢,不说更好。
三是我觉得像版本目录学这样的学问,做的是实学。这也就意味着研究者用的是实在力气,花的是实在功夫,解决的是实在的问题。
这种学问,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更容易做得好,做得深,做得精;年龄一大,大多数人自然力不从心,或者是虽然尚可勉力为之而功成名遂者却不想再做苦功,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一代代学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
那么,顺其自然就是了。做不动了就不做;不想费牛劲儿干活儿,也不妨一边儿歇着。可是很多人身子不行了,嗓子眼儿里的劲头却越来越大,特别喜欢摆出名家的派头,像洪常青一样做神仙指路状,一本正经地指教众娘子该怎样跳着脚儿走路。
多少年来,我一直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好为人师(现在在大学里做教书匠,需要不停地讲,这跟“师”没什么内在的联系,只是讨口饭吃而已),不要讲这些让大学一二年级本科生听起来好像很高妙而实际上却空洞无物的大道理。尽管我有很多自己的坚持,甚至冥顽不化,固执得很,但这仅仅是我自己个儿的事儿,跟别人没有丝毫关系。所以,我绝不妄对他人轻言治学方法和治学理念这些事儿。
最近几年由于种种原因讲过一些看似与此相关的内容,但大家只要认真看过我讲的这些东西就会知道,我只是讲自己是怎样想、怎样做的,这是为了让关心敝人研究的人了解我的想法,让这些人知道,我虽然很蠢很笨,但做蠢活儿笨活儿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方法论的思考,并不是脑瓜子里一片空白啥也没想,但绝不认为自己这些认识对别人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现在,既然来了,我就还本着这种精神,和各位朋友谈一谈我是怎样看待版本目录学研究这回事儿的。这些话,大家觉得或对或错、或是或非都没有关系,知道天下有这么一号人就行了。假如我讲的这些话,对大家多少有些参考的价值,能够引发一些思考,就算我没有白讲,没白白占用大家很多时间。
一、版本目录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
我讲这个内容,很多人会以为很平常,不过老生常谈而已。可若是细说起来,也许还有一些不那么平常的东西。
说这个内容平常,是不用说也谁都知道,不管是古籍目录知识,还是古籍版本知识,当然都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若说这个问题也不那么平常,就是目前学术界的一般认识和实践,实际上大多只是就版本目录来研究版本目录,这意味着版本目录表象背后所蕴涵的大量历史研究的价值,并没有在普遍的层面上得到足够的认识,更缺乏足够的挖掘和利用。
谈到这一问题,我们首先要大力肯定的是,近十几年来,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取得很多重要的实质性进展,而在这诸多进展当中,这些年成长起来的年轻学人,也就是我们这次会议的主角“新生代”学人,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可圈可点,可喜可贺。
这样的研究,虽然是版本目录学研究最基本的内容,甚至也可以说是最核心的内容,但并不是版本目录研究的全部。我们若是对这些基本内容适当向外拓展,向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其他主题延展,就可以看到,版本目录学的外延,还有很大很大一大片广阔的田野,在等待着我们去耕耘,在诱惑着我们去垦殖。
我们向外拓展版本目录学的研究范围,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广阔的空间,其内在机理,是历史文献研究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古代的历史,已经背离我们远去,我们认识它的途径,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要依赖历史文献的记载,特别是传世基本文献的记载,而我刚刚谈到的版本目录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针对的就是这些文献自身的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这就意味着我们稍微展宽一点视野,增多一些对相关史事的意识,就可以在掌握这些历史文献基本特征和内在机理的同时,由文献学的视角切入相关的史事,探索并解决一些相关的历史问题。
下面我想从我个人的学术经历中举述两个例证,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是版本学方面的事例。
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多少年来,从来没有人对这个书名有过什么疑问,晚近时期的著名学者缪钺先生,甚至明确宣称对陈寿这部书,“如此称呼,千载相承,并无异议”。然而,一辈辈学者世代相承的看法,并不一定就真的符合历史实际,而像缪钺先生这样自信满满,也并不是在他的眼前就没有与之相悖的史料,只是由于这些学者都像他一样,缺乏相应的学术意识和学术眼光,对明晃晃地摆在眼前的证据视而不见,从而就错失了发现真相的机会。
这个证据,就是此书直到明万历年间以前的所有旧刻本,在卷端题名的地方,都是镌作“国志”而不是“三国志”。这告诉了我们什么?它无可置疑地告诉我们:陈寿撰著的这部纪传体史书,本名是叫“国志”,而不是大家习以为常的“三国志”。
要很好地确认旧刻本陈寿书题名形式的重要性,当然需要具备很多基本的版本学知识,并不仅仅因为那个后来衍生的“三”字笔画太过简单,就相信其书古刻本没有省略这个字不镌的道理。譬如需要了解所谓“小题”和“大题”的由来与关系,需要了解卷端题名同书前目录题名的原生与衍生关系,需要了解书口题名的性质和产生过程,需要了解进书表的形式与表题的由来等等。这些,还都是基本的版本学知识和文献学知识,是我揭示陈寿书书名的基础,但我最终能够更加自信、更加确切地认定这部书的书名是“国志”而不是“三国志”,还与对“国志”这一书名内在涵义的理解具有直接关联,这就涉及更广阔的文化史问题,不能拘泥于就版本论版本。

日本《古典研究会丛书》影印南宋初年浙中重刻所谓咸平“专刻本”《吴书》
这就是“国志”这一书名的本义乃是“国别之志”,即魏、蜀(汉)、吴三个政权自为一国,故犹如载述西汉史事的《汉书》一样,分别名之为“魏书”、“蜀书”和“吴书”,以体现其断代为“书”的设置;而若是合而观之,这三国之史又犹如国别之志。在这后面,都有很深厚的文化背景。再并观前后时代类似的称谓,如“国风”、“国语”、“国策”、“国统”、“国春秋”之类,我们就能透过“国志”这一书名,看到一个更为普遍同时还贯穿很长一个时段的社会观念。进一步思索,还会牵涉到宋代以后日益盛行的正统论问题(别详拙文《陈寿〈三国志〉本名〈国志〉说》、《十六国春秋本名考》。前者收入拙著《祭獭食跖》,后者尚未正式发表)。
这样的认识,已经超越于狭隘的版本学内容之外很远了,但仍然主要是基于古籍版本所做的研究。这就是我所说的把版本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所取得的成果。
第二个事例,主要是目录学研究方面的问题。
最近我研读西汉竹书《赵正书》,并据之撰写《生死秦始皇》一书,有很多内容,都涉及目录学知识,或者说都是依赖目录学知识展开论述的。其中一项重要的收获,是通过对《汉书·艺文志》所著录“小说家”的分析,清楚指出新发现的《赵正书》应当是一篇小说,因而其纪事的史料价值是远不能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的。这不仅廓清了《赵正书》的发现带给人们的迷惘和困惑,同时还连带着合理地解释了“偶语诗书者弃市”这句话的确切涵义,进而重新阐释了秦始对待儒家的真实状况,还揭示了中国古代早期“小说”的真实形态。
这都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跃出于狭义的目录学研究之外很多,但是所有这些论述的出发点,都是常规的目录学问题。这当然也是我所说的把目录学作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所取得的新收获。
我自己通过这些研究所取得的经验,是研究古籍版本目录问题,犹如研究所有历史问题一样,要尽量放宽眼界,先要看得多,才能想得美,才能事半功倍,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这么多年来,我在研究中尤其注意不要划地为牢,自我约束手脚。认真读书,读书得间,纵心所之,走到哪里是哪里。研究版本目录问题,由于这些内容几乎是所有研究都必须依赖的重要基础,就更不知道它会把你带到哪里。大胆放飞自我,由这里出发,前面会有无垠的天地。
二、版本目录学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
版本目录,是研治古代文史必备的入门知识。这一点,随口说说,大概谁都没有异议,可若是落实到研究实践中来,则可以说是天差地别,各有各的干法,特别是很多历史学者对掌握版本目录知识、关注版本目录问题的认识,在我看来,是很不妥当的。
例如,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文史兼通,学术领域宽广,在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的很多问题上,都提出了自己高水平的见解。在我十分有限的见闻范围内,黄永年先生的古代文史素养和研究水平,可以说并世无双。但由于先生的研究大多都是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为基础,以文献考辨为主要分析手段,竟然被某些自以为是的历史学者,贬抑为“历史文献学家”,意即黄永年先生基于文献考辨的文史研究,很不够档次,算不上对古代历史“问题”的研究,当然也就不配“历史学家”这一桂冠,只能勉强算作是一个“历史文献学家”。
关于这一点,我可以举述一个很具体的例证。这就是大约二十年前,某一位很有名、也很有地位的历史学者,当然是我的学术前辈。当时,这位前辈很诚恳地对我说:“你的老师,近年出版的像《唐史史料学》和《古籍版本学》这样的书籍,才代表他的学术水平,而他关于唐史和北朝史的研究,就达不到这样的程度。”我当然听得出来,这位先生讲这些话的言外之意,他是说黄永年先生的唐史研究和北朝史研究,不管是方法,还是见识,都殊不足道。
我从来无意站在师承门派的立场上来评判一个学者的素养、水平、成果和学术贡献,老师水平高并不意味着学生也有成就。抛开这些无聊的世俗观念不谈,我很在意的是,这位前辈的评价涉及我们对学术研究方法的认识,而像他这样的认识,我是不能认同的。
如同我在一开始讲的,像历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的研究,究竟该怎样做好,往往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做法。在我看来,黄永年先生之所以那样重视历史文献的基础,重视版本目录问题,并不是他要把这样的问题视作自己研究的重点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内容或是专门的内容,而是他认为研治古代文史问题,必须由此入手,必须立足于此,不然是做不出来像样的研究的。黄永年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他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他就是一个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的历史学者。在他看来,若是不具备相应的版本目录学知识,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历史学者。
这一点,从他撰著相关著述的情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黄永年先生写《唐史史料学》,写《古籍版本学》,写《古籍整理概论》,这些内容通贯的版本目录学著作,写作的过程,大致都是在一个月时间之内,可谓一挥而就。为什么写得这样快,又能写得这么好?是因为他日积月累,早已烂熟于胸。平时,就是靠这些知识做学问,搞研究;到带研究生,有教学需要时,就倾泻而出,用不着现花什么力气。更准确地说,可以说黄永年先生从来没拿版本目录学知识当一回事儿,他真正关心的,是研究和解决那些疑难的历史问题,版本目录,不过是他需要利用的基本手段而已。
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我想从相反的方面来举述两个例证。
一个是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提出的和籴之法由西北边州地方制度而被引进为唐朝中央制度的观点;更清楚地讲,是陈寅恪先生把和籴以济京师这件事情,看作是隋唐制度河西地方化的一项重要例证。针对这一观点,黄永年先生曾撰写《元魏李唐和籴以济京师事考释》一文,对陈说做出很有力的批驳(此文收入先生文集《文史探微》)。
在这篇文章写成和发表之后,先生不止一次对我讲到:“没想到陈寅恪先生做学问竟会这么粗疏,连《册府元龟》都没有看。”这是因为稍一展读《册府元龟》,就可以看到许多唐代以前中原政权施行和籴以济京师的做法。这虽然大多都不是第一手的原始史料,但它很便利,也很可靠。

中华书局影印明崇祯刻本《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是分类的政书(这也是黄永年先生提出的观点),主要是编录所谓“正经正史”的内容,因而查找这类史事,是极为便利的。可是,陈寅恪先生竟然查也没查,看都没看,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说明陈寅恪先生对相关目录学知识重视不够,要不然何以能够在提出如此重要的观点时竟不去稍加查核?
版本目录学知识就是这么重要,稍一疏忽,它真的就能把你带到很深的沟里去。即使你研究历史的立意再高远,所谓“问题意识”再浓烈,版本目录这一关过不了,结果都很难说。就以陈寅恪先生这项研究为事例,即使《册府元龟》里没有上述那些内容,但你若是连这样最为便利的基本史籍都没有查核过,那么,就算结论对了,也只能说是蒙的。作为一项严谨的历史研究,这样的做法,是要不得的。
另一个事例,是我在研究司马光构建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时谈到的田余庆先生《论轮台诏》一文的问题。
田余庆先生在《论轮台诏》这篇文章中,以为汉武帝与其太子刘据之间,存在着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由此导致了巫蛊事变,并出现了他在晚年改变自己治国路线的政治大变革。田余庆先生得出这一观点的史料基础,是北宋人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记载,而这些记载是不见于《史记》、《汉书》这些可信的西汉基本史料的。
研究各个不同时期的历史问题,应该怎样合理地选用史料,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目录学问题。我考上研究生,一入门跟随黄永年先生读书,他就非常明确地在课堂上讲过,研究秦汉问题,是绝对不能拿《通鉴》当史料用的。这是因为司马光写《通鉴》时,看不到什么我们今天见不到的有用的史籍。
现在,田余庆先生竟然主要依赖《通鉴》,得出这么重要的看法,能靠得住么?尽管田余庆先生这篇文章受到中国学术界的广泛赞誉,风行中国历史学界很多年,但至少我认为是绝对靠不住的。
因为这并不是什么复杂的问题,是很基本很基本的目录学知识问题。经我查核,司马光写《通鉴》这段内容时,依据的是南朝刘宋时期王俭撰著的神仙家故事《汉武故事》。稍习史料目录学知识的人都会明白,这当然是很不可靠的。
做古代文史研究,有讲究的人,是很讲究“博通”二字的。只有博通,才能精深。只盯着一口井往下挖,是怎么挖也挖不到大海的。而研究的博通,首先就是版本目录学知识的博通,在这方面若是孤陋寡闻,其成果的总体质量和学术造诣的水平,我总是要怀疑的。业师黄永年先生一生的研究,都以版本目录学知识作为重要基础,道理正是如此。
我想,上述这两个事例,已经能够很好地说明了版本目录学知识是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基础和必备条件。反过来说,我们若是重视版本目录学知识,关注版本目录学研究,就应该能够让我们更有底气、更有条件,去研究和解决狭义的版本目录学以外的众多历史问题。这也是我想和大家讲的一项重要经验和体会。
我就胡乱说这些,一如既往,卑之无甚高论,根本上不了正道,但愿不要被信为野狐禅而贻误众生。如前所述,我只是知识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我是怎样看待版本目录学研究、还有我是怎样从事这方面研究的。
谢谢大家。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