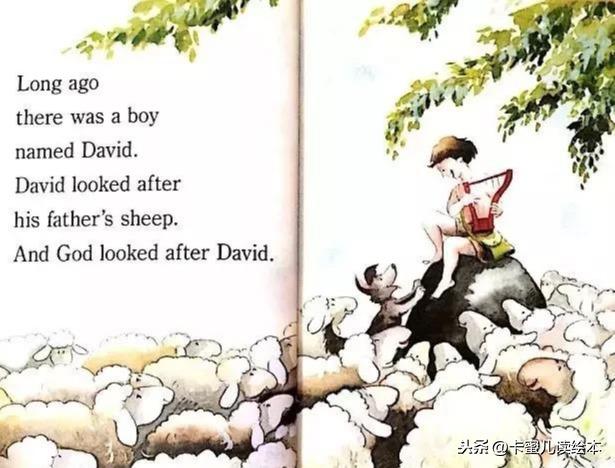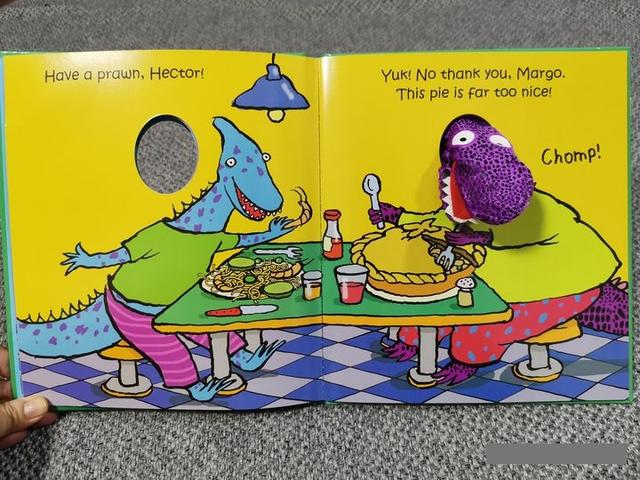后羿观北斗知农事(晚商杞地地望辨)
杞是晚商时期的一个重要国族,其族长早在武丁时期就被封为侯,担负着守卫边疆的责任。杞地还是商王室征伐夷方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厘清杞地地望,对研究晚商政治军事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晚商杞地,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晚商杞地在今河南杞县,王国维、董作宾、岛邦男、王献唐、钟柏生、郑杰祥、孙亚冰、林欢、李发等先生持此观点;二是认为晚商杞地在今山东新泰,李学勤、王恩田、陈平、沈长云、陈絜等先生持此观点。
两说各有所据,且皆可与征夷方行程中的其他地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两说的分析思路不尽相同,持河南杞县说的学者多是在识读出甲骨文中的“杞”字后,将作为地名的“杞”与《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所载的杞地相对应,从而得出杞地地望。持山东新泰说的学者则主要依据出土文献进行推定。前者属于维持传统观点,后者属于另创新说。笔者以为,就目前掌握的文献材料,将晚商杞地定在今山东新泰地区缺乏坚实的证据。

史料价值辨析
在研究上古史时,我们应优先分析同期史料是否可信,若在证明同期史料不可信的情况下,再以《史记》《汉书》等经典史书的记载为依据,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山东新泰说主要依据有四,一是甲骨文提供的地理信息,主要包括作为定点的割地地望和从杞地到割地所用的时间。据1973年山东兖州李宫村出土的割册父癸卣(《铭图》12099)和割父乙爵(《铭图》07973),将割地定在兖州。据甲骨材料得出从杞地到割地所用的时间,再乘以当时每日行进里程,就得出了从杞地到割地的距离。然后再通过比较兖州与新泰、杞县的距离从而推断出晚商杞地地望。二是晚商时期的杞妇卣铭文(《铭图》12944)反映出亚醜族与杞族联姻,亚醜族居于今山东青州苏埠屯,杞族居地应与之相近。三是西周中期后段的史密簋铭文(《铭图》05327)有“东国杞夷”的记载,而西周时期的“东国”主要指今山东地区。四是山东新泰出土的一批春秋早期的杞伯诸器,可以证明杞族活动于今山东新泰。
在这四则证据中,史密簋和杞伯诸器皆非晚商时期的史料,它们只能说明西周中期后段和春秋早期杞国的地望,并不能直接证明晚商时期的杞地地望。在商周鼎革和两周之际的大变革之下,各国族居徙无常,加大了地名流动的可能性。因此,可以论证晚商杞地地望的同期史料只有杞妇卣铭文(《铭图》12944)和甲骨卜辞中的地理信息。
但杞妇卣铭文(《铭图》12944)无法为确定杞地地望提供直接支持,因为婚嫁有远有近,两个国族通婚并不能证明其居地就一定毗邻,有时两个通婚的国族居地不仅不相邻,反而十分遥远。如《合集》2816有“妇周”的记载,其含义是“周氏”之女嫁往商王室者,所谓的“周”实际上是妘姓琱氏,其居地在今陕西西部。晚商国都在今河南安阳,距离陕西西部甚远,商琱通婚并不意味着两族居地相邻。两周之际的曹伯盘铭文(《铭图》14394)云:“曹伯媵齐叔姬盘。”由铭文可知,该器是曹国国君为嫁到齐国的女儿叔姬所作,而曹国位于今河南东部,齐国位于今山东北部,两国也不毗邻。《左传》成公十八年记载晋、杞联姻,春秋时期的杞国在今山东中东部,距离位于今山西的晋国玄远,两国也非邻国。因此,尽管确定了杞女夫家亚醜族的居地,但不能据此直接反推杞族居地。
割地地望难以确定
甲骨卜辞反映出的地理信息以割地作为推算的定点,因此确定割地地望是确定杞地地望的前提。学界一般采用两种方法确定割地地望,一是利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地名进行对证,二是利用割氏二器的出土地点将其地望直接定在今山东兖州地区。前一种方法尤其需要确定“割”字的释读。“割”字从刀从索,过去长期被认为与“索”字无异,学者们往往将《左传》所载的索地视为割地,而索地的地望又有今河南荥阳说、今江苏徐州一带说之争。但近年古文字学家的研究表明,“割”字取“以刀断索”之义,与“以手持系编造绳索”的“索”字意思完全相反。在正确释读出“割”字后,建立在“割”“索”二字基础上的今河南荥阳说、今江苏徐州一带说就不应再予考虑。
“割”“葛”二字双声叠韵,有学者提出“割”字作为地名可通假为“葛”,地望或在今河南宁陵县的葛乡,这是值得重视的意见。虽然一般认为考古资料的确定性要远大于文字通假,但学界在利用青铜器出土地点来确定某地地望时一般选用科学考古发掘品或大规模采集品,这样才能尽可能减小地名流动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割氏器仅有两件,又非科学发掘的墓葬出土。尽管考古学家指出兖州李宫村附近存在诸多殷墟四期商文化遗址,力图为割地在兖州提供考古学证据,但商文化属于一个笼统的考古学文化,其涵盖的国族众多,具体到李宫村附近商文化的族属仍然不能确定。所以,割氏二器不能排除被其他国族从外地带到今兖州地区的可能性,其出土地仅为确定割地地望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不具有排他性。
因此,晚商割地地望至少有今山东兖州、今河南宁陵两种可能性,是一个难以确定的地点。定点不确定,必然影响在此基础上推导出的杞地地望。实际上,即使我们假定割地地望就在今山东兖州,仍然无法得出杞地在今山东新泰的结论,因为学者所使用的两则用以确定从杞地到割地时间的史料均存在问题。
从杞地到割地的时间无法确定
第一则用于确定从杞地到割地时间的史料是由李学勤先生系联并拟补的三版出组二类卜辞,即《合集》24473+《合集》24364正+《合集》24367,从中得到一条完整的时地链:己卯日(16)在杞──庚辰日(17)自杞步于[雷]——[辛]巳日(18)、壬午日(19)和癸未日(20)在雷——甲申日(21)在割。([ ]中皆为李学勤先生拟补的内容)由此可以得出从杞地到割地大约需要2天。虽然《合集》24364正和《合集》24367的系联相对合理,但《合集》24473的月份、内容、地名都与《合集》24364正、《合集》24367不同,没有切实证据可以佐证李先生拟补的“雷”地是正确的。因此,这则史料无法提供完整的证据链。
第二则史料是一版黄类卜辞,即《合集》36751。根据该片卜辞记载,可以得出另一条完整的时地链:庚寅日(27)在A(字不识,以字母代替),步于杞——壬辰日(29)在杞,步于B(字不识,以字母代替)──癸巳日(30)在B——甲午日(31)在B,步于割。尽管商王率军在庚寅日、壬辰日、癸巳日分别驻扎在不同地点,但驻扎地的地名或无法识读或争议极大,不具备定点的作用,可以确定的地名仍然只有“杞”和“割”。
据《合集》36751显示的时地信息来看,商王在甲午日“步于割”(即商王率军前往割地),但缺乏何时“在割”(即到达割地)的记载,而《合集》36953“在割卜夕”的记载可以证明商王到达过割地。因为《合集》36751内容单一,皆为王步之事,可以通过王步卜辞的辞例推断商王何时到达割地。
根据《合集》36751、门艺缀合的《合集》36501+36752+37410+36772、孙亚冰缀合的《合集》36830+《补编》11115+《前》2.9.6+《合集》36555等比较完整的黄类王步卜辞可知,黄类王步卜辞每条文辞的时间间隔至少有1天、2天、3天、4天,这也是从B地到割地所需时间的四种可能性。加上从杞地到B地需要1天,则从杞地到割地所需时间至少有2天、3天、4天、5天四种可能性。
根据宋镇豪、陈絜两位先生的研究,商周时期的行军速度大约为每日60—80里,按此计算,杞地到割地的距离分别有120—160里、180—240里、240—320里、300—400里四种可能性。兖州距新泰约为200里,距杞县约为420里,大体在此范围之内,新泰说和杞县说均有可能成立。设若割地为今河南宁陵县,则距杞县约为100里,距新泰约为550里,在四种可能的行程中,可以到达杞县,到达新泰则有难度。由此可知,卜辞也无法证明晚商杞地在今山东新泰,按照经典史书记载将晚商杞地定在今河南杞县相对稳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作者:张斌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