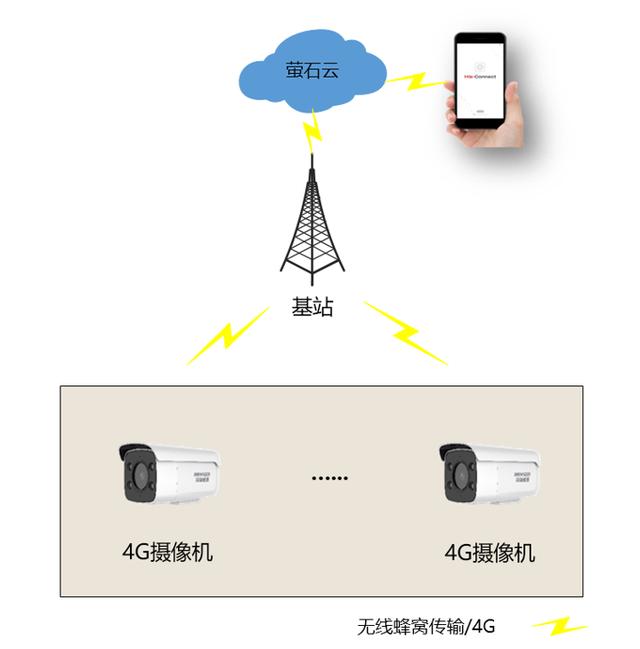等待戈多74(罗巍等待戈多)
编辑∣郝永慧 记者/志文 剧照摄影/于音

《等待·戈多》
时间:2014.12.3-12.10
地点:东宫影剧院
导演:罗巍
演员:姜哲元、杜虔行、李唫等
《等待•戈多》上演的第一天是媒体场。演出结束后,罗巍走上舞台和观众见面,颇有些腼腆地说道,“我没有什么可说的,希望大家多提意见”。短促的尴尬之后,饰演波卓的演员李唫开了口:“谢谢大家!” “对,谢谢大家……”罗巍应道。

隔天再见,是在使馆区河边一个幽静得只有扫路工才会不时经过的小咖啡馆里。依照那天晚上罗巍的表现和这一日谈话的地点,我想对话一定会进行得相当艰难;说实话,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没有气场,如此不善言辞的导演。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见面未到三分钟,罗巍就已经在自己的主场射了好几次门,健谈得甚至让人有点儿吃惊——而且,不得不说,还是相当优雅的那种。“媒体场那天很多人都在玩儿手机,但是奇怪的是,后面没有一场是这样的。可见这些有知识的人对“等待戈多”这个本儿有多深的偏见。”
三分嘲讽,三分无奈。剩下四分应该是冷静,理性的思考。这就是我所观察到的神情,人的和戏的。
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类”
谈到自己的初衷和对这个戏的想法,罗巍说得最多的似乎不是“等待”,也不是“戈多”,而是“人类”。这样一个大而无当的概念不免让人生疑,而面对这个概念,罗巍并没有选择“拆卸”和“组装”,而是直面戈戈和狄狄、波卓和幸运儿惨淡的人生。
《文周》:你怎么看待自己的这版作品“忠实”于贝克特的一面?
罗巍:忠实在于从文本本身来看改动是非常微弱的。改动最多的是比如说把古罗马的一个诗人的名字换成李白,把凯撒的名字换成了奥巴马,最多也就是做一些这样的置换和调整。所以几乎所有的语言都是来自于我们的翻译本。当然我综合了好几个本子,然后做了一些调整。我们完全没有另外的解构,解构也是完全按照原著,只不过做了一些删减,删减比较厉害的部分就是等待,尤其是第二幕。还有一个方面,我们现在所呈现出来的本身就是贝克特先生剧本当中存在的东西。有很多观众都会有这样的疑问,说这出戏怎么会排成这样?不是很枯燥么?不是根本就没法看的么?不是没有什么故事么?为什么你们这一版什么都有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因为很多人本身是带着他脑子里既有的“观念”去看的这场戏,他觉得他已经知道荒诞派戏剧是什么样儿了,所以他看不到别的东西。实际上我们所有的东西,包括人物,事件,包括剧本的结构,都完全没有被打乱。所以可以说非常忠实,可能还没有什么版本像我的这部这样忠实。

《文周》:你在《等待•戈多》当中想表达出什么和原剧不同的东西吗?
罗巍:如果说颠覆,我觉得是相对于这个戏以往的演出的历史,以往大家基本上都是在关注所谓人类等待的虚无,人生就是一个等待的过程,是无聊的,诸如此类。而我们这一次认为,“等待”这个命题对当下的人类已经不是一个有危机感的东西了,因为我们有咖啡,有书,有电影,有女朋友,有别墅,所有这些光鲜亮丽的表象都在帮助我们忘记和回避我们的存在。我不是想要回答“戈多是谁”这个问题,我是想展示一种关系,也就是戈多对于这两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类要找东西拴住自己?这是我们想要表达的核心问题。
之前有很多业内人士,甚至是戏文系毕业的我的师兄师姐,在谈到这部戏的时候,他们还以为这个戏只有两个人,由此你就能看出人们对这个戏的误解和偏见有多深。实际上波卓和幸运儿的篇幅是占得相当之大的,如果说这两个人没有了,等待戈多也可以演,就是演两个人在那儿等,可是为什么贝克特先生要把这对奴隶和奴隶主放上舞台?这才是当下的人类可怕的处境。这两个人一直在走路,幸运儿身上背了极其沉重的行李,而且不放下来。他有放下来的权利,但他自己放弃了,这就牵扯到当下的人类一个很切身的命题,也就是你如何选择你的人生,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很多人为了求得安全感会希望负重,觉得我的人生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有价值,我是被肯定的。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就说世界将会变成一个大市场,而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退化成一种交易关系,市场关系。所以我想我颠覆的并不是贝克特先生,而是我们以往对这部剧的观念,以为等待才是这部戏要说的东西。而我觉得恰恰相反,这出戏的人物关系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我说的是尊严”
要说剧中最惹眼的,莫过于舞美布景。罗巍对他的布景有一种“漫不经心”的认真。“您的这些舞美,有什么含义在里面吗?”“没什么特殊的含义,”——这往往只是开头,接下来——好像有不止一层含义。虽然在我看来,整个舞台上似乎总是隐隐约约有那么一股“政治氛围”,但罗巍强调,那只是他想表达的其中一个问题。“政治只是交易的一个方面,我说的是尊严。”

《文周》:舞美中的的那座雕像其实被原剧本称作“树”,这种转换的构思是什么?
罗巍:它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首先,这个剧本本身有一个很强烈的特质,就是很多东西都是不确定的,比如戈多是谁,什么时候来,等等。所以在整个演出当中也会有很多指鹿为马的东西,比如白萝卜、胡萝卜,拿出来的是葡萄干,鞭子叫普拉达,篮子叫LV,包括雕像,我们管它叫树,但具体是什么树,并不知道,它就是一种不确定的体现。
其次,在这样的基点上,我们还要想一想现在的世界上为什么到处有偶像、权威,无论是商界、政界还是演艺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功人士,有的干脆就称为“男神”、“女神”?就是因为过去的那个神坍塌了,人们不再相信,但是这些人神的存在恰恰说明人类从心理上是对宗教是有需求的。这种东西在中国称之为“道”,可能哲学家还会称之为“真理”,其实都是一个意思。雕像的基座上还有三个字,“知识就”。上帝就是被我们的理性和知识消灭的。一战和二战之后,人们就会有疑问,哪有什么能够拯救人们的上帝?没有了这样的终极关怀,才有了存在主义。
《文周》:时钟在这个戏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和作用,您是怎样构思的?
罗巍:贝克特在这个剧本中着重探讨了时间,因为时间感是和我们的存在感直接关联的。一旦你没有了时间的感觉,你就会发现你是不会死的,这就是波卓为什么说你提什么都行,但是千万不要提时间。我们这个钟是一个没有针的钟,很多人说我们用了达利的形状,但我没有想到我的舞美设计会把这个钟画得那么像达利的钟,我只是告诉他要一个没有指针的钟,最后就设计成那样了。不过我们的这个钟也是有说法的:时间是扭曲的,而且时间是静止的,我们不论做什么都不会改变时间的属性。
《文周》:戏中出现了各种名牌、购物车还有塑料袋,这是原剧中没有的。
罗巍:是的。我想对现代人而言,什么能代表权势?就是财富、资本,或者奢侈品。什么能代表尊严?是不是有钱就有尊严?现在有钱可以做任何事情,你可以搞戏,你可以成为一个大师,或者你也可以买官卖官,买个教授的职位,受人尊重,就是钱无所不能。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尊严,有没有戏中所说的“立场”?人类的尊严是不是在遭受资本的无情践踏?我认为展现这些也就是戏剧的价值。

“艺术如果是大众的,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
《等待•戈多》的角色们一直在“耍宝”,然而有趣的是,罗巍要求他们真诚。“真诚地耍宝”,在导演看来,这不失为一个真实的人,而这当然与那些“能演”的演员相去甚远。当然,谈到演员,罗巍也不无遗憾。“要拿我这个年龄段的演员,演出来完全会是另一个样子,但是他们太年轻了。”
《文周》:我们看到这出戏中的人物也都没有什么明确的性格,那么演员如何把握?
罗巍:我一直在跟他们说,“把握当下”,把握行动,也就是现在他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其实贝克特的剧本当中都有潜在的、非常清晰的人物的行动线索,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跟他们的心理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比如波卓他对表演的爱好,比如我对扮演戈戈的演员说,你演的这个角色是一个彻底被生活打败的人,你可以为了一根鸡骨头低三下四,这就是你生存的原则。我想这出戏的荒诞性也就体现在这种两难的境遇。
我也对我的演员说,这个戏我们也可以这么演:两个人就一动不动地站在树下,时不时地说两句台词,把该说的台词都说完;波卓和幸运儿从舞台这边走到舞台那边,走一个小时。这样的话,我们展示的就是一个“状态”,一个静态的东西。但是我希望他们能演活生生的人,贝克特写的这几个人物是鲜活的、真实的,能看得到的人。我们可以站在理论家的高度说“现在的人都是符号”,但是,我们只有在舞台上展示活生生的人,才能够触动观众那根麻木的神经。

《文周》:怎么考虑到要用特型演员?
罗巍:坦率地说,十几年前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也没看懂,当我弄完了《朱丽小姐》,偶然地又看到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剧本与《朱丽小姐》的异曲同工之处,也就是它们都探讨了权力关系。那个时候我就想我要找一个“残疾人”,因为这就是我们现代的人的写照。比如我们这些知识型的人,我们的脑袋都特别发达,也就是理性特别发达,思维特别活跃;但是我们因此也丧失了我们的本能,比如说爱的能力。特别是从掌握了知识的女性身上,能看得更明显。朱丽小姐身上就不具备爱的能力,因为她启蒙了,她开化了,而这种能力应该是女性天生具有的,这就很荒诞。从形象上来说,没有比现在这个演员更符合我对现代人的理解的了。
《文周》:《等待戈多》这出戏在50年代首演时反响就很一般,反而到监狱里效果奇佳,所以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观众的接受度一直不是很高,缺乏您谈到的那种“阅历”。那么《等待戈多》对于普通观众到底有什么意义?
罗巍:我觉得一出好戏就是能让浅的人看得浅,深的人看得深,我并不希望我应该从事非常极端,或者先锋前卫的探索,我还是比较尊重原著、文本本身赋予的内涵,我的工作无非就是把这种东西挖掘出来。艺术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大众艺术”,艺术如果是大众的,世界不会是现在这样。所以我不去考虑有多少观众能够欣赏。如果一场演出五百个观众里能有一个观众看到“上帝死了之后,人也死了”,我觉得就是成功的。我没有想很多。

————————————————————————————————————————————————————————————————————————————————————
首场演出,我身后的两位观众在中途便起身退场了,声音听上去有些愤然。这样的问题对于一出荒诞派戏剧来说似乎是家常便饭,更何况观众并非是自愿买票前来“捧场”。我把这样的问题告诉了罗巍,他倒显得淡然,似乎对自己的创作充满了自信,但另一方面又主动让我提些意见。“现在我听到的大多都是好评,这不是一件好事。”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面前摆着《朱丽小姐》的剧本,黑字体上满是圈圈点点。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