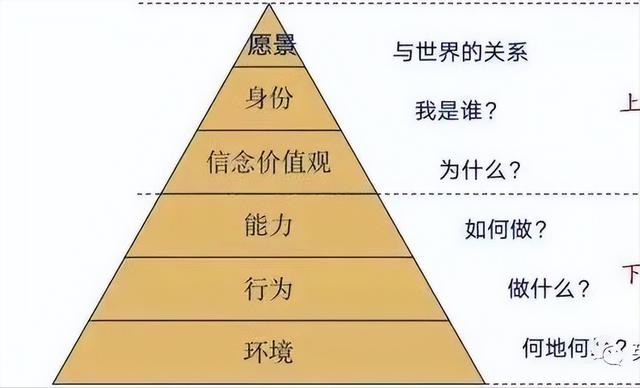竹林七贤为什么受到人们的敬仰(竹林七贤真实与想象)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34期,原文标题《竹林七贤,真实与想象》,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竹林七贤”的七人是真实存在过的历史人物毫无争议,但是否共同聚会过的团体则并不能达成共识。后世所形成的“竹林七贤”的称谓,是对淡泊隐逸、自由放纵的士人精神的想象,却也在某种程度上抹掉了这七人性格与命运的差异。
实习记者/徐亦凡
主笔/丘濂

《七贤雅集图》王明明绘
“竹林七贤”存在吗?
嵇康、阮籍、山涛、向秀、阮咸、刘伶、王戎,这七人因为“竹林七贤”的名号被后人视作一体,也作为纵情自我、竹林游弋的故事主人公成了中国士人阶层千年来钦羡的文化符号。直到上世纪40年代,这段从古至今流传的“七贤”历史首次引发真实性的考量。
学术大家陈寅恪先生发出新论,认为“竹林七贤”并非历史实录,而是后人附会创造出的故事。陈寅恪在《清谈误国》中提出,先有“七贤”后有“竹林”,东晋士人受到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佛经中“竹林精舍”之名和《论语》中“作者七人”的说法,融合出“竹林七贤”一说。他认为,“竹林”既非地名,也不是事实的竹林。“竹林七贤”故事发生地在今天的河南焦作,陈寅恪考证称,焦作属北方而无竹。
陈寅恪的见解推动更多学者对“竹林七贤”真实性予以考证,带来了不同维度的质疑与讨论。
相对易于解决的是“竹林”问题。陈寅恪认为竹林是子虚乌有,而是来自对佛经的附会,但这种说法与《魏氏春秋》有所出入。学者卫绍生认为,《魏氏春秋》两度提及“游于竹林”,那不该是虚指,而应当有一个确切地点。学者范寿康则提出,“所谓的竹林,似乎并无一定的地点,他们七人都喜欢选择附近各处的竹林作为集会的地方就是了”。但《魏氏春秋》在叙述竹林七贤时,多谈及嵇康所寓居的山阳县,这里应当是七贤主要活动地点,也更可能是竹林所在地。
学者王晓毅则通过实地考察和梳理历史文献记载,试图证明,嵇康居所山阳,也就是今天的焦作在古代是有竹子生长的,甚至作为经济作物大面积人工种植。六朝地理文献《述征记》和《水经注》则明确记载,山阳嵇康园宅附近种有竹林。
即便确有竹林,七贤前的“竹林”名号是否仍有可能来自佛经呢?王晓毅对《大正藏》中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迦兰陀讲经园林的翻译进行了统计,发现共有“竹园”“竹林”或“竹林园”三种。但在形成“竹林七贤”之说的东晋初期,中国社会更习惯称竹林为“竹园”,直到七贤名号流传开后,佛经翻译中的“竹林”比重才有所上升。可见并非时人借佛经为七人命名,更可能是“竹林七贤”称号的流传影响了佛经翻译。
从佛道两教的分野来反驳陈寅恪也是一种思路。学者韩格平认为,用佛教意味浓郁的说法来为“道家情趣卓然的玄学领袖命名,既与嵇康等人对佛教的态度相抵触,也难以为中土广大士人所接受”,东晋时期儒释道虽然有融合,但还是相对独立的不同学说。佐证是南京西善桥出土的东晋古墓壁画,在画中,七位魏晋名士与春秋时期隐士荣启期并列出现,而后者是众所周知的道家人物。韩格平据此推断,将竹林七贤的命名确定在道家范畴是符合士人共识的。
质疑还来自七人居所距离,如果相隔甚远,也可能成为齐聚山阳的阻碍。不过梳理史料可以发现,如果以嵇康寓所山阳为中心,其余六人都距其不远。
其中向秀与山涛原籍便在河内郡,今天的地理范围大致涵盖焦作市全市,以及洛阳、新乡、鹤壁、安阳四市的部分地区。向秀在《思旧赋》称,“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实他不仅住处与嵇康接近,二人在隐居生活中也接触密切,常常同游。而王戎原籍虽在琅琊(今山东省东南部地区),但“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可见是嵇康多年的邻居。至于阮氏叔侄,他们居住在250里外的洛阳,但史书中留下他们在山阳往返的记录。事实上,当时洛阳的达官贵人最喜欢北上河内,“在山墅中饮酒清谈”。刘伶虽是沛国人(今安徽宿州部分地区和淮北),活动范围却在洛阳与河内一带,刘伶墓距离嵇康的竹林园也仅几十里,比起山涛与向秀故里甚至更近。
有竹林,有七贤,没有地理限制,但据此依然难以确认“竹林七贤”的故事究竟有无真实发生过。比如韩格平推测,这个名号可能是倾心道家学说的士族文人基于自己的审美情趣提出的;还有看法认为“竹林之游”存在,但未必是这七个人的故事,陆威仪在《哈佛中国史》中就认为,这七个人没有在同一地方聚齐过,有些可能从未见过面,生活中并无交集;但也有学者提出,这个名号其实在当时就已经存在,只是因为魏晋禅代之际的政治恐怖而无法见诸文献。对嵇阮二人颇有研究的汉学家侯思孟的看法与之相似,他认为这一得名应有其事实基础,并非完全出自传说,但侯思孟也认为“竹林七贤”故事在其身后百年流传可能出于司马政权的宣传需求,试图借此传达对诸贤的宽厚态度。
公元248年的竹林同游真实吗?
公元248年,即正始九年,是这个偶像符号真实出现过的最合理年份,七位名士的人生轨迹极有可能在这一年交汇于山阳竹林。
正始年间,曹魏政权与司马氏族政治斗争绵延,混乱政局是促使当时名士避世隐居的重要前提。而在248年时,七贤都没有官职,处于闲暇状态。
最早在山阳定居的,应是嵇康。在魏晋时期,山阳并非穷乡僻壤,反而是名士“隐居”胜地,而且与洛阳之间有便利的交通和驿站。嵇康在山阳有园宅,可能继承自父亲,也可能是魏长乐亭公主与其结婚的陪嫁。
隐居山阳前,嵇康曾短暂为官,但不久辞官致仕。个中原因与他崇尚的老、庄不无关系,嵇康对庄子的思想深以为然,选择隐居与这种价值观也足以自洽。而政治因素则更为重要,一方面,嵇康与曹魏有姻亲关系,有着无法剥离的天然政治身份,而另一方面,他的性格也无法支撑自己在政治争斗中顺遂自如。
作为七贤中声名最盛者,嵇康对于政治的极力回避远比阮籍更坚定。嵇康纵情山水以追求精神自由,寓居山阳过着“反传统反社会”的返归山林生活。山涛举荐嵇康出仕时,他坚定回绝,称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直指司马氏。侯思孟认为,嵇康一再拒绝与司马政权合作虽然很危险,但远离政治带来的自由也使其获得精神满足。
向秀此时也处于隐居状态,他与嵇康相识于洛阳,住在山阳临近的怀县。向秀与嵇康性格并不相同,不仅低调内向,也并无违背礼教的行为。据《世说新语》记载称,“康傲世不羁……而秀雅好读书”,性格差异如此巨大的两人,却私交甚笃,一起锻铁一起灌园,还和另一才子吕安交游甚密。《太平御览》记录了三人的隐居生活,“向秀常与嵇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他们时常远足,随意漫游,从心所欲的状态完全符合人们对归隐生活的想象。
247年,七贤中年龄最大的山涛因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辞去河南从事一职,从洛阳回到河内,《晋书》记载称,“投传而去。未二年,果有曹爽之事,遂隐身不交世务”。明辨时局又极善自保,后人对于山涛的这一特质大多无异议。学者罗宗强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中提及,山涛在处世态度上与嵇康、阮籍的任性放诞非常不同,从没有违礼之举,他积极入世也谨慎处事,非常有见识,“不看准政治形势,是不会采取行动的”。在山涛身上,出入儒道、二者调和的处世方式体现得极为鲜明,他最大特点就是所谓“通达”,“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所以,他有志于出仕以济世,又深谙老庄超脱物外和避害保身的精神,才会在两大政治集团的夺权漩涡中及时抽身而出,于斗争最激烈时归隐山林,避开了两年后的“高平陵之变”,没有因追随曹爽而遭连累。
阮籍也在同期选择远离政局。248年,他曾短暂任尚书郎一职,后曹爽欲召其为参军,但阮籍假托生病隐居乡里。相较于山涛的明哲保身,阮籍辞任官职似乎更多出于对腐朽局势的回避,对世事感到不可为的无奈。不同于前者在玄儒上的调和,阮籍身上体现出更多矛盾,这种苦闷在他的咏怀诗中也有所折射。他反对名教,对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可又并不能完全超脱物外,他心中也有济世之志,曾感慨“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不论是何动机使阮籍拒绝曹爽,至少他急流勇退,在248年得以加入竹林之游。
而嵇康与阮籍的结识,以及七贤有可能相识,都离不开山涛发挥的关键作用。244年出任河内郡功曹时,山涛结交了才子嵇康、吕安,又介绍阮籍与嵇康相识。《世说新语》中记载,“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邀请他们来家中做客,三人清谈“达旦往返”。
七人中,山涛最年长,而王戎最年幼,二人相差29岁。但王戎自小就非常聪慧,“幼而颖悟,神采秀彻”。他的父亲王浑与阮籍都曾任尚书郎,但阮籍每每上门拜访时,却是与小自己20多岁的王戎相谈甚欢,《世说新语》记载阮籍对王浑说,“与卿语,不如与阿戎语”。王戎极有可能在阮籍辞官后被他带入清谈与聚会。
阮咸为阮籍之侄。阮咸本人也是放达随性、不拘小节的名士风格,会用酒瓮痛饮,据说还曾“与猪共饮”一缸酒。
另一位无意于仕途的刘伶也非等闲之人。他行事作风极其豁达,而且最是爱喝酒,还写过传世的《酒德颂》。尽管他长得矮且容貌甚陋,却是难得看上别人。但他与阮籍、嵇康的关系却很不错。《晋书》记载称,刘伶“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
至此可见,七人已经相识,彼此间的空间距离也不构成同游的阻碍。时、空、人三元素都已聚齐,七贤同游不是不可能事件,这个名号或许就来自他们七人某次竹林聚会。
可惜的是,248年也成了七人可能相聚的唯一时间。一年后,政局遽然生变。司马懿趁曹爽与魏帝曹芳到高平陵谒陵时发动政变,也称正始之变。
高平陵事变后,阮籍被司马懿召为从事中郎,他重新出仕,离开了山阳竹林。
被赋予的群体想象
当“竹林七贤”的名号在后世文献、诗歌、画像以及士人口中被屡屡提及时,它也成了一个被标签化的偶像群体。其实,七贤虽都谈玄饮酒,脾气秉性却各有差异。至于政治立场七人更是不尽相同,其中嵇康与王戎算得上是处于两极。嵇康半生隐居山阳,至死也未出仕司马政权,最终却卷入朋友吕安之事入狱,并遭司马氏处死。幼年成名的王戎却是七人中最热衷仕途的,《世说新语》和《晋书》还记载他贪财吝啬。王戎官拜司徒,封安丰侯,70余岁善终。后来南朝人颜延之作《五君咏》,以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向秀五人各成一诗,就弃在官场上颇有作为的山涛、王戎二人不取。
虽然命运与性格大相径庭,但被覆盖于“竹林七贤”的名号下时,“豪尚虚无,轻蔑礼法”或是任性放诞、喝酒纵情成为七贤的统一标签。
但这也说明,七贤的故事真伪好像不那么重要,至少对于中国士人阶层来说,“竹林七贤”更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被赋予了审美理想和精神寄托,“竹林之游”则成为文人所向往的一种情结。
学者孙立群认为,中国古代士人从产生之始就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视参政入仕如农夫之耕,而士人隐逸与士人入仕是相并而生的。从这一视角理解,与谈玄、归隐联系最为密切的七贤故事看起来是个令人向往的精神自由模板,是在混乱时局中也要追求人格独立与自我意识。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魏晋风度》,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