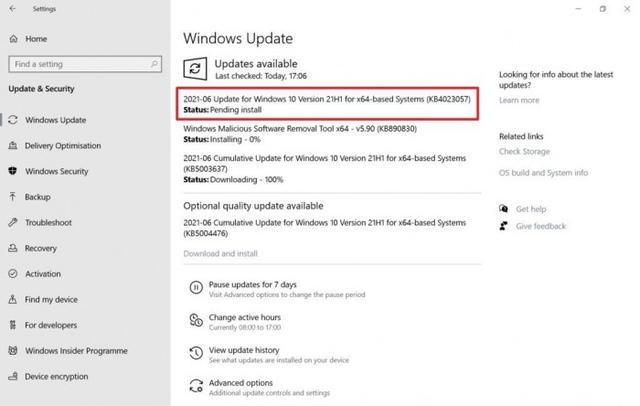弱者向更弱者举起了屠刀(总对弱者加标签)

繁华都市,高楼迭起,居住和穿梭其间的人乐于讨论土地价格、建筑师的设计理念、投资者心态,却往往忽略建筑工地的铁皮围墙之内,曾有这么一群人,靠双手和肩膀一点点筑起整座高楼。
从二十岁出头至今十余年,林立青一直在台湾工地做监工,负责整合技术部门、协调不同工种、替雇主监督施工进度。他既是工地工人、管理者,也是观察者、记录者。去年年初在台湾出版、今年四月引入大陆的《做工的人》一书,将人们的涣散已久的视线,拉回到工地,聚焦于一个个鲜活的人。
在台湾版的封面底端写着三行字:“这社会要求他人有尊严地活着的,几乎都是收入稳定的人。”封底写:“一个青年监工的批判与关怀,那些心疼他说不出,所以他写下来。”从决心写他们的那一刻起,林立青就明白要做什么——“翻转外界对工人迷信无知的误解”——哪怕他最终可能什么都没能改变。

《做工的人》
作者:林立青 著 / 赖小路 摄影
版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18年4月
近日,新京报书评周刊的记者采访了他。但在那之前,我们先来一起读一篇他书中的故事。

走水路
(“走水路”,即是静脉注射毒品的意思)
作者 | 林立青
来源 | 《做工的人》
阿钦吸毒。
或者说,他只能吸毒。
阿钦是铁工,全家以前都是包小铁皮屋的铁工包商,人们俗称为“铁栋”。
然而,从阿钦的父亲开始,他们家的招牌已经变成一片白,实际上也无法再做铁工了。自从内地的钢铁低价销回台后,台湾的铁工厂慢慢凋零。还有规模的,找上设计师和建筑师往下游抢食工作,市区内的新屋或装潢,全都被这样的形态抢走了。像阿钦家这样的小铁工厂,只能修修旧屋顶。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阿钦兄弟俩还过得去。当初父亲还在时,送他们去参加职训的结果是拥有焊工资格,虽然接不到案,但至少是专业师傅。
台湾的传统习俗,兄弟中有一人会留在家里,以免父母无人照顾。哥哥阿祈留在彰化,阿钦则到云林的大工业区和几个包商的临时工厂内,焊接铁管和白铁管。
焊工有职业生命的限制。首先是眼睛的老化。从事电焊的工人们,在几年内就必须戴上有色镜片。接着是夜盲。刚从业几天,就可以感受到眼睛和眼皮中间似乎有了沙;再过几年后,眼睛内就如同有结石般地难受。反复发作的眼炎也使得焊工必须在工作和休息之间取舍。但不做就没钱,阿祈就是这样,撑到一眼全瞎后,不得不退休。
接着是烂肺。电焊的工作是用高温将金属烧固。金属烧熔时的废气,会使肺部纤维化,焊工们在天冷时会喘不上气,就算带上支气管扩张剂也未必能撑住。常听说户外焊工昏眩晕倒,就是这个原因。这些有毒的气体,造成了工人的肺部受伤,甚至神经受损,又因为焊工的作业空间常必须蹲低爬高,保持同一姿势以做到焊点位置的完整,血液的不循环也使这些病变更为严重。焊工的脸部、手部也常常严重脱皮,像是蛇爬过一样,因为高温烧灼。
他们的老父亲走得很急,倒下去后,一周就在医院离世了,说是血液中毒,心肺功能全毁。那时候的台湾还不流行叶克膜(人工肺)插管。
阿钦是进了这个厂区后,开始用安(安非他命)的。这个厂区无法容许烟、酒、槟榔,进场前还要酒测,但吸毒难验。
他吸安后,工作如有神助。毒品最大的功效便是让人忘却酸麻痒闷热,所以他能够背负起完全符合安检的护具,并且毫无病痛、耐热耐重、做好做满、眼睛不痛,长蹲起立后再也没有晕眩。
吸毒的后遗症是变得只能专注于一点,这倒和阿钦的工作性质相符合。他的焊道又美又细,如同鱼鳞般地堆叠,相较于其他师傅在细节上的土渣,他的每一个焊点都干净美观,室内的氩焊更是焊出了淡紫色堆叠而出的弧形。这些成品被工厂内拍照后打印出来,作为验收的标准。厂区内所有人都说他是第一流的优秀师傅,焊道满铺,动作确实,并且几乎不用起来走动休息。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但这也引起了其他师傅的嫉妒。厂区内同做电焊的其他工人们,没有几人可以和阿钦有同样的技术,加上他不爱交际,人们也就在背后说他搞得大家都没好日子过。接着开始说他有吸毒,但这反而带来了保护──厂区内的工程师们认为这些纯属中伤,毕竟阿钦的工作成果比起其他人,实在好得太多。那些高学历的工程师总回:“你也去吸啊!”
这个厂区每年需要造册列管,而且对于人员、机械的管制极严,由于阿钦卡死了电焊工的活,所有进场的焊工都需要经过多种测验才能进场。现在这些资格比起阿钦当年考试时难上太多,有些不重要的部分,工厂甚至引进外劳帮忙焊。阿钦倒是对这些语言不大通的外劳很好,在他的观念里,有了这样的技术就不怕被欺负,工厂也愿意派个外劳在他身边。
他也是少数人证合一,又都在现场工作的师傅。有些机械故障或设备损坏的外地包商只能找他。重新找人对这些工程师来说无疑是大麻烦,并且还需要审核。阿钦的电焊机、发电机、氩焊机以及气体钢瓶,则是每年都通过认证,在厂区内作为劳检标准。甚至在扫具区内,他还有独立的小隔间和充电插座。如此一来,工厂的人方便找他,他也乐得不用把设备拿来拿去。
他把老家工厂的发票带在身上,厂区内的维修安装随时可开发票。另外,他帮人代工的每日工资是四千,夜间加班加倍,一个月约有十万上下的收入,足以应付他每个月一万二的药钱,加每周召妓一次。趁着星期天休息,开着小货车回彰化老家时,面对兄嫂,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也只能多给点钱来换取家里的宁静。
哥哥阿祈在彰化老家,原先生活还算过得去,毕竟两代累积下来的口碑声誉,使得他虽然没有每天上工,但修修屋顶、招牌每月都还能挣个四五万。
但阿祈的家里愈来愈不平静。他若是接了案,照顾老母亲的整个工作就落在妻子身上;但如果不接案,那更没有收入可言。阿钦明白,嫂嫂已经倦了。两个孩子都在外地读大学。婆婆已中风三年,老人的身体只有愈来愈差,让嫂嫂连对自己的丈夫都逐渐失去了耐心。每一次,阿钦只能回家看看妈妈后给钱,一阵推托之后,总是硬让大嫂收下,接着他回到工厂继续工作,很累的时候就买安来用。
母亲在中风后第四年离开了。没想到哥哥嫂嫂在丧礼办完后,因为老人家临终前的疥虫而互相指责,所有恶毒话语尽出,最后还互殴且闹起离婚。嫂嫂气得北上去找女儿,同时寄回离婚协议书。夫妻俩两地僵持,谁也不让谁。
这样过了一个月后,遇上台风季,阿祈受雇到庙旁的铁皮屋上焊屋板时,突然就没有任何声音地倒下了。紧急送医后,确定是中风──下半身、右手连同眼睛,都没了作用。等阿钦赶回去时,嫂子早已回到家,和儿女们照料起阿祈。阿钦还是只能塞钱,大嫂这时候却对他客气了起来。
他们全家都知道,这不可能好起来了。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阿祈身体的所有病痛,在此时全部爆发开来,只剩一只眼睛在白天有用。他有想过自杀,试过用枕头憋气,看能不能就这样死去,但每次还是忍不住叫出声音,拍打身边的妻。两只脚全废了,焊工长蹲使得阿祈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下半身,每次妻子为他换尿布时,他便开始说话糟蹋自己,也不想让儿女看到自己的样子。只是在病痛下,人的尊严一再被击倒,即使每天吞下止痛药,依然痛苦。他为小事骂起妻子,在夜里梦见疥虫而惊醒,却又因看见妻子无奈的眼神而更加痛苦。他的体重逐渐减轻,手脚也变得愈来愈细。
过年的时候,阿钦回家了,他想着应该包个大包给兄嫂,也该问问侄子、侄女的学费、杂费、生活费,是否能让他帮忙。
两兄弟总算有机会私下相谈一番,没有旁人。哥哥却趁着这时候,用仅存的左手握住阿钦的手,慢慢地,挤出了一个要求……左边眼睛还流着泪。
阿钦吓到了,两个月再没有回来过。
当他再回来时,和哥哥谈了更久。
哥哥的儿子准备退伍了,女儿再没几天就毕业了,妻子照顾了妈妈四年,他不要再拖磨家里下去。他说,趁着他劳保还在,寿险也还有缴的状况下,快点解决。
说着说着,两兄弟只能哭。
阿钦对哥哥说:“你再等我一下。”
隔周,嫂子要北上两天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阿钦回来照顾哥哥。他带着哥哥到宫庙逛逛,开车带他去看兄弟俩以前去过的地方。
隔天早上,他拿出了那一对针头和两个注射瓶。这总共花了八万。
哥哥笑着千谢万谢他,他却悲愤难抑地对着哥哥哭了起来。
四万元全部打入了哥哥的身体。兄弟俩手牵着手,阿祈不停祝福着弟弟,两兄弟抽抽搭搭地哭。接着,阿祈的声音慢慢变小。
他脸上挂着笑容,再没有反应了。
阿祈没有进医院,这是兄弟俩说好的。宫庙的人直接找来了葬仪社,妻女赶回家时,邻居们都说阿祈大有福报,是在家中离世的,想是他撑到女儿毕业了,无牵无挂地走,安详的面容像是活神仙般。
但阿钦违背了承诺。他没有如应允哥哥的那样收下自己该拿的那份遗产。他把房子全部让嫂子收租,哥哥的葬礼也全由他负担。
阿钦回到了厂区,继续工作。只有过年时,他才会回去发红包给侄子和侄女,也会去看看爸妈和哥哥。
他在祖坟里,留有一支针给自己。
林立青:为工人们写一本书,
即便什么都不会改变
采写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林立青,本名林亚靖,毕业于台湾东南科技大学进修部土木工程系。后从事工程监工十年。《做工的人》是他的第一部作品。
“
如果我们判断人的标准,是用刻苦,是用勤奋,是用力争上游的努力和对于生活的认真,去决定一个人的品格,那我们不可能看不出来她们值得拥有尊敬,我们又怎么能够允许这个社会将她们分别列上不同的标签呢?……如果我们的社会再对弱者加上标签,那无疑是将他们推往这个社会的更边缘处。而一些谣传和政治的挑拨,使得这些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女子们,更成为社会上几乎无声无息的人。你看不到她们的无助,更听不见那些哭声。
——林立青《台湾媳妇》
”
到工地做监工,对林立青来说,是一系列偶然的必然结果。
国中(初中)毕业后,因为成绩不理想,林立青不想继续读书了。老师和父母劝他去读五专,毕业后是大专生,学历比本科大学低一点。选专业时,电子、电机类的热门专业都被成绩更好的学生报满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台湾的城市建设趋缓,重大工程项目差不多已经结束,建筑行业不甚景气。选专业时,他不得已选了被人挑剩下的土木工程。2005年,林立青从五专毕业,之后又读了两年“二技”(两年制专科大学),服了兵役,在面包店烤过面包,搬运过包裹,在大卖场的生鲜部做工作人员,替卖场拆组过电脑。最终,七年的土木工程学习经历将他推向工地。
二十岁出头的毛头小子,在一群五六十岁的老师傅中间做起监工。在工地很苦,对身体损耗也大,林立青因为长时间双肩负重不均造成了“高低肩”。想去学做工,结果不管是贴瓷砖、抹墙壁还是刷油漆,都因为支气管炎和气喘作罢。直到《做工的人》出版,他还被高血压和头痛困扰。加上脚常闷在鞋子里导致的香港脚,长期被汗渍浸透、劳动期间过度摩擦产生“烧裆”,胯下和大腿内侧生癣,红肿瘙痒。他想过换一份工作,却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他在电话那头苦笑:“有点悲哀吧?”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虽是监工,但林立青并不像人们理所当然所想的那样,是个提着鞭子在工人后面敲打的狠角色,他更多把自己视作工人的一份子,一同劳作,一同玩乐。他也有身为监工的矛盾,有时被迫陷入“在施工进度和工人安危下挣扎求生”的困境;有时会说出“我永远不会配合警察办案抓外劳(外籍劳工)”之类的话。更多则是无可奈何:“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恐惧。”“我不知道他们的未来会变得怎样,也最好不要去想。”“一如现实,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林立青从未想过自己会写书出书,对每天和砖瓦泥墙打交道的他来说,这件事太过遥远了。
“读书读不好才去做工咧。”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网络上充斥着对做工的人的嘲讽和偏见。在大多数人眼中,最好的人生出路不外乎高考金榜题名、考上公务员,或是做企业家赚钱;而做工则是“底端的人”才会去做的事。连《商业周刊》这样的主流媒体也曾不无偏见地报道:“泥水工的周薪是10万块,比教授还多三倍”。
“根本不是这样的。”林立青气不过,和他们在网上你一句我一句地吵,吵到后来,他发现网络上的人对做工一无所知。“既然你不懂,我就写给你看,写到你懂。”他于是写工人如何同路边卖槟榔的姑娘搭讪(“亏槟榔”),写工地上去参加宫庙活动的年轻工人“八嘎囧”,写深受工人们喜爱、酒精浓度10%以上的药酒“保力达B”,写工地上不受人待见的拾荒者。为了“展现工人的真实状态”,他将一篇篇文章发到网上。其中流传颇广的是《做工的人》的开篇《工地“八嘎囧”时代》,专写那些爱去寺庙中跳祭祀舞的年轻工人,在别人眼中,他们不学无术、乏善可陈,林立青想为他们正名,“他们有信念和爱,代表一种可贵的青年亚文化”。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白天,他是工人师傅口中的“小林”,是位表情严肃的监工;夜晚,他变成“同情心没有泯灭的写作者”,把那些亲近的人、身边的事一一记录下来。
外籍劳工们薪酬低廉、待遇恶劣,被用背心后面的数字来称呼。户外的钢筋板模工常在烈日下负重切板,太阳底下晒过的钢筋和皮肤一接触,便起了水泡,晒伤、中暑是家常便饭。如遇大雨,做室外防水、洗石的师傅不得不在雨后收拾残局,抽水,与泥泞争斗。外墙砌砖的工人为了保证砖与砖之间水泥砂的黏性,需用水浇红砖,水流到人行道或水沟中,又被环保局开罚单。电焊工大多饱受眼疾的困扰,视力退化,金属烧熔时的废气会使肺部纤维化。水泥工因为长期和水泥、沙、喷固精接触,易患皮肤病。打墙工的手部肌肉关节损耗严重。还有举着广告牌推销楼盘的看板人,日薪最低五百台币(约合人民币107元),当天领工资还会扣掉一百,没有买水、上厕所的自由,大多是游民、身心障碍者、受伤的工人或年老体衰的人。

图片来源:《做工的人》; 摄影 / 赖小路
得知他在写一本关于他们的书,有师傅会特地找来,对他说:“你快来问我,我全部都告诉你。”然后从35年前第一天上工工资只有300台币讲起,“我听了快十年了,他们讲得不亦乐乎”。有的师傅不善言谈,不知从哪里讲起,却希望被问到,有问必答。
书出版后,有师傅找到林立青,问他为什么不写他,为什么写得这么少。还有的师傅得知自己借钱的故事是用化名写的,不无惋惜地碎碎念:“要是用本名就好了,用本名大家就知道我活得很辛苦,就知道我已经尽力了,是因为世道生活不容易,我才变成这样的。”
有个师傅每年都会关心他什么时候结婚,帮他求姻缘签,听说他要写书,就去寺庙里求了一个“文曲签”:“你出书卖得太好,把我多年求的姻缘签的神力都用光了,所以要求文曲,才会卖更多、赚更多钱。”师傅忘记了,林立青其实是基督徒。
工人们的反应让林立青惊讶,也让他发现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角度多么不一样。“所以我只能用诚实的文字、诚实的主观才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关注。你用太多虚假的客观,反而大家连看都不愿意看。”在他看来,文字和真实的力量恰恰就在这里——“有人的地方,文字就一定会有力量,它让我们重视,让我们聚焦,让我们看到应该要重新去理解、认识并且珍惜的情感、生命。”

《做工的人》繁体版书封
版本: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2017年2月
2017年2月,这本以工地工人为主角的书一经问世,便引发台湾读者们的强烈反响。虽然只是一本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处女作,却受到评论家纷纷盛赞,称他对工地工人的刻画“拓宽了台湾文学的向度……折射出阶级文化的厚度”;作家顾玉玲评价其“破墙而出”,她期待这本书的出现和林立青的书写能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的隔阂;金石堂“十大影响力”好书、Openbook好书奖“美好生活书”……一个个颇具声望的奖项也纷至沓来。
第一次尝试写作的林立青从没想过这本书会引发讨论,更没想过会得奖,他甚至“有点白目”地跑去问出版社:为什么这些奖没有一个是有奖金的?有人邀请他上台领奖,他会在颁奖当天特地跑去买新衣服,但上台领奖时还是难掩尴尬,“会全身发毛”。
荣誉称赞之外,批评声不断。有人质疑他的写作立场,认为他身为监工,无法真正平视工人们,夸大了苦难的成分。林立青了解这些质疑,他坦言自己有能力上的局限,“我不会比铁工更懂铁工,也不会比水电工更懂水电工,我没有办法突破这个极限”。他叹了口气,反问:“到底这样的文字应不应该写?能不能写?没有人可以回答。书写到底是要质疑这个人的存在、这个人的角度,还是书写本身?”
《做工的人》全书以“我”串联,毫不避讳主观的介入。用书的序言作者、作家房慧真的话说,就是“他身在其中,也得分担那悲恨怨怒的一部分”——林立青想明白了:“与其为了保持客观中立、政治正确,不如诚实地把我的局限、我的视野、甚至我的偏见都直接掺在一起”。
“你说一支笔、一本书、一个人能改变社会到什么程度,我是觉得太难了。可能问题会被人知道,但是真说改变,我不觉得自己有那个能量。我更不觉得自己有能力改变台湾对于劳工阶级的观点,那不可能,我们必须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
唯一的改变可能是,《做工的人》出版后的翌年,一位铁工师傅出版了《做铁工的人》,他原来不敢写,怕没市场,现在敢了。
《做工的人》的扉页,林立青郑重写下一行字:“如有雷同,请哀矜而勿喜。”
这话来自曾子:“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孟氏任命阳肤做典狱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曾子回答说,在上位的人离开了正道,百姓早就离心离德了。你如能弄清他们的状况,就应当怜悯他们,而不要自鸣得意。
林立青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即便从这些故事中看到真相,即便得知了做工的人的苦衷,也不要高兴。因为,“这并不值得高兴,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高兴”。



我是农民工,我在东莞

《我的诗篇》很动人,但它不是当代工人的史诗
▼
直接点击 关键词查看以往的精彩~
扫海报二维码,参与本周“我有嘉宾”线上沙龙~
或者点击阅读原文,到我们的微店看看呀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