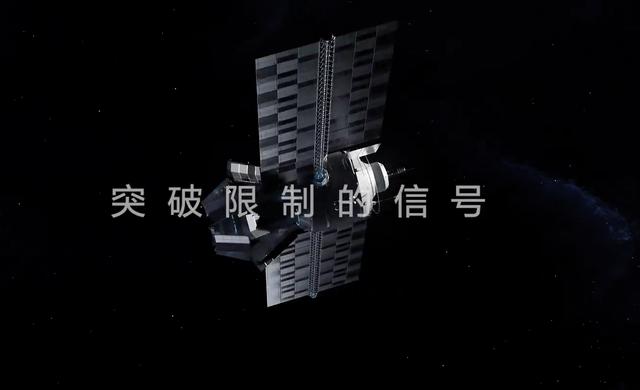电影沙丘到底讲的什么(沙丘与沙丘之前)
陈晃
在2021年,《沙丘》绝对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受关注的电影之一,其原著同时获得星云奖和雨果奖,对许多科幻作品都产生了影响,但这部科幻史诗被搬上银幕的过程却是困难重重。
佐杜洛夫斯基和大卫·林奇都曾经试图改编这个大部头原著,前者从未完成,后者则根本不愿意承认那是自己的作品。这次《沙丘》的导演维伦纽瓦,也是《银翼杀手2049》和《降临》的导演。在转型科幻片之后,维伦纽瓦受到的赞誉越来越多,这或许也是他能够接下《沙丘》电影改编的原因。

《沙丘》能受到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与原著对后世科幻作品产生的巨大影响也是分不开的。由于成书年代早,后世大量科幻与奇幻作品都受到了这部小说的影响,《星球大战》系列电影就直接沿用了《沙丘》中银河帝国的设定,《冰与火之歌》也对其中各个家族势力争权夺利的桥段有所借鉴。
《沙丘》构建的世界是在十几个世纪之后,人类已经可以进行便利的星际旅行、不需要电脑而只需大脑芯片就能进行复杂运算。而在这样高度发达的科技背景下,人类又回到了古老的封建帝国制度: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各大领主、家族之间互相争斗又互相制衡,处于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则长期生活在剥削与压迫之中。
故事围绕着一种叫“香料”的东西展开:在一个被黄沙填满的星球上,存在着大量“香料”,它是人类进行星际旅行的关键,各大势力争相抢夺对香料的开采权,而这个星球的原住民——弗雷曼人,只能在一个又一个殖民者的手下辗转。这与现实的对照十分明显——香料指的是石油,沙丘则暗示中东地区。
在哈肯尼家族管理沙丘和弗雷曼人多年后,皇帝突然指派厄崔迪家族为新殖民者,真实目的却是想借哈肯尼家族之手除去势力日益强大的厄崔迪家族。在两大家族的战争后,厄崔迪家族仅有族长的儿子和他的母亲存活了下来,他们进入沙丘,加入了弗雷曼人。
长达两个半小时的影片,讲述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个类似“王子复仇记”的简单故事。导演维伦纽瓦自己也在访谈中说过,“宏大景观与一个男孩的故事,他将慢慢卸下所有来源于家业遗产的负担,并在越来越深地进入这庞大场景之时,与他身份的另一面达成和解。”
影片男主角,由蒂莫西·柴勒梅德饰演的保罗,在有着厄崔迪家族唯一后继者身份的同时,也是弗雷曼人的救世主,担负着带领弗雷曼人走出殖民统治压迫的责任,但对于这座沙丘星球来说,他又是一个外来者。在如此复杂的身份之下,如何自洽、确定自我认同,也是故事线发现的一个重要部分。
但电影的主题与内涵要复杂得多。《沙丘》原著小说本身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科幻故事,而更多是一则关于生态主义、反垄断、反殖民的地缘政治寓言。在电影开头的旁白里,就已经道出了影片反殖民主义的主题之一:下一个压迫者又会是谁?
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一部《沙丘》似乎就像是星际旅行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但反殖民只是影片主题的一部分。帝国制度下的政治博弈、各大势力之间的利益冲突、水资源缺乏与沙漠化的环境问题、弗雷曼人的宗教信仰、个体在时代下的选择与挣扎,这些宏大的命题都被包裹在影片看似简单的故事线与华丽的画面之下,共同成就了这一部史诗级的作品。
但正如我们可以在后世许多作品中找到《沙丘》原著的影子,在如今这部《沙丘》电影中,也能看出许多对过往科幻电影的借鉴,尤其是维伦纽瓦代表作《银翼杀手2049》的前作,1982年《银翼杀手》的导演雷德利·斯科特。无论是美学还是主题,都明显表现出了这两代科幻导演的传承与发展。
从赛博朋克到废土美学
在《银翼杀手2049》与《降临》之后,《沙丘》又进一步成就了维伦纽瓦作为新一代最重要科幻导演的地位。在《银翼杀手2049》上映后,他就不断被拿来与雷德利·斯科特——1982年版《银翼杀手》的导演,同时也创作了《异形》《火星救援》等经典科幻电影——相比较。但单从美学上来看,这两位导演还是有着一定的区别。
对废土世界的呈现一直是维伦纽瓦的标志性电影美学。《降临》和《银翼杀手2049》都已极致地展现了这一点,在《沙丘》中,这种影像风格同样得到了延续:漫天的黄沙、奇诡的石城、晦暗的宇宙空间,都富有静默的冲击力甚至压迫感。而具有强烈工业设计感的飞船造型,又有几分对雷德利·斯科特赛博朋克美学风格的传承。
尽管“赛博朋克”这个词现在几乎已经被说滥了,但事实上,这一科幻作品流派的开创者正是1982年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它将传统科幻表达与黑色电影结合在一起,聚焦于人与技术、自然以及社会秩序的关系。在美学层面,赛博朋克则着力于描绘未来被异化的城市景观:在《银翼杀手》开篇的场景,黑暗的城市里充斥着巨幅的霓虹灯广告,高耸的烟囱喷出火焰遮蔽了天空,飞行器在巨大的金字塔形建筑旁漂浮而过。在我们熟悉的高楼与霓虹之间,又夹杂了飞行器、虚拟三维画面等具有未来感的元素,这种熟悉的陌生感正是赛博朋克美学的关键所在。
在《沙丘》中,作为“外星怪物”的沙虫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存在,所谓“香料”正是沙虫的排泄物,它是沙丘星球真正的主人,有着人类不能理解的力量。

沙虫
沙虫在整部电影中的镜头很少,它的出现便意味着死亡的威胁。沙虫的形象与现实中的沙虫相似,都是长长的蠕虫,区别在于其巨大的体型,和口中锋利的獠牙。这一形象有着强烈的性暗示意味:沙虫的身形仿若阳具,巨大且长满利齿的口又令人联想到阴道口与阴齿。
有着性意味的外星怪物形象,其实也是雷德利·斯科特的首创。在《异形》系列中,他与艺术家H·R·盖格合作,创造了异形这样一个恐怖又迷人的外星怪物。异形的头是阳具的形象,而异形的卵、和它在人类身上的寄生者“抱脸虫”形似女性生殖器,异形破腹而出的生产方式,又是对生殖恐惧的隐喻。
性暗示的怪物形象似乎总是有着难以名状的吸引力却又令人恐惧。《沙丘》并不是一部具有恐怖元素的电影,但其中宏大的星系、沙丘与渺小人类命运的对比,在许多科幻作品中被会被作为恐怖元素来运用。“人类最大的恐惧来源于未知”,这也是《沙丘》很大一部分魅力所在:神秘的沙丘星球、恐怖的怪物沙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所谓“真相”在背后隐身,又似乎显得已经不那么重要。
颠覆传统的政治与宗教叙事
上映后,大众对《沙丘》的评价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其中饱受诟病的一点便是其背景社会制度的落后,连建筑风格都充满了古典的历史感。尽管故事设定在一千年之后,整个星系的政治架构却仿若中世纪的欧洲。当部分观众急于批评这样的设定不合理时,却完全忽视了这种“不合理”正是作者本意的可能性:人类对于权力的渴望与现代民族国家的纷争,是否又会让我们在某一天回到如今看来落后腐朽的政治环境中?是否那样的制度反而能够更加稳固?
影片中大家族对弗雷曼人的殖民统治,也与欧洲白人对美洲、非洲原住民的殖民如出一辙:他们疯狂掠夺当地资源、奴役当地原住民,丝毫不关心原住民的生存状况和文化传统。当这些我们都早已熟知的历史又重新发生在未来的太空场景中,也传递出一种对于人性以及人类命运的悲怆。
《沙丘》中的各路政治势力,除了皇帝、领主、工会,还有一个特殊的组织: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与其他势力不同,这个组织还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男主角保罗的救世主身份便是由姐妹会一手操纵而成。
当保罗第一次抵达沙丘星球,围观的弗雷曼人们便朝着他发出了“天选之人”的呼喊。基督教文化对于弥赛亚(救世主)的执念深植于整个西方世界,将自己看作“待拯救之人”,而将一切希望寄托于来自“救世主”的虚无且未知的救赎。而《沙丘》虽然围绕着“选民与救世主”这样一个陈旧的主题展开,但本质上是对这一叙事的解构。“救世主”保罗之所以能成为“救世主”,完全不是因为他是“天选之人”,只是因为她的母亲,姐妹会的一员,把他从小培养成了救世主。
“救世主”的身份竟然不是来自于上帝的选择,而是被人培养出来的,这一设定本身就几乎已经构成了对传统基督教神学的亵渎。更不用说,当保罗意识到自己“被成为”救世主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排斥、被欺骗,丝毫没有对这一身份的神圣性的敬畏。在一番挣扎之后,他最终接受救世主身份的契机,却是自己的父亲被杀、家族覆灭这样个人化的原因。至于他对弗雷曼人的态度,影片中也没有太多具体的展现。
另一种对《沙丘》对批评认为,对于男主角的刻画仍然没有走出“白人男性救世主”的传统叙事,但保罗的区别在于,他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荧幕形象的羸弱的白人男性,他的“救世主”身份也来自于他的母亲——或者说是姐妹会这样的一个女性共同体。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构成了对“白人男性救世主”叙事的颠覆。
对于传统救世主叙事的反叛,维伦纽瓦早在《银翼杀手2049》中就已经有过类似的尝试。影片主角K原以为自己是人造人自然生产的后代,他的存在便是对人类伦理、人造人定义的撼动,而对于被人类奴役的人造人来说,K就是他们的“救世主”。而在经历了一系列寻找和追问之后,K最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复制品、一个复杂计划中的一枚棋子,这样剧烈的转变似乎让他失去了自我,但另一方面,作为人造人的K原本就不应当有自我,他只能迷失在神、人类、人造人、赛博体的身份认同之中。

《银翼杀手2049》剧照
追问信仰与身份认同的主题,实际上也是对雷德利·斯科特1982年那部《银翼杀手》的延续。在《银翼杀手》的设定里,人造人只有四年寿命,他们的使命就是为人类服务,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人类创造了人造人,人造人为人类服务,那么对于人造人来说,人类就是相当于“神”的存在。但人造人如何确定自己与人类的差别?如果他们拥有了自由意志,还与人有什么差别?人造人又如何确定自己的“自由意志”是不是人造的产物?
在随后的《异形》系列前传里,雷德利·斯科特对这一命题进行了更深的挖掘:创造人类的外星人被人类当作神,人类创造了人造人,人造人为了成为神又创造了异形。所谓的神性与人性相互冲突又相互交织,人类与人造人都在寻找自我、超越自我的路程上挣扎。
而《沙丘》直接用政治斗争消解崇高的宗教性,无疑是一种更加激进的手法。男主角保罗作为救世主的预言能力也无法带来什么改变,只是给他涂增痛苦。在原著中,即便到故事后半部分保罗逐渐接受自我身份之后,也始终苦恼于自己“救世主”的特殊性,也并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引领者的“圣父”角色出现,造就他特殊身份的母亲,后来所做的也只是像圣母一样,恳求他,即“圣子”展现神迹。整个看似“王子复仇记”的成长过程,实质只是各方势力相互博弈的牺牲品。
来自赛博朋克世界的隐忧
很多观众对《沙丘》不满的另一个点,则是在于其中的打斗场面,所有人使用冷兵器作战。原著中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科技已经足以开发制衡热兵器的护盾,人类为了避免高科技武器会产生的的致命威胁,不得不重新回到冷兵器战斗模式中。
关于“避免科技反噬人类”,电影中还有其他体现。两大家族的公爵和男爵身边都有一位会翻白眼的“门泰特”,他们是受过特殊训练的谋士,拥有近乎电脑运算程度的大脑,这样做也是为了避免人类对于人工智能的过度依赖。这就意味着在《沙丘》构建的这个世界中,或许曾经发生过高科技发展威胁到了人类生存的事件,如今这种冷兵器作战的模式也是一种对科技发展的警示。
因此,尽管《沙丘》中没有人工智能的痕迹,却暗含了对人工智能的反思。自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人造人与科技伦理就是其重要母题之一,两部《银翼杀手》便都是明确的针对人工智能与人类的故事。人造人可以说是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形态,这一跨度同时也带来了“技术人格化”/“人格技术化”的伦理问题。当“人”与“非人”的界限愈加模糊,人本身的存在也成为了一个疑问。
《银翼杀手2049》中,人类与人造人所生的孩子就对这一疑问提出了致命一击。人造人拥有人类的外表、人类的思维、人类的感情,如果连生育能力也拥有,那与人类还有什么区别?人类之所以是人类,到底是为什么?
对于长期浸淫于人类中心主义文化中的我们大部分人来说,这样的诘问似乎显得不可思议,但事实上人类的主体性也是在漫长历史中被缓慢建构出来的。古希腊时期已经有了“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样的命题,但中世纪的神权暴政和自然环境的束缚抑制了对人类主体性的进一步思考,直到德国古典学派的哲学家们确立了人类相对于客观自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对“理性”的推崇也进一步扩大了人类对外界的他者化。
后现代哲学家们开始用“存在论”对人本主义进行解构。仅仅因为我们自己是人类,便认为其他一切事物都是人类的“客体”,是否太过傲慢?如果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体”这一概念本身就不成立,那么人类的主体性也就无从谈起。在1982年版《银翼杀手》中,便利用人与宇宙、人与人造人的关系,探讨了主体客体二元对立的合理性,维伦纽瓦的《银翼杀手2049》则是用具有生育能力的人造人直接消解了人类作为主体的存在。
《沙丘》中的主客体则更加复杂。对于人类来说,宇宙与自然(神秘莫测的沙丘星球、沙虫)是客体;对于殖民者来说,原住民弗雷曼人也是客体;对于男主角保罗来说,他所面对的整个世界,包括涉及被迫卷入的政治斗争、被强行赋予的救世主身份,都是客体。共同特点是,这些主体在客体面前都显得迷茫无助。此外,布满沙丘的星球、匮乏的水资源所象征的生态问题,也是学界针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评中十分常见的面向之一,生态批评认为,正是人类的过度自我造成了普遍的生态危机。
虽然《沙丘》并不是一个赛博朋克电影,但其中表达的东西与赛博朋克并没有太大区别,都充满了对资本、权力、技术的未知走向的焦虑。巴尔萨摩认为:“技术被转变为技术商品,赛博空间并没有消弭种族、阶级和性别标志,而是复制了主导性的权力关系, 承袭了商品拜物教的现状。”这也是从雷德利·斯科特到维伦纽瓦两代科幻作者都致力于探讨的问题。在科技渗入生活、个体被符号化的可能的未来世界中,技术成为剥削手段的一部分,仍然处于资本垄断体系之下,用詹姆逊的话来说,赛博朋克只是一种“现在倾向的扩大”。
责任编辑:伍勤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