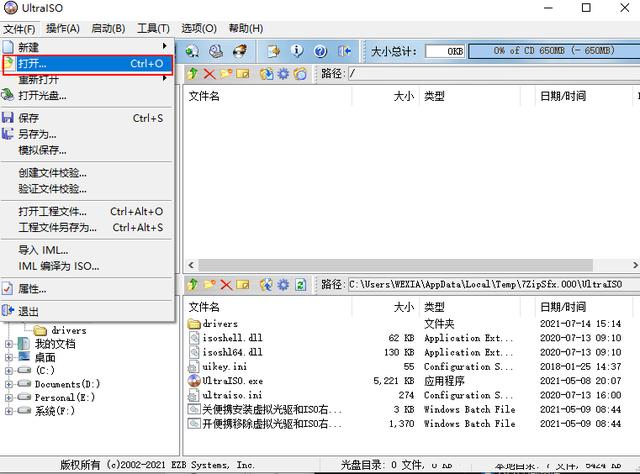突然被男朋友抛弃(接连被男友抛弃)

作家萧红
1935年,作家萧红与恋人萧军现身在一个文人朋友间的聚会上,萧红如往常般与朋友们友好交谈,但大家却从她的脸上察觉出了异常。
萧红的眼角及脸颊上都有明显的血痕淤青,泛着肿胀。
“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作家靳以不由关切地问道。
“没什么,没什么,是我不小心磕碰到的。”萧红的解释看似满不在乎,但眼神还是在不经意中流出几丝酸楚。
这些面部微表情没有逃过友人的目光,若只是磕碰,怎么伤处那么分散?众人不由将怀疑的眼神投向一旁的萧军。
已几杯酒下肚的萧军借着酒劲一脸放肆,言语无所顾忌:“有必要掩盖吗?你就说实话呀!”

萧军
萧红强撑着已有些尴尬的笑颜,试图继续搪塞:“没什么大碍,是我自己磕碰的。”
她一味地退让,换来的是丈夫萧军愈发地肆无忌惮:“我就直说了,她这伤就是我打的!怎么样?”
话语中没有半丝愧疚,倒是摆着一副自以为敢作敢当的架势。
友人们还未来得及迸出忿然不平的谴责声,萧军便自顾着扬长而去,聚会不欢而散。
萧红不得已追了出去,那追随的步伐中渗着些许卑微,每追逐一步,曾经似火的心也就凉却一分。
她不由得问自己,他还是那个救她于恶水深坑的“萧三郎”吗?他还是那个和她共患难、同啃一个馒头的爱人吗?好陌生。

萧红与萧军
时光飞逝,很快来到1940年,香港尖沙咀上空铅云压顶,冷风掺和其中,时而将暗云拂得散碎零落,时而癫狂地翻卷着云团,动荡不安的气息四散。
尖沙咀乐道街一处寓所内,萧红坐在写字桌前,身边早已没有了萧军,陪伴着她的只有一支笔和稿纸。
萧红伏案专注地写着文字,渴了啜一口苦茶,这本是一个作家的普通日常,可是这一段段文字几乎成了她人生的绝笔。
因为她距生命之烛燃尽已没有多远的距离了,她自己也有感知。
如今的萧红面容枯黄,无几丝血色,肺部总有止不住的剧烈咳嗽,还伴着难以消失的疼痛。
病痛的侵扰阻止不了萧红提笔书写文字,之前她已经写出了不少备受瞩目的作品,大多是关乎别人的人生。

萧红与作品《呼兰河传》
而这一次她书写的作品与自己有关,但却不是外人嘴舌间关于她的那些八卦绯闻。
外界对萧红从来都是褒贬不一,有人对她的作品不吝啬赞扬,称她为难得的文学才女,也有人同情她的悲苦人生。
但也有言语批驳她放浪无定性,比如连续两次弄出怀着前任的孩子和另外一个男人结婚的荒唐事,还痛批她自私,身为母亲却抛下孩子不管不顾。
而此刻的萧红并无意用文字去回击外界对她的种种批判,也未对自己做任何辩解。
她将笔触伸向了那方曾孕育过她的土地:遥远的故乡呼兰。
在生命将接近终点之时,她却忆起关于起点的那些点点滴滴。

萧红与母亲
位于黑龙江省呼兰河畔的呼兰县偏远古老,但形形色色的人或安逸、或躁动、或温和、或狂戾地活跃在这方土地上,为其注入了鲜活却沾染灰暗的复杂色彩。
萧红生于此,长于此,出生在地主家庭,从不缺吃穿,却无幸福可言。
她的父亲张廷举身体力行地证明了“地主”这类身份被人定义为反派是合理的。
张廷举在女儿萧红眼里,与其说是父亲,不如说是一个高高在上的掌权者,他是一家之主,是轴心,妻子、儿女、仆人都得围着他的指令转。

萧红雕塑
而冷漠专横是他的标签,即便对他自己的父亲也是如此。
他是一扇冰封的门,家人的心酸、悲苦他全拒之门外,与利益相关,他才会全盘定夺。
萧红九岁那年,母亲因霍乱感染病故,他在同年仅隔几月就能另娶新妻。
他喜怒无常,愤怒时将茶碗肆意就地暴摔,这是萧红记忆里永远的阴影。
萧红的童年从未感受过父亲半句温言暖语,斥责喝骂是父亲和她的交流方式,萧红若有些许反抗,父亲干脆拳脚相加。
而在冰天寒地里唯一的那束暖光来自于她的祖父,萧红本名张秀环,祖父为她更名为张迺莹,萧红则是她后来的笔名。
面对着专横的父亲,萧红更愿意和慈祥的祖父待在那空气清冽、溢满绿草芳花的小花园里,祖父亲切地教她种花、认识各种昆虫、植物。

童年时的萧红
祖父对萧红而言,就如那遮雨挡尘的大伞,当父亲要对她暴力相向时,祖父都会出言制止。
除了温暖的祖父,文学是她的精神食粮,在课本那一页页的文字里,萧红懂得了自由、平等,也了解了娜拉这样一名深陷苦难却勇于挣破牢笼的新女性。
在学堂里,萧红从不摆富家大小姐的架子,在别人都逃避做卫生、打扫教室时,她都是主动拿起扫帚、抹布扫地、擦窗。
而父亲却丝毫未被思想上进的萧红所感染,当过教育局长的他骨子里却觉得女孩家读书无用,找个家底硬的人家嫁了才是正理。
于是在萧红14岁时,其父便给她擅自定亲,对象是所谓门当户对的军阀世家少爷汪恩甲。

萧红童年时与祖父的塑像
深受自由主义思想熏陶的萧红不愿自己的人生及婚姻大事交给他人定夺,对这门亲事一直持反对态度。
因此与父亲原本僵冷的关系演变为火药与导火索这种一触就爆的激化场面。
幸好有祖父一直在旁调停,萧红才得以继续完成学业。
1928年,受爱国思潮影响,萧红参加了119反日护路游行示威活动,她主动担起了宣传员的职责。
不过萧红18岁那年,祖父去世,萧红悲痛难以言表,唯一温暖她心底的那道暖光也消失了。
面对着父亲的责难、逼婚,继母的冷漠,萧红只觉自己如身在冰窖里一般寒冷,孤独。
逆境中,小说里的人物娜拉浮在她脑海中,她要像娜拉那样去抗争,她要逃离。

萧红祖父
周遭一众人里只有表哥陆哲舜对她展开温暖笑颜,她面临众叛亲离,而他却站在了她身边,给了她冲破桎梏的精神力量。
于是他们一起逃离了,一起上学,一起高谈阔论,但由于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很快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钱,没有了物质基础,想完成学业,也就成了妄想。
陆哲舜本质上还是个经不起多大风霜的纨绔子弟,而萧红社会阅历尚浅,自给自足的能力严重欠缺、纵有满腔热忱,报负远大,在现实面前,一切只是虚妄。
陆哲舜很快低了头,决定返回家中,而萧红虽心有不甘,但也只能跟随表哥返回那个冰冷的家。
结果是陆哲舜很快取得了家族的原谅,但被禁止和萧红来往,而萧红则被严苛的父亲软禁在家中,饱受打骂。

萧红
在陷入黑暗深渊之时,幸得心慈的姑姑救助,萧红在拿到了不多的资助后,便再次逃脱。
在逃离期间,萧红仍不忘文字创作,多次向文学报刊投稿,也获得过微薄的稿费。
但她的生活依然是穷困落魄,颠沛流离,这时,曾被她拒婚的少爷汪恩甲居然出现在她眼前。
汪恩甲脸上看不出对萧红逃婚展现出的愤怒,只有温言暖语,还表示愿意给她经济上的支持。
萧红懂得好马不吃回头草的道理,可看看如今的自己,节衣缩食,依然穷困潦倒。
有些人在外遭遇沟沟坎坎,伤痕累累,但他们还有一个家,还有暖心的父母,那是他们可以停靠疗伤的港湾。
可萧红呢?所谓的家形同冰牢,她流落在外,不近人情的父亲从未找过她,更未伸手给她一丝援助。

萧红素描画像
若回去,等待她的将是恶言恶语、拳脚相加,她有家等于没家,此时的她太需要一个依靠了。
而对她释放暖意的只有眼前的汪恩甲,他的“诚意”逐渐消融了萧红对他的抵触之意,两人走到了一块儿。
但真的靠得住吗?萧红用单纯的想法去解读汪恩甲,却没想到汪恩甲一半为了报复,一半为了情欲的目的。
她被蒙蔽了,之后汪恩甲的哥哥现身,刻意搅乱她与汪恩甲的关系,汪恩甲却选择站在自己哥哥那边,让她尴尬,她依然看不清现实。
生活的窘迫、对情感的依赖让萧红降低了起码的判断力与智商,她选择与汪恩甲同居,越陷越深。
最后的结果是在他们欠了旅馆一大笔住宿费时,汪恩甲甩开她独自离去,再也没有回来。

萧红
他留给萧红的只有一个尚在她腹中的胎儿,他们并未成婚,这自然让萧红遭到不少白眼与非议。
萧红被房东扣留了,并被警告,如果不还清房钱,会将她卖到妓院抵债。
几乎身无分文的萧红既恐惧又无助,危急之时,突然想到了她曾投过稿的哈尔滨《国际协报》,便提笔向该报社写了一封求助信。
因为她告诉旅馆老板,收信人会帮着还钱,所以老板才答应让伙计帮她寄信。
报社编辑裴馨园收到求助信后,对此事高度关注,便委托为报社撰稿的作者萧军前往旅馆探望萧红。
萧军素来是个多情种,他早已成婚,但他初见萧红就对她产生了别样的情感。

萧红与萧军
尽管眼前的萧红身怀有孕,还带着些凄凉憔悴,但他却觉得此女有一种摄魂之美,霎时间,亲近之意不禁流出。
而身处窘境的萧红,难得见到有人对她投以欣赏、温暖的目光,自然觉得萧军尤为亲切。
尽管萧军以及报社也无法替萧红还清高额的住宿费,但此后,报社的编辑们及萧军时常来旅馆探望萧红,给她一些物质资助,还送她书刊与她交流文学。
对萧红来说,都是温暖的慰藉。
终于,逃跑的机会来了,那几日,疯狂的暴雨突袭哈尔滨城区,整个城市几乎半截都泡在了水里。
这本是个灾难,但却给了萧红获得自由的机会,旅馆的伙计告知萧红,老板自己出去避难了,她可以趁着现在赶紧走。

萧红
萧红离开旅馆之后,在第一时间便联系报社,报社编辑安排她暂住在报馆附近的寓所内。
临产期终于到了,在医院里,当护士抱着萧红生下的孩子站在她面前时,她不但没有一个母亲看到新生儿的喜悦,而是将头埋进被子里探出个手摇摆着:
“我没有能力养,我要不了这个孩子!”
萧红内心是无奈的,当时她几乎连自己都养不活。
但在外人看来,她确实薄情,她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是的,没有必要为萧红辩解。
只是谁又给萧红示范过父爱母爱及责任感呢?是她那暴戾薄情的父亲?或是对她不冷不热,在她九岁就早逝的母亲?
孩子最终被萧红托付给一户有诚意收养的人家。
没有了孩子,萧军与萧红越走越近,他将没有固定居所的萧红接到自己并不宽敞的简陋小屋里,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

萧红与萧军
由于收入来源不多,生活清贫,一开始几乎全靠萧军做家庭教师和借债生活。
虽然日子清苦,但同样热爱文学的两人志趣相投,在互相勉励下进行各自的文学创作,倒也生出许多欢乐。
这段时期也是萧红写作灵感全力迸发之时。
1933年,她以自己动荡和坎坷的少年时期为蓝本创作出了小说《弃儿》,当时给自己取的笔名为悄吟,一经发表,反响不小,也博得读者不少热泪。
当时也正是日军肆虐中华大地的黑暗时期,同为热血青年的萧红萧军认为身为中华儿女都应该义不容辞地肩负抗日的责任。
不能拿枪上战场,就用笔杆子来推动抗日热潮。
于是倾注了萧红萧军满腔热血的抗日题材作品《跋涉》问世,这时的两个人志向相合,互协互助,情侣关系和谐融洽。

萧红与萧军
《跋涉》一经出版,迅速在青年人中造成一股轰动热潮,受到文字激励的他们燃起了更高涨、更勇敢的反日情绪。
可正是《跋涉》这部散文小说险些给萧红、萧军招来杀身之祸。
因为《跋涉》中大部分文字都揭露了日伪的丑恶嘴脸,并反映了日军侵华后的社会黑暗,激发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
因此《跋涉》的作者萧红萧军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怀疑,欲对“二萧”进行迫害。
“二萧”对杀机已有察觉,便在中共地下党的掩护下从哈尔滨乘船逃到青岛,被爱国文人舒群、倪菁华夫妻接济。
到了异地,“二萧”依然笔耕不辍,进行着各自的文学创作。
萧军以“三郎”为笔名创作了小说《八月的乡村》,而萧红则开始创作透着浓浓乡土民风的小说《生死场》。

萧红的作品《生死场》
《生死场》生动描述了东北贫农的朴素与坚强,他们在那方寒冷的土地上倔强地扎挣着。
萧红笔下的众生们没有被刻意优雅化的行为和言语,尽显随性自然的风土味。
在《生死场》中,李青山、王婆、赵老三这样的人物都有明显的小脾性,还有些陋习,但面对入村侵略的日军,却不屈、不惧、不出卖同胞。
如此的性格转折,反倒更让读者为书中人物命运牵挂动容,热血沸腾。
这恰恰体现了作者萧红构思精妙的文字功底,这种不加雕琢的人物性格刻画反倒深刻地展露了人物的品格,丝毫不留模式化歌颂的痕迹。这一年,萧红才23岁。

鲁迅
而“二萧”合著的《跋涉》虽给她们带来了动荡飘摇的生活,但也使两人在文学界的地位更上一层楼,更受到了文学大师鲁迅的垂青。
早就仰慕鲁迅先生才华的萧红,在青岛时就以读者的身份给鲁迅写信,而鲁迅在众多回信中,偏对这个读者的文字印象深刻,特地给她回信。
在愉快的书信往来中,鲁迅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年轻女作者的作品。
鲁迅先生关注的不只是自己的作品发展,他对立志于走文学道路的有志青年从来都是不遗余力的去帮扶,于是在1934年向萧红、萧军发起了见面邀约。
收到邀约的萧红萧军欣喜不已,一方面可以和自己素来敬佩的文豪见面,一方面也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于是他们不假思索地从青岛搬迁至上海。

公咖咖啡馆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来到上海“内山书店”见到了敬仰已久的鲁迅先生。
之后鲁迅带上妻子许广平和小儿子将“二萧”约到一家名为“公咖”的咖啡馆交流。
面对两个文学晚辈,鲁迅丝毫没有摆出什么大架子,整个交流过程亲切畅快,见“二萧”生活拮据,还主动掏出一些钱资助二人,“二萧”对此感激不尽。
在鲁迅先生的指导下,萧红完成了小说《生死场》,并被出版。
生活逐渐好转,可萧红萧军的感情非但没有升温,两人之间的裂痕却逐渐扩大,很大一部分原因竟来自于鲁迅,这又是为何?

萧红
还得从萧红的作品《生死场》说起,当《生死场》与萧军创作的《八月的乡村》两部作品都交与鲁迅阅稿后,鲁迅对这两部作品都做了客观的评价,但评价大不相同。
对于萧军的《八月的乡村》,鲁迅委婉地表示,整个作品立意不错,但需要删改的地方很多。
而对于萧红的作品《生死场》,鲁迅毫不吝啬赞美,并为《生死场》作序,称其将北方人民对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表现得力透纸背。
而当时另一位极具影响力的文人胡风则为萧红写了后记。
而当《生死场》面临出版困难的时候,鲁迅慷慨解囊,使其顺利地出版。
一经发行,作品里渲染的精神力量感染了无数的读者,萧红也因此声名鹊起,在文学界的名气也超过了萧军。
尽管鲁迅也给《八月的乡村》作了序,也给予了作品一定的肯定,尽管萧红一直支持萧军的创作,但此时萧军性情中狭隘的一面展露了出来。
当初他对萧红报以好感爱意的时候,萧红是一个弱者、被救助者的身份,样样都不如他,却对他温柔体贴。

萧红作品
这种感觉让他舒适,便激起了他的保护欲。
而当萧红的文采俞发亮眼,光芒甚至盖过他时,他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性便暴露无遗,他不允许曾经的弱者比自己强。
于是烦躁、计较、抱怨逐渐统领了萧军的整个思维,时常与萧红一言不合,便放声争吵。
而萧红对此甘愿做一个承受者,她努力想磨合好两人之间的关系。
然而爱情如果变质,是她掌控不了的。
在感情上,萧军绝对是一个纵欲者。
在与萧红相识之前,他便有一个由家族撮合而成的妻子许淑凡,她对萧军贤惠顺从,还为他生了孩子,可却挡不住萧军见异思迁。
定力在萧军的感情世界里也是从来没有的,他可以心血来潮地爱上一个怀着别人孩子的孕妇,不惜抛妻弃儿。
但他又怎会甘心从今往后只对一个怀过别人孩子的女人忠贞呢?
而原则在萧军的感情里更是没有踪迹,面对自己好朋友的妻子,他都能不顾伦理地去追求。

萧红的肖像及作品
忍无可忍的萧红终于爆发了,与萧军展开唇舌之战,对他有失伦理道德的行为加以斥责。
后果就是,被萧军言语辱骂外加拳打脚踢,但他从来不在自己身上找错。
感情世界再次跌入阴冷的冰窖,悲凉无助之感笼罩着萧红。
这时只有他给她温暖的慰藉,这便是和她日渐熟悉的长辈鲁迅先生。

鲁迅
鲁迅在萧红眼里是导师,如明灯,照亮了她的写作之路。
又似父亲,温和宽厚又不失幽默,给从未感受过父爱的萧红缕缕暖意。
而他的慈祥又带有昔日祖父的影子。
鲁迅就是暗夜里的那道光,让萧红拼命想去追随。
在萧红陷入情感泥沼时,鲁迅邀请她去家中做客,看着鲁迅先生和他的伴侣许广平和善的笑容、和谐的家庭氛围,萧红备觉温暖。
此后便主动登门拜访鲁迅,和他交流文学。
鲁迅那时的身体已经严重告恙了,萧红会主动帮助许广平一起操持家务,做饭、包饺子给鲁迅吃,也给鲁迅增添了不少欢乐。

鲁迅
鲁迅同情萧红凄凉的身世与孤独的心境,对她从来都是广开大门,欢迎她前来做客。
在鲁迅家里,萧红感受到的是家庭的和谐温暖,而一回到和萧军的同住的小屋,却只有萧军的猜忌和变本加厉地斥责。
萧军甚至对外散布萧红对鲁迅有私情的谣言。
而鲁迅眼见萧红陷于痛苦纠纷中,便劝她抽脱出来,让她去日本散心,并写信叮嘱在日本的好友照顾她。

鲁迅画像
但令人悲痛的是,在萧红去往日本几个月后,鲁迅先生在同年十月因病去世。
听闻噩耗,远在海外的萧红悲痛不已,她在凝聚着满满缅怀之意的《海外的悲悼》中对鲁迅先生表达了沉痛地哀思。
1937年元月,萧红从日本返回上海后,立刻前往公墓拜祭鲁迅,对此,鲁迅的伴侣许广平深表感激。

萧红悼念鲁迅
虽然在许广平后来的回忆录里,谈及萧红前去日本时,说了一句,“她终于走了”,似乎在暗示对萧红当初过于频繁地造访、打扰鲁迅休息表示不满。
但萧红得当的言谈举止还是让许广平对她颇有好感,再见面时,还是和谐友好地相处。
从萧红在鲁迅去世后写给萧军的信里,也看得出萧红对许广平的情谊之深。

萧红写给萧军的信
生活还得继续,但萧军的偏执和滥情仍然不改,在无数次卑微地妥协后,萧红终于心灰意冷,决定与萧军分道扬镳。
而萧红永远不能割舍的是文学创作,无论人生之船怎样颠簸,她都不会放下手中的笔,也不会放下火热的抗日情怀。

端木蕻良、萧军、萧红
1937年,萧红前往武汉做抗战宣传,邂逅了青年作家端木蕻良。
如果说萧军是奔腾却会灼伤人的烈火,那么端木蕻良则像一条静谧的河流,性格谦和。
他对萧红的文学作品很感兴趣,也表达了发自内心的欣赏,在与萧红展开文学探讨时也十分投机。
之前感情的破裂,慈父般的导师鲁迅的离世,让萧红伤痕累累,此刻的她太需要感情抚慰了。
而眼前的端木蕻良让她感觉尤为亲切,所以当端木蕻良向她表达爱意时,她欣然接受了。
可正当萧红准备展开一段新的感情生活时,她却发现自己已经怀上了萧军的孩子。

萧红与端木蕻良
当萧红为此愁绪万千时,大度的端木蕻良决定给萧红一个婚礼,这更让萧红感激涕零。
历经了前两次失败的感情,萧红更加呵护与端木的这段婚姻,婚后不久,日军将魔爪又伸向了武汉。
在罪恶的炮弹轰击武汉时,为了不让丈夫端木和自己同陷苦难,萧红毅然让端木先踏上前往重庆的船只,而自己则大着肚子留在了武汉。
不久,她与萧军的孩子出世,可由于战乱,医疗环境恶劣,孩子刚出生不久便不幸夭折。
等到再与端木会合时,两人决定前往香港,但饱经生活之苦、身体抵抗力极差的萧红此时已患上肺部重疾。
而身为丈夫的端木此时事务繁忙,无暇整日陪在萧红身边,所以萧红大多时候还是形单影只。

《呼兰河传》
在病痛中,文字成了萧红唯一的精神伴侣,她将这一生的爱、恨、酸楚全倾洒在回忆式散文小说《呼兰河传》中。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这段清爽却又哀怨的文字,散发出萧红对人生既向往又无奈的愁绪。
《呼兰河传》完稿于1940年底,而在萧红病情不断恶化,生命之烛即将燃尽之时,病魔依然挡不住她对文学的热爱。
在1941年底,拖着被病魔侵蚀的身体,萧红仍然拿着笔书写她人生最后一部小说《马伯乐》。
而他的丈夫端木在萧红距生命终点还有十天的时候,才忙完公务来到她身边。
此时的香港正遭日军无情地轰炸,整个医疗环境极差。

萧红
之前一直陪伴守候萧红的是端木委托的青年作家骆宾基,他向来欣赏萧红的文字,对萧红尊重而钦慕。
萧红为了表示对他的感激,决定将《呼兰河传》的版权赠与骆宾基。
而萧红丈夫端木虽然没有对萧红有太多的陪伴,但却对当时医生不负责任的手术方案提出质疑。
医生硬说萧红生了喉瘤,要切割掉,但端木表示,肺结核病人动了手术,伤口无法愈合,但萧红选择遵照医生决定。
但最终医生的决定被证实为误诊,萧红于1942年1月永远闭上了眼睛。
作家萧红的一生只有短短的30年,她的人生,是酸楚的、悲凉的,但也是灿烂的,蕴藏在她文字中的生命源泉永不枯竭。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