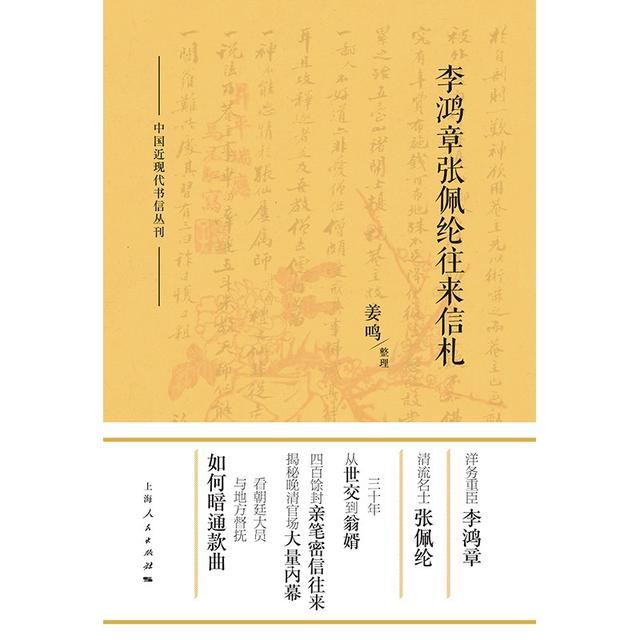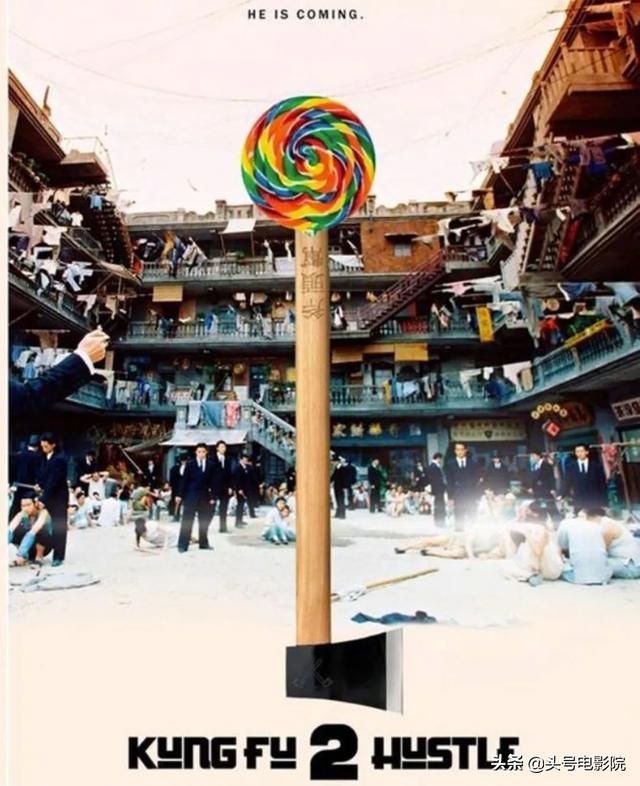五行木图标(村庄五行木)
村庄五行:木

我最早接触过的木,怕是小板凳了,再后来依次是烧火棍,柴禾等等,但记忆最早最深的就是那黑色的让人望而生畏的棺材架了。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自已有多大,我家在路边上住,出了门就是一条马路,从我家往村口走有七八户人家。我还记得就在第六户人家门口,我从村口往回走,那是个傍晚,我看到那户人家门口放着一个大大的木架子,上面亮着彩色的灯,有很多人在那户人家出出进进,看上去很热闹,我不知道热闹的背后是因为有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也不知道那个大大的黑色架子是做什么用的,我好奇的是上面有着彩色的灯,分几个地方挂着,挺别致,反正以前没看到过。
在村庄,树是最多的,比鸡多,比狗多,甚至比人还要多出很多来。房前屋后都是树,院子当中也是树,路边上,地边上也都是树,最多的就是杨树,因为是材料,盖房可做大梁。在我的记忆里,能叫得上名字的有核桃树,桑树,拐枣树,柿子树,杏树,枣树,梨树,樱桃树,皂角树等。为了给蚕摘桑叶,我曾和小伙伴们爬上村子里最粗大的那棵桑树。我也从核桃树上掉下来过,不算高,但着实把人吓到了,脸擦破了皮,火辣辣的烧得疼。还曾在弯脖子的拐枣树下用麻绳绑过一架简易的秋千,闭着眼睛坐在上面晃悠,一坐一个下午,不曾想过时间的流逝。
少年的我,似乎总站在邻居家院子里的那棵杏树下,那是杏子即将成熟的季节,满树都是摇头晃脑的杏子,馋的我直流口水,但熟透黄澄澄的却没有几个,我在寻找着先黄的个别杏子。我仰着头,盯着树上的每一颗杏子,那些刚带上点黄色的杏子,很快就被我找到,我找来长长的竹竿,将它敲打下来,杏子掉落下来的那一瞬间,我扔掉手中的竹竿,三步并作两步冲到跟前,蹲下身子,把它捡起来,然后洗也不洗,直接在胳膊上擦拭几下,就放进了嘴里,那酸酸的味道至今让人回味无穷。
在天晴时,阳光斑驳的照在树上,我站在树下仰望,总能透过枝叶的缝隙与阳光对接。那是温暖的日子,阳光也在对着我笑。在雨天,我光着脚丫子,戴着草帽,披着塑料纸站在树下,尽管有雨水冷不丁滴下来,打在我的脸上,或者一下子钻进脖子里,冰凉的让我颤栗几下,但我还是坚持寻找。也不知道我在这棵杏树下站立了多少时间,回想起来,那大抵是一段时光的缩影。
每个少年都有一个侠客梦,年少时的我,曾经无数次的找来木板,用砍刀割来劈去的,想要把它做成一把剑的模样,但大都没有做好过,总是半途而废,偶尔做成的一把,样子也是极其古怪,即便如此,我照样把它挂在腰间,大摇大摆的走出门去,好像自已真的成了一名侠客。也和小伙伴们在村庄里打斗,嘴里喊得噼里啪啦,但木剑却沉闷着,直到玩成两个半截,才扔到一边,侠客梦也暂时搁浅。
每个少年都有一个陀螺梦,砍砍削削,细心的装点,陀螺是旋转着的梦,是不想停止的梦。在麦场上,鞭子不停地抽打着,陀螺飞快的旋转着,转着转着,少年扔掉手中的鞭子,成为了青年,中年;转着转着,麦场上人去楼空,曾经的少年远走他乡;转着转着,围观的长者已消失不见,长眠在这片苍凉的黄土地下。
要问村庄人摸过最多的木是什么,很多人想不到,其实是顶门棍。傍晚关门,支根顶门棍,清早起来,拿去顶门棍,顶门棍虽说只是一根粗大结实点的普通棍子,但用来顶门,它的名字和意义就不一般了,它是一家人的安稳之托。一根顶门棍,可以让人在夜里睡得踏实。虽然,在村庄每一户人家里,顶门棍总是立在门后,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锄头把断在我手里那天,我才清晰的发觉锄头把是木的,并没有想像中那么坚不可摧,而此前,我一直以为一把锄头可以用一辈子的。锄头把断了的同时,我也知道我已经长大,变得勇猛有力。当我把架子车飞快的推进巷道,架子车的左轮子被巷道里突出的半块石头垫起,我被突如其来的方向改变重重摔在了地上,半天都没有爬起来。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后,我拉开架子车,几步窜进家门,从院子里提出一把锄头,抡圆了,使出平生最大的力气,狠狠的朝着那露在外面的半个石头砸去,那半块石头生生的被我砸开了花。就在同时,手臂般粗细的锄把从中间拦腰震断,一分为二,我怔怔的站在原地,手里握着断掉的半根锄把,突然间觉得鼻子一热,鼻血滴答滴答流下来……那个时候的我,是无知的,是愚昧的,但有着一颗比石头还坚硬的心,所以弱小的我,可以拼尽全身力气去粉碎一块挡着我路的石头,也许无知即无畏。
我近距离的看到木匠作业,是在那间老厨房里。木匠在不分昼夜的赶制一个大木匣子,厚重的木板似乎预示着事件的沉重。木匠用刨子推一下,就刨出一朵打着卷的木花,一朵又一朵,纷纷散落在地上,生命似乎可以像木屑一样轻薄,无足轻重。在刻着岁月纹理的木板上,木匠用墨线打出直直的线条,从这头到那头,随着刺耳的电锯声响起,木板一分为二,从线条处完全分离。木匠把木板重新拼凑在一起,装订,修整,粘合,大木匣子做好了,外加一个带着拱形的盖子,里面有足够能躺下去一个大人的位置。
静守在一旁的我,或坐,或立,或蹲,一直在边上看着,我不知道做它的意义何在。后来,木匠拿来一个小铁桶,还有一把刷子,小铁桶里是黑色的粘稠液体。木匠用刷子蘸着黑色的液体,开始涂染那个大木匣子,从头到尾,从上往下,一点缝隙也不放过,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里就开始不安起来,那和乌鸦身子一般无二的黑,让人心生厌恶。再后来,木匠还用其它花花绿绿的颜料给大木匣子画上一些枝枝蔓蔓的怪东西,似物非物,让人望而生畏,不寒而颤,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不敢再站在边上看了,我离得远远的。
最终知晓了,那个大木匣子是用来装人的,我的祖母被装了进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总是疑惑,不知道祖母一个人在里面会不会觉得闷。棺材这个刺耳的字眼在以后的许多年里,一直刺痛着我的耳膜,因为我知道了,棺材是生命的终止符。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