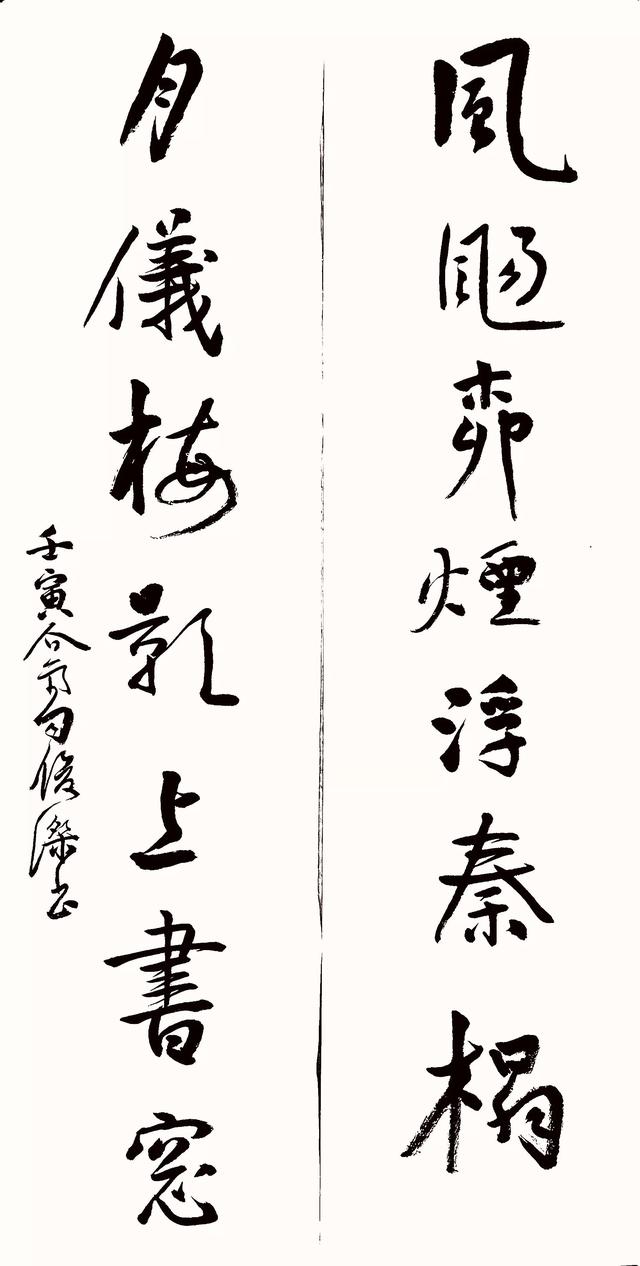苏州人早餐吃面吗(怎么就这么爱吃面呢)

作者:我方特邀作者杨基宁
立夏以后,又到了该吃枫镇大面的时节了。
这个因为《舌尖上的中国》大火特火的苏式汤面,如今已成为“苏州最红汤面”。很多文艺青年,来苏州都要吃上一碗。尽管很红,但千万记得,它其实是苏式面里不多的白汤面。以前,苏州人讲究“不时不食”,这枫镇大面一般只有夏天才有的吃,如今很多面馆已经不分时令,每季都有枫镇大面。但从口味上来说,总感觉加了酒酿的面汤,只有大热天吃才过瘾才有感觉。
如果要选择一样美食代表苏州,那唯有苏式汤面。苏州谚语说“面要头汤、浴要浑汤”。意思是吃面要趁早,用精心熬煮的第一锅汤下出来的头汤面汤色最清、味道最鲜。由此可见老苏州的头汤面是何等重要。
对于北方人来说,总觉得吃米的南方人对面食不太感冒,但对于鱼米之乡的苏州,这却一个极大的误解。长久以来,产米的苏州人却把“吃面”当成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传承——爷爷带着儿子吃面,儿子带着孙子吃面,口味传承,习惯传承。直至今天,当你旅行到苏州,看到满大街各种“XX兴”招牌的面馆,以及面馆里几十乃至上百种面的选择,你就会知道这座城市对面的执念有多深?
那么问题来了——苏州人,怎么这么爱吃面呢?
一、最早的挂面出自苏州
虽然总有“南人饭米,北人饭面”的说法,而苏州人对本地的一碗面情有独钟。而这一碗面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
据南宋庄季裕在《鸡肋编》中说:“建炎(1127-1130)之后,江、浙、湘、湖、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
靖康之耻后,金兵入侵逼得宋室南迁。使得江南地区人口急剧增多,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必然会让江南地域的文化发生巨大变化。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一日三餐的改变,大量“饭面”的北人到来,使得面粉需求变得空前高涨,以至于“绍兴(1131-1162)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意思就是南宋初年时,由于麦子市场需求量大增,而江南农民种麦子的利润竟是种水稻的数倍。同时,官府也出台了鼓励政策“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

这么多北方人来到这里,“吃面”的习惯自然也来了,所以有了类似“无锡包子苏州面”的说法,往上溯源都是南宋年间。
而当时凡是面食均称之为饼,《靖康缃素杂记》就记载 : “几以面为食具者,皆谓之饼 :故火烧而食者,呼为烧饼;水渝而食者,呼为汤饼;笼蒸而食者,呼为蒸饼。”而汤饼又叫煮饼,宋代本就处于向面条的转型中,汤饼后的索饼,也就是面条的“祖先”。
从此,苏州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方为糕,圆为团,扁为饼,尖为粽”之外,又多出了一种“条为面”的新食法。

而到了南宋中期,目前记载的最早的挂面“药棋面”已是天下闻名,而它是平江府(苏州)昆山县的特产。成书于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的《玉峰志》中就有这样记载:“药棋面,细仅一分,其薄如纸,可为远方馈,虽都人、朝贵亦争致之。”将面条脱水成干,耐保存,易携带,能运往当时的都城杭州,寻常的食物已被改良成馈赠佳品,成为贵族官僚们喜爱的馈赠之物,说明它还具备了保健食品的疗效,这既是苏州人对面食发展的贡献,也是苏州人精心于食馔的一个例证。
二、两三百年的融会贯通
可苏州毕竟是种米的嘛,只靠特殊年代的短时间移民,能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习俗吗?
当然不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从明清年代起,苏州经济地位的改变。这个唐宋时期的“江南小城”,随着中国经济版图的变迁,突然华丽转身,一跃而起成为中国东南的商贸重镇。
比如明朝弘治年间,朝鲜官员遭海难漂流中国,经明朝官府救助,沿大运河北上回国,后写成了《漂海录》,其中就有他对于苏州的繁华记录,而崔溥经过的自胥门经金门、阊门直至枫桥一线运河流经处,均是苏州的重要商业区。崔溥行后不久,唐伯虎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阊门即事》,诗中云:“世间乐土是吴中,中有阊门又擅雄;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若使画师描作画,画师应道画难工。”
商业的发展,让苏州从明朝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苏州成为江南经济中心的同时,又成了一个人口流动的中心。天南海北的商客云集在此地,“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都大幅度增加,随之激活了城市日用品的消费,饮食业也就火速发展起来。

然后各地人员汇集,苏州流动人口中商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天南海北的商人往这里凑,带来的都是他们家乡的货物,从手工业原料到吃穿用度所需各种商品无不具备,几乎当时各个行业都有明确的外地商帮经营。例如蜡烛业多为绍兴人开设,煤炭铺行多为宁绍商人开设,烟店则多为河南、福建商人开设,晋商则多经营钱业,经营粮食业的多为湖南商人。酱坊一业,则共有徽苏宁绍四帮,共计86家……
另外,各种会馆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出来,苏州的会馆最早创于万历年间,到乾隆时为最高峰,这也充分反映了苏州的工商业日趋繁荣的轨迹。据碑刻资料的统计,明清时期苏州的会馆,就增加到近百所。
这么多人,南来北往地在此汇集,吃饭当然是个大问题,餐饮口味很重要,特别是会馆和会馆周边,往往就能找到最有那个地方特点的美食。这就好比前些年北京驻京办没有裁撤之前,北京老饕们总爱去各地驻京办寻找美食一个道理。换句话说,苏州作为明清两代最重要的移民城市,在这两三百年的融会贯通中,各地的方言和滋味,渐渐都融入在这一碗包罗万象却汤清气正的“苏式面”中。
三、乾隆曾是苏式面的最佳推广人
苏州碑刻博物馆里,有一块光绪三十年(1904)的《苏州面馆业各店捐输碑》,让面馆从利润中,每千文捐一文,作为公所公盛之用。
刻录在碑上的面馆有八十八家,捐了一百五十文以上者有三十余家:观正兴、松鹤楼、正元馆、义昌福、陆正兴、张锦记……这些名字很多依旧在苏州的大街上抬头就能看到,当然能上这块碑的,基本上都是相对较大的面馆,估计很多小面馆还排不上座次。

吃面,终于成了在苏州生活的标配。
其实,当年的“苏州一碗面”,影响已远不止在姑苏。
在民国十七年(1928)出版的《杭俗遗风》中记录了不少在清道光、同治年间杭州旧俗。而在“苏州馆”的条目下就清楚写道:“苏州馆店所卖之面,细而且软。有火鸡、三鲜、焖肉、羊肉臊子、卤子等,每碗廿一、廿八、三四十文不等,惟炒面每大盘八十四文,亦卖各小吃并酒、点心、春饼等,均全此为荤面店。尤有素面店,专卖清汤素面与菜花拗面,六八文起价,如上斤则用铜锅,名‘铜锅大面’,再三四月间,添卖五香鳝鱼,小菜面汤亦各二文。”这至少能说明,也就是说早在一百五十多年前,苏州的一碗面早已在江南打开市场了。
当然苏州面的最重要的推广大使,大概是乾隆皇帝,在苏州的书场里听评弹,你大概时常听到他,吃完一碗面,心满意足打个饱嗝。据说大名鼎鼎的“奥灶面”,是他和一个有点耳背的昆山好婆误打误撞的结果,“鏖糟”二字本是苏州土语,意思是“龌龊的很,脏兮兮不干净”。但乾隆爷偏偏把它理解为“奥灶——奥妙在灶头”,一下子名扬海内。

而文章一开头的枫镇大面,在评弹里又是吃货乾隆的功劳,他微服来到枫桥镇,又累又饿,敲开一家小面馆的门。谁知这店主是烂赌鬼,无心经营,店里没啥吃的。于是,他随手抓来食材和调料,乱烧一顿:没有骨汤就用剩下的鳝鱼骨熬汤,没有酒去腥,临时抓起酒酿,没有面浇头,拎起一块还没上卤的白肉,凑出一碗汤面来。结果,天子不出意外的大大点赞,于是这碗在枫桥镇的面日后名声大震,还好没叫“赌鬼面”。
不过,乾隆爷在苏州各类奇闻异事颇多,多半故事类型都是苏州寻常之物,皇帝偶然碰到后惊为天物,大加赞赏。究竟是皇帝老儿见识太浅,还是天子品位独特,站位高才能发现普通人发现不了的美?苏州百姓大概都认为是前者:皇帝老儿其实也蛮可怜的,深宫禁地中实在是吃不着什么好东西。
当然这种自信,源自于明清两代,苏州各行各业的手工业产品都是领风气之先,所谓苏作更是精致优雅的代名词。而苏州面,也如明清的谚语“苏州样,广州匠”,要的就是精细。周星驰《食神》里那句“一碗杂烩饭也要用心做”,放在一碗苏州面里,实在是最普通的要求。所以,一碗苏式汤面,见证的不止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变迁,更是苏州人生活和性格的缩影:精致内敛,不张扬,看似简单平常,却底蕴深厚。

吃这样一碗面,何尝不能吃出多少人生真谛!
参考资料:老凡《苏州人吃面.面话》、苏州烟雨《汤汤水水一碗面》、肖禹《明清时期苏州多外地货》、陈学文《明清时期的苏州商业》、范金民《朝鲜人眼中的运河风情》
北齐的支柱——晋阳城
人不自助,天难助,后周世宗柴荣:莫欺少年穷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