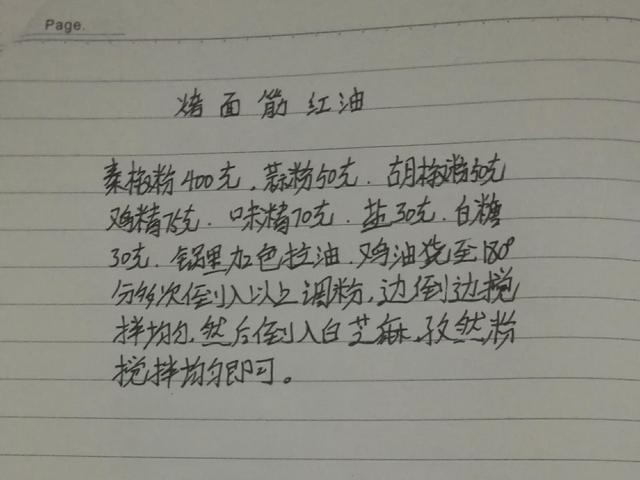横向写作问题(往下沉的写作姿态)

《当梨子挂满山崖》
花山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出版
优秀的散文作品应当是一种有难度的写作——这是近年来一些有眼光且有成就的散文家,在创作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共识。刘江滨是这个共识群体的重要一员。前些年,他在评论散文家彭程有关创作难度的倡导与实验时,曾有过由点及面的引申性阐发:“我认为追求‘有难度的写作’应该成为引起散文界警觉的一个共识,或者散文写作者寻求的一个方向目标……追求‘难度’,是自设门槛,唯如此,才有创新和超越。”这是属于刘江滨的对散文创作难度的理解与认知,也是他自己在创作中的坚守和追求。
高端的散文写作需要自觉的“难度”意识。然而,散文的难度具体表现在哪里?或者说散文家向着难度的攀登应该从何处入手?却仍是一个需要探究和讨论的问题。从近年来散文创作发展变化的态势看,一些散文家似乎将创作的难度更多看成一种手段,一种技巧,一种叙事策略或修辞方式。而沿着这样的路径进行“难度”的经营,或许可以增加散文行文的“摇曳”与“繁复”,难免要付出弱化乃至遮蔽作为散文之魂魄的主体表达的代价,甚至有可能造成散文文体特质的模糊与紊乱,直至消解散文之所以是散文的依据和边界。相比之下,刘江滨对散文难度的追求呈现另一番情景——作家没有在文本形式和技巧层面过多用力,而是让创作重心向内转、往下沉,化作对精神自我的发掘、提炼和提升,进而以不断丰盈强大的自我挑战散文的“难度”,推动艺术的前行。这点在他的散文集《当梨子挂满山崖》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翻开这部散文集,作家的散文世界里几乎没有什么冷僻场景和稀奇物象,取而代之的是每见于普通人生命经验的世相撷取、心灵沉吟、人情物理、血脉乡愁等。只是我们一旦同这些寻常内容心目对接,随之而来的却正是所谓“熟悉的陌生化”,即在作家并不新鲜的“能指”中蓦然感受到“所指”的颖异与别样。《那乡音里的乡愁》写出方言口语的生动性与差异性,将之纳入文学艺术和地域文化的范畴。倡导在推广普通话时,应当自觉地保护方言口语,以利于文化发展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春天的风》《夏天的雨》《秋天的月》《冬天的雪》一组文字,写的都是人们几近熟视无睹的景物。然而,作家偏偏拥有“画到生时是熟时”的笔墨,于是,大自然的生动气象,或呈现新的禀赋、新的意境,或平添新的哲理、新的旨趣,以至让忙碌的现代人禁不住会有“千江有水千江月”的感叹。
如果说以上作品的“推陈出新”得益于作家对审美对象的深入体察和敏锐发现,那么还有一些作品的平中见奇,靠的是作家对客观事物的动态描写和对外部环境的历史把握。《农家院里的瓮》《家住石家庄》《那一簇温暖的烟火》《坐飞机》《坐火车》等作品乍一看来,只是书写了发生在作家身边的事物更替与环境变迁,更多属于小细节、短镜头,再加品味即可发现,其中分明融入了时代的跫音与社会的投影,是一种个体视线里的历史记叙。而这种由“小切口”走向“大历史”的构思与手法,正是作家强大主体意识与丰足创作实力的自然外化。
刘江滨视野开阔,阅读广泛,文心绵密,这使得其走笔落墨,不但洋溢着浓郁的书卷气,而且有让人豁然开朗的“审智”特点。《桃之夭夭》以桃花为“文眼”,让神思和笔墨在古典文学长河间穿行,一时间“总把新桃换旧符”的习俗、“人面桃花相映红”的故事、“桃红又见一年春”的畅想纷至沓来,其结果不仅生动传播了与桃相关的知识,而且从较深的层面切入传统文化的特殊蕴涵。《时间之笔》围绕河北境内的沙丘平台遗址展开叙事,依次打捞出商纣王“酒池肉林”、赵武灵王“沙丘宫变”和秦始皇驾崩沙丘的历史往事。而作家之所以钩沉历史,并非单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旨在以历史为镜鉴、为昭示。《深夜绽放的花》书香浮动、意脉别裁,作品从“我”的失眠说开去,自然地引出古时骚人墨客的相关诗作,以烘托失眠之苦。接下来,作家笔调为之一转,坦言失眠带给自己神秘的好处——大脑在朦朦胧胧、似睡非睡的状态中,做天马行空般的高速运转,于是,奇思妙想、清词丽句在“前意识”的客厅里翩然起舞。这时,前人所谓“梦中得句”的说法有了新的诠释。
(作者:古 耜,系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