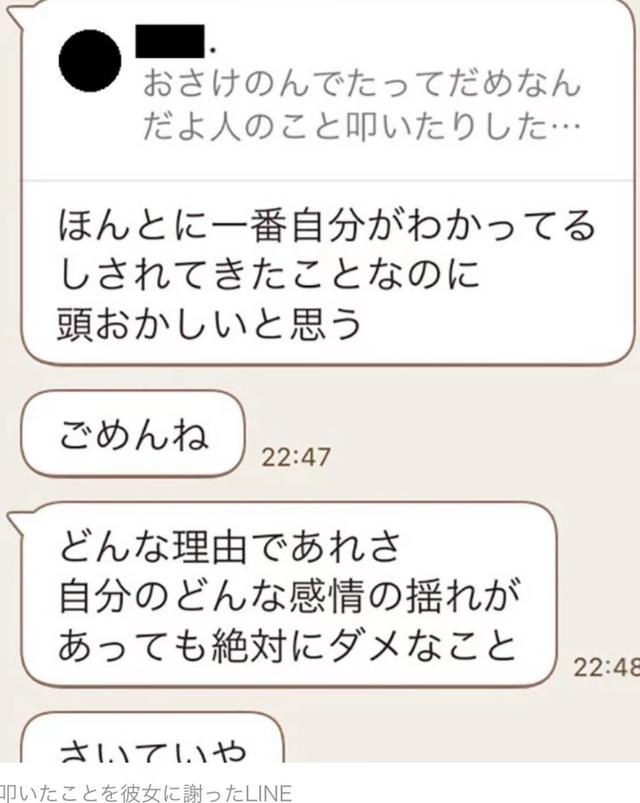朱生豪写给宋清如的一段话(朱生豪宋清如从前时间慢)


在浙江嘉兴的朱生豪故居门前有座雕像,上面刻着诗人兼翻译家的朱生豪与妻子,二人身体相连,脸庞依偎似是在窃窃私语。雕像底部摘自朱生豪曾写给宋清如的信:
“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
那时新婚不久,宋清如回娘家小住,留朱生豪独自在家。明知未到归期,他仍是每日跑去车站等待妻子回来,常失落而归,又怕打扰到宋清如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便将写给妻子的信锁在家中书柜里,再没寄出去。
有人说,朱生豪的一生简单纯粹,只做了两件事:翻译莎翁文集,给宋清如写信。
世间面貌不同的爱情故事千万种,这仍是其中最浪漫也最心碎的那个。

刚上之江大学时,出身富贵的宋清如一股子傲气,她向来不信传统观念中“女子早早回归家庭,嫁作他人妇”那一套,便辞去家中为她订下的娃娃亲。从私塾启蒙到女中,宋清如始终维持读书与写诗的习惯。
中学毕业,家人希望她能早日完婚,在抗争中,宋清如态度坚决,宁愿不要嫁妆,也要选择继续上学。
说来奇怪,民国时期信息较为闭塞,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也更为严苛,仍是不乏一批又一批生自旧时代的新女性,她们温婉的外表下,往往蕴藏着远大抱负与不逊于时下男子的坚韧心性。

▲ 宋清如
在褪色的旧照片中,宋清如留黑色短发,脸上仍带着少女的羞怯,扬起的嘴角分明流露出几分桀骜,常以素颜示人,连涂脂抹粉也不屑:
认识我的,是宋清如;不认识我的,我还是我。
这样的自信既来源于外在,也与那份诗意才华相关。可惜,这份自信很快便被击碎,第一次参加诗社活动时,她不懂得传统诗词的平仄,信心满满地写了一首半文半白的“宝塔诗”,摹状而吟,聚诗成塔。
样式虽新颖,当时的诗社活动却多是以交流旧体诗词为主。
待她分享结束,没有一人作声,空气中弥漫着若有似无的尴尬,直到传到朱生豪手中时,他仔仔细细将看到的诗句低声读完,虽一语未发,却低头笑了。
这低头一笑,让宋清如记到心里。多年后她还不断提起这个场景,语气极为动情,想必是自信心突然受挫,无言的安慰倒显得尤为珍贵。
后来才知,这朱生豪虽在学业上高她三级,实际年龄却小她一岁,“那时,他完全是个孩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的,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这与旁人对朱生豪的印象截然不同。在多数人眼中,朱生豪沉静寡言且敏感多思,这与家庭有关。
不似宋清如自小家境殷实,在顺风顺水的环境中成长,朱生豪出自嘉兴当地商贾人家,起初衣食无缺,自小成绩颇佳,始终位列甲等第一名,本该是骄矜的少年郎。
然而到了民国11年,他刚满10岁,家中突逢变故,父母经营的布店统统倒闭,先是母亲病逝,家中陷入极为晦暗的一段时光,两年后,父亲因积劳成疾也溘然长逝。
父母双双亡故,剩余产业无以为继,此时朱生豪只有12岁。
经济尚有可依,父母多年积蓄可以供他读书,生活上落得无人可依。最终寡居的姑母收养了他,多少尝到了些寄人篱下的滋味。
很长一段时间内,朱生豪近乎封闭了自己的情绪,全然将心思放在了读书上,不负所望,有位老师甚至认为他的聪明才力“不当以学生视之”:
多前人未发之论,爽利无比。其人今年才二十岁,渊默若处子,轻易不发一言。之江办学数十年,恐无此不易之才也。
突逢巨变的悲痛被全然寄托在学业上,学业有所成,曾经开朗和善的朱生豪却变得日渐沉默。

▲ 之江大学1932年中国文学会合影(后排右一为朱生豪)
直至在大学校园里遇见性子截然不同的宋清如,后者眼眸中的盈盈笑意与诗中显露的才气,他这才发觉:原来这个混沌的世间可以如此“诗意地栖居”。
起初二人只谈诗词,那场诗社活动结束三天后,朱生豪便写信给宋清如,以请她指正之名,而教她一些旧体诗词,逐渐地,他们开始谈过往经历与未来展望。
时局动荡,对于两个年轻人而言,前路一片迷茫。
很快,朱生豪即将毕业,他在师友中向来有才子的美誉。又因擅长英文,被上海世界书局聘作英文编辑,他怀着“肩上人生的担负”,踏上了未来的旅程。
远行之前,两人晦明晦暗的关系才有些微突破,朱生豪写了三首《鹧鸪天》递给留在之江大学的宋清如,宋清如打开书信,其中有句:
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从前不曾宣泄于口的情意,此刻跃然纸上。

到了1937年,江浙沦陷。
宋清如毕业后从杭州一路逃至四川教书,朱生豪依然在世界书局。两人之间的距离遥远,身处异地,书信成了最好的载体。写信人彼时的情感寄托于纸上,字与句都不再干涸反倒有了自身的意味。
很多信中,朱生豪是抑郁的,随着眼界逐渐开阔,以往的诗歌在历代文豪面前自觉微末,陷入了无法适从的彷徨。他的身体也始终孱弱,时不时生出寻死的念头,竟有些像他欣赏的英国诗人济慈。

▲ 济慈
济慈只活了25年,生命如同夏花般短暂,他曾写道:
头枕在爱人的胸膛,
永远感受她柔软的起伏,
在甜蜜的不安永远清醒,
不断,不断听她温柔的呼吸,
如此永生,否则就让我在痴迷中死去。
商人重利,诗人多情。诗人的爱总是浪漫炽热,又带着决绝的意味。朱生豪亦然,他的浪漫世人皆知,比如那句被人引用无数次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抑或是“为了你,我也有走向光明的热望,世界于我不会太寂寞。”
可倘若没有收到宋清如的回信,他又会寝食难安,化作不讲理的孩童,在纸上控诉着:
费你五分钟那么宝贵的时间,两滴眼泪那么多的墨水,却免得我一会儿恨你一会儿体谅你,一会儿发誓不再爱你,一会儿发誓无论你怎样待我不好,我总死心眼儿爱你。
他将男女之爱分为四种:原始的爱,摩登的爱,理智的爱与精神的爱。
他认为自己与宋清如之间属于第三种,理智且哲学的爱,这是一种宁静而非炙热的爱意,关乎爱情,却又不止步于男女之爱。
朱生豪对宋清如的情感是复杂的,年少突逢变故的不安底色上,夹杂着恰逢知己的欣喜与对亲密关系的渴望……又常年浸染浪漫诗文,这令他始终保持在激昂而饱满的情绪之中。
关系尚未确定时,颠簸流离的几年中,两人家中双双开始催促婚姻之事。令人意外的是,在特殊时代环境下,两人都曾是不婚主义者。
▲ 朱生豪
朱生豪是对当时婚姻制度的不满与多年困苦环境所迫;宋清如则坚定认为家庭会束缚住自己,结婚意味丧失一切。虽同为不婚主义者,朱生豪反倒劝慰她:一个自己有所树立的女子,结了婚也不妨碍她为一个不平凡者。
他鼓励宋清如不要被性别束缚,从重重的桎梏里把自己的心灵解放出来,不要有什么小姐式的感伤,须得耐得了苦,受得住讥笑与轻蔑。
在众多花样繁复的称谓中,最动人的是朱生豪曾称呼宋为弟弟,宋清如大他一岁,性别与年龄都成了相反,至于为什么,朱生豪解释:
“论年岁我不比你大什么,忧患比你经得多,人生的经验则不见比你丰富什么,但就自己所有的学问,几年来冷静的观察与思索,以及早入世诸点上,也许确能做一个对你有一点益处的朋友,不止是一个温柔的好男子而已。”
有人说,从前民国闻名天下的四大情书,徐志摩的《爱眉小札》;朱湘所写的《海外寄霓君》,沈从文为张兆和所写的《湘行书简》与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两地书》。到了朱生豪这里,通通差了一个等级:
沈从文是深情无措的稚子,鲁迅成了温情别扭的硬汉,朱湘是温柔委屈的弱书生,徐志摩看上去只是个自以为是的小白脸。
无他,时而是故作憨态的弟弟,时而是高山流水遇知音,时而成了富有人生经验的年长者。书信中透露出的爱意背后有万般形态,性格自发的矛盾感导致他显得格外真挚与迷人。
柴米夫妻
有人将朱生豪这一生归结为两件事:翻译莎翁名作,给宋清如写信。
少有人知连翻译莎翁也不乏宋清如的因素,鲁迅曾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慷慨激昂地呼吁时下读书人翻译莎翁名著,不免让人轻看。朱生豪提笔给宋清如写信:
你崇拜不崇拜民族英雄?如果把莎士比亚译成功以后,舍弟说我将成为一个民族英雄,因为有人曾经说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老莎的译本都没有。
他揣着两本《牛津辞典》与《英汉四用辞典》便开始翻译,空虚的失落感中找到了一些价值感,为了国家,也为了想做宋清如心中的英雄,这成了他心中认定的事情。
朱生豪的译作版本还原了作品的诗意,字与句都经过数遍推敲。
无奈1941年底,袭击珍珠港事件爆发,日军进占租界,冲进报社,朱生豪虽跟从职工群里逃走,却无法顾及原本的诗词集与译本。后来日军在报馆中放了一把大火,付之一炬。
他只能重新再译,战火纷飞下,仅《暴风雨》一篇就翻译了三次。好在,这段日子里有失也有得。朱生豪与宋清如终于相聚,相约逃离此地,还是朋友建议,二人本是眷侣,不如结成夫妻, 好方便同行。
▲ 词人夏承焘
炽热的爱情回归婚姻,无非两种结局:始终浪漫,或是成了一地鸡毛。婚礼时,好友兼词人夏承焘送了一句婚联:
才子佳人,柴米夫妻。
提到婚后生活,曾有人想为宋清如立书作传,宋清如只淡然一笑:“写什么,值得吗?无非是他译莎,我烧饭。”
战争与贫穷充斥着生活,那时物价飞涨,虽二人生活简朴,却永远追不上高涨的米价,宋清如回忆那时的朱生豪面若泰然,偶尔午夜梦回时会见他泪湿枕巾。
两人的感情一如既往,朱生豪的翻译工作每天从3000字加到8000字,平日里足不出户,精神上却如坐囚笼,只有埋头工作时,才恢复了一点自尊心。
有位好心的邻居曾向他提议某个县的教育局长是同为之江大学毕业的同学,若是你们找他谋一个教师的职位,大概不成问题。朱生豪当时虽不作答,但事后吐露,“要我到敌伪那里去要饭吃,我宁愿到妈妈那里去。”
此时,他的母亲早已过世。
▲ 朱生豪与宋清如之子,朱尚刚
支撑着他的仅有宋清如与心中微弱的信念,他坚持只有将莎翁杰作译出来后,才能响亮地回答那些嘲讽我们是无文化国家的人们,“炎黄子孙绝不会永远落后。”
后人皆称朱宋二人情感中,宋清如的情感浓度远不如朱生豪,也只有宋清如懂他的抱负与坚持,不曾逼迫他从事不喜欢的事务,安于清贫。
曾经惟恐自己被婚姻束缚的宋清如甘愿洗手做羹汤,揽下了家里家外的活计,还得去隔壁裁缝铺做些加工的活才能贴补。
就算如此,向来孱弱的朱生豪在长期辛勤工作与贫困的生活条件中仍是病了,被确诊为肺结核。他长期在病痛的折磨中又因经济状况不肯就医,到了末期,只算得上勉强维持生命。
直至离世前夕,朱生豪已然病体惬惬,他仍仰卧在床上高声朗诵莎剧原文,声音铿锵。时而清醒时而昏睡,清醒时只无奈告诉宋清如:“莎士比亚剧本还有5部没有翻译完,早知一病不起,我就是拼了命也要把它译完。”
可他始终没有熬过这场病,临走前,他轻轻地喊着宋清如:“小清清,我要去了。”
在后人纠结如何定论朱生豪此人时,宋清如总结为首先他是诗人,其次是一个爱国者,最后才是翻译家。
朱生豪的儿子朱尚刚认为,这是对“朱生豪是怎样的人?”这个问题这基本的评价。他认为父亲既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偶尔烧个灶火也会弄得满屋子烟。可当国破家亡时刻,又能以身相殉自己的事业。
这是怎样的执着?有位老教授看过他的译本惊为天人:“很多人都不相信,这部优秀的译作,竟然是一个从来都没有出过国的人翻译的。”
归于尘土
朱生豪去世那一年,宋清如33岁,孩子刚满一岁,异地十年,真正的婚姻却只有两年半,在独子朱尚刚看来,父亲的生命火花稍纵即逝,而母亲的一生则漫长而坎坷。
宋清如心中清楚,朱生豪留下的唯一财产,只有一妻一子,还有未完成的莎翁译作。为了完成丈夫的遗愿,她带着孩子,向学校请假独自前往重庆,想联系朱生豪的弟弟继续完成译本。
那时交通不便,其中艰难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联系到朱生豪幼弟,其弟试译了一部分寄给出版社。然朱生豪翻译风格擅长文字的意趣美感,并非常人能代替,被出版社拒了回来。
丈夫遗愿未了,还有180万字莎翁译稿未曾面世,倘若此时中断,朱生豪多年心血将毁于一旦。
她又一次地,自己挑起了这个胆子。
那时宋清如还在杭州当教师,同事印象里,她总是睡得很晚,闲暇时间里也只待在家中看书,很少出门。
▲ 宋清如老年
儿子朱尚刚记忆中的母亲,远无早年朱生豪信中描述的那般活泼生动,朱生豪的去世仿佛带走了她的快乐,也带走了她的悲伤。
她很少和儿子提及与父亲相关的事情,只有去他坟前祭奠时,伫立良久,一语不发。
零零散散花了三年多时间,剩下的莎翁终于译完,悉数寄给出版社,对方却回复说已有其他译稿。宋清如知道后神情平静,无一丝怨怼之意,将一堆译稿默默收了起来。
现实并非童话。坊间传闻她寡居多年后曾与一骆姓男子同居,还生下一个女儿,真假莫辨。
遥想她与朱生豪谈起婚姻问题,后者曾在信中告诉她:
我以为你的身体不是个耐得起辛苦磨练的人生战士的身体,事实上你需要一个较温柔的环境。你如真结了婚一定会使我感到甚大的悲哀,但我对你太关切了,我殊不愿见你永远是一头彷徨歧路的迷羊。
此时两人尚未结成夫妻,却也可侧面验证若是朱生豪本人得知,亦不会怪她。可终究,宋清如没有与骆先生走在一起。至于原因,就连儿子也不曾交待。
到了晚年,宋清如把一切都看得很淡,漂泊了三十多年,她回到嘉兴的朱氏老宅,住在偏屋中,平日里不常言语,只在提及朱生豪时话略多些。
短短几年的相处时光在她未来孤寂的几十年中,都不断被拿来咀嚼其中美好与细碎。
有人提出将这些书信是否能用来出版,她未曾想便拒绝了,准备在去世之前,用一把火将这些烧干净,与她一起告别这人世间。
或许不舍,她终究没有将过往信件烧去,珍藏的那些书信被一一整理,挑了一部分成了书,名为《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宋清如本是才女,写得一手漂亮的新式诗词,曾被《现代》杂志主编誉为“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可惜她的诗作多在抗战时间消亡干净,只留下零星几首:
假如你是一阵过路的西风
我是西风中飘零的败叶
你悄悄地来,又悄悄地去了
寂寞的路上只留下落叶寂寞的叹息
一语成谶,两人的命运真如秋风与落叶。1997年,距离朱生豪去世已经半个世纪,宋清如终是去了。
遥想五十年前,朱生豪去世两周年时,宋清如曾写过一封长信,通篇悲怆,其中有一句:
“当我走完了这命定的路程时,会看见你含着笑向我招手。那时候,我将轻快地跟着你的踪迹,哪管是天堂或是地狱。”
参考资料:
1.朱生豪、宋清如《伉俪》
2.朱生豪《朱生豪情书集》
3.董桥《朱生豪夫人宋清如》
4.朱尚刚《朱生豪给宋清如的信》
5.Lens《朱生豪和宋清如这场异地恋,来听听儿子朱尚刚怎么说》
6.宋清如、彭重熙《宋清如与彭重熙谈朱生豪》
7.陶佳佳《“宋清如至上主义者”:朱生豪式浪漫》
十点人物志原创内容 转载请联系后台授权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