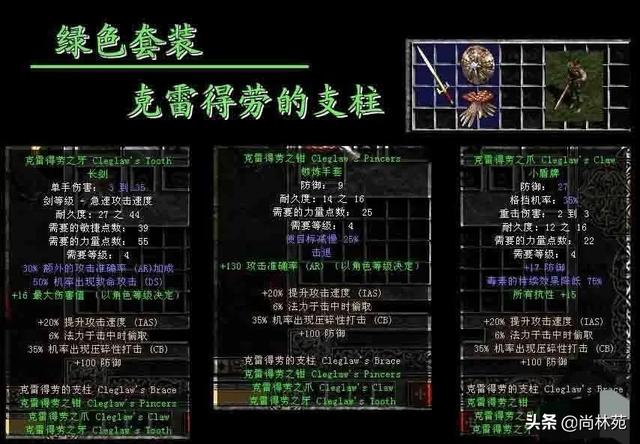男权与女权并非对立碾压的存在(解释男权下女性的从属地位)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平等已经成为政治思想的默认设置,不平等只有在理由充分的情况下才会被接受。
而在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情况正好相反。
不平等是习惯性的、合理的标准,而平等,如果能被考虑到的话,则需要理由。不平等无处不在,真实可感,而平等则需要被想象、争论和凭空构想出来。
简言之,平等需要被发明。

新民说重磅新书《发明人类》提供了一幅关于人类概念如何产生的全景视图。这本书虽然够厚(600页),但是真好看啊……作者西佩·斯图尔曼聚焦希罗多德、司马迁、蒙田、博厄斯等人对各自时代的边境经验的思索,分析世界历史上不同宗教经典、哲学、史书、民族志中“共同人类”观的异同,追溯跨文化平等的演进。这么说吧,虽然是社科书,虽然有些学术,但是阅读起来丝滑无比,看一段就想看两段,看一页就想看完一章,非常有启发性。
今天的推文,便来自这本书。
现代平等的发明(节选)
17 世纪六七十年代,笛卡尔主义已经确立了自己“新哲学”的地位。在追随者当中,最激进的要数弗朗索瓦·普兰·德拉巴尔,他是一名辍学的神学系学生,在17世纪70年代发表了三篇关于两性平等的论文。大学里的经院哲学使普兰感到幻灭,1665年左右,他转向笛卡尔哲学与现代自然法。尽管社会与政治问题在笛卡尔的思想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但普兰却专注于这些问题,并沿着笛卡尔的路线发展出了一种社会批判。
站在后世回溯,我们可以将普兰的思想视为最早的可辨认的启蒙社会哲学之一。
普兰向那些将男权至上合理化为“自然”的自然法哲学家发起了挑战,要求他们用清晰明了的语言解释他们所谓“自然”的含义。他总结道,这些哲学家不假思索地将一种仅基于习俗的差异归结为自然。根据普兰的说法,女人的从属地位就如其他所有形式的人类附庸一般,是由“运气、权力与习俗”造成的,根本没有自然依据。从笛卡尔的思想出发,他重塑了早期女性主义在妇女问题(querelle des femmes)上的观点,这是一股相当持久的欧洲思潮,可以追溯到15世纪早期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作品。
普兰对偏见和习俗展开了普遍的批评,并将之与一种环境论的社会心理学相结合。他于1673年出版的第一本书的书名是纲领性的:《关于两性平等的物质与道德论述,以见出克服偏见的重要性》。普兰邀请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自行判断当时的性别化社会习俗是否具备理性与自然的基础:“你天生被赋予理性,”他疾呼道,“运用你的理性,不要盲目地将其献祭给任何人。”笛卡尔式理性自主因此变成了社会批评的工具。
普兰对女性从属地位的批判经常被概括为一个简洁的公式,即“心灵从未有性别之分”,但这具有误导性。实际上,普兰声称,他的目的是证明男女在身心方面都是平等的。他的论证确实是从无实体的心灵没有性别之分开始的,但是紧接着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补充,即解剖学研究并没有发现男性与女性的大脑有任何不同。

基于笛卡尔对人体生理学的机械论解释,普兰反对当时在医学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亚里士多德、盖仑和希波克拉底的理论。上述理论用女性的“冷”“湿”体液界定其本质,与男性的“热”“干”相对。普兰反驳说,这“将性别差异太过极端化”了,因为除了生殖器官之外,男性与女性的身体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运作。因此,普兰对于平等的论证依赖于理性主义和生物学:无实体的心灵没有性别之分;大脑没有性别之分;除了生殖器官之外,身体也无性别之分。使人之为人的,是我们的思维能力和驱动身体运行的生物机制。用笛卡尔的话讲,身体的外在形态与相貌是次要品质,不会影响我们的基本人性。
显然,这就需要对存在于所有地区和大陆的高度不平等的性别制度做出解释。这里,普兰将笛卡尔关于习俗力量的零星论述发展为一种环境论的心理学。他默默舍弃了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说,转而将新生儿的心灵描述为一块白板(tabula rasa)。从婴儿时期开始,我们就踏上了生命的旅程,他说我们“就像被海水带到某个新世界海岸上的外邦人,对于这个新世界一无所知,既不了解那里的事物,也不了解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所讲的语言,以及所遵守的法律”比起笛卡尔,这听起来更像是洛克。这与普兰对种族中心主义的蔑视十分吻合(他的这一观念很可能承自蒙田):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最好的,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个国家;他在哪种宗教下长大,哪种宗教就是他所要真正信仰且必须遵循的,虽然他可能从未停下来审视该宗教,或将之与其他宗教进行比较。一个人对于自己的同胞总是比对一个外邦人更加亲切。
为了解释女性的从属地位,普兰接着概述了一段关于人类的推测史。他解释说,在人类历史之初,并不存在制度上的不平等。在那个遥远的时代,没有政府,没有科学,没有雇佣关系,没有国教,男人与女人都是天真单纯的,他们从事农业与狩猎,“就像今天的野蛮人仍然在做的那样”。因此,人类历史的第一阶段就实现了自然平等。
普兰继而展示不平等是如何出现的。随着社会变得更加复杂,男女之间的简单合作关系被大家庭、宗族与部落所取代。人口增加,资源开始稀缺,争夺土地与货物的斗争频发。男性身体相对强健,他们通过暴力与计谋获得对其他人的控制权。女性身体相对柔弱,不能参与这些军事冒险,因此被排除在权力与权威的席位之外。征服了更大领土的男性将女人视为战利品的一部分,并轻视她们,因为征服者总是轻视被征服者。
男人为自己强大的身体力量而着迷,幻想自己在所有方面都可凌驾于女人之上。因此,婚姻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最初的阶段,女人都是嫁给自己大家族里的男人,他们待她们如姐妹,但是从那以后,女人被许配给陌生人,而这些人待她们更像仆人。普兰认为,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人们开始相信女人不如男人。
自愿互惠的制度现在让位于一种胁迫性和恐吓性的严苛制度(主要包括父权制家庭、私有财产和封地),很快又被有组织的宗教所掌控。和其他所有事物一样,宗教机构也由男性统治。对于基督教及其特殊的历史地位,普兰保持了谨慎的沉默,但是他对于男性垄断神职的观察,会让读者想起基督教,特别是罗马天主教的等级体系。普兰把历史表现为不平等和压迫的增加,这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其中的一些人滥用他们的权力和闲暇,密谋如何征服他人,进而将自由的黄金时代变成一个奴役的黑铁时代。压迫使利润与商品陷入混乱,以至于一个人为了生存需要依赖另一个人。纯真与和平都渐渐成为过去,混乱进一步加剧,产生了贪婪、野心、虚荣、奢侈、懒惰、傲慢、残忍、暴政、虚假、争吵、战争、不安和焦虑——“总而言之,几乎所有的身心疾病都困扰着我们”。这个悲观的历史观甚至早于卢梭(后者可能曾读过普兰的作品)。
就像天文学上的日心说,普兰的历史学推测纠正了普通的常识经验。不假思索地接受自己所“见”之物的人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太阳在转动而地球保持静止,同样,他们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观察到的周围女性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模式就是对女性“本质”的忠实反映。
普兰试图阐述的是,17 世纪女性的行为方式并不能确切地反映出女性的本质,而是无数个世纪以来对女性的压迫及错误教育的结果。用现代术语来说,性别是在性别制度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