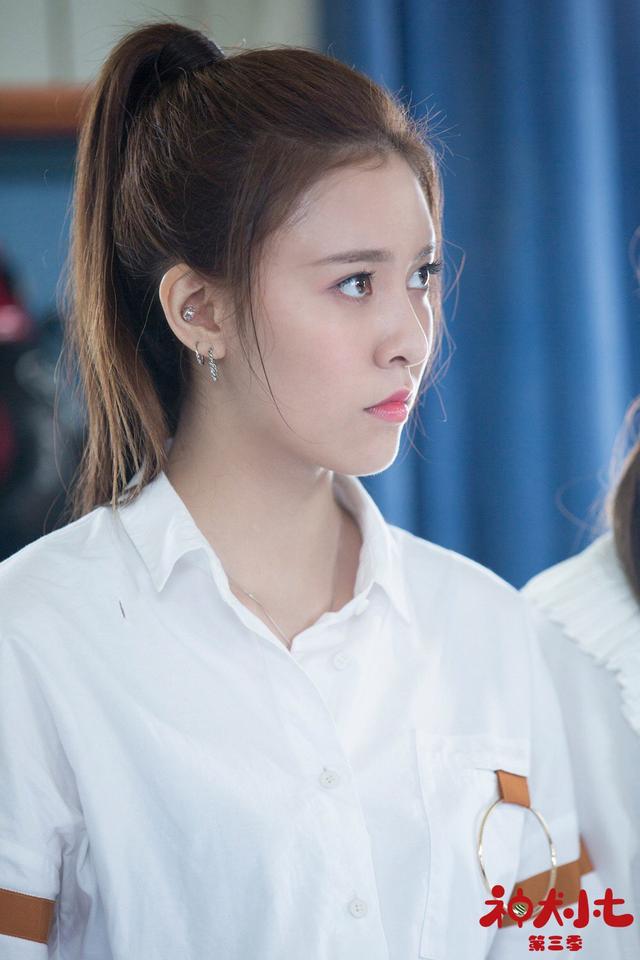马诗里描写马的诗句有哪些(马家骏诗词选初版前言)

马家骏教授
文/马家骏
秦山万叠闪明珠, 春染椒溪满岸萸,
日映轻岚笛飘翠, 花红柳绿绣宏图。
这是1984年4月10日《陕西日报》上发表的我的一首诗, 它的题目叫《过佛坪》。佛坪是陕西秦岭万山丛中的一个小县, 县城人口不多, 它是国宝大熊猫和金丝猴的故乡。可能读到这本小册子的有些外省同志,还不知道这个县。佛坪,我也是那时有机会去过一次。1984年春,我应邀在汉中师范学院讲学。由汉中回西安,通常是十二个小时的火车。这次却坐汽车斜穿秦岭,用两天的路程,颠簸回西安。连西安都桃红柳绿了,秦岭山顶路上却还有一尺厚的雪。为什么偏要走一条艰难的路呢?原来我的学生郭鹏在佛坪工作(时任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在他操心下,县上领导让派车接送我,几位书记、县长还亲自看望和陪同。有人开玩说:在佛坪的历史上第一次来了文学教授, 面对盛情, 我只有用给学生、干部、教师们作两场报告这种简易劳动来回报。佛坪的山水优美,故而写下了上面那首七绝,题赠给佛坪的同志。
事隔了七年,家在富庶的洋具的郭鹏同志还在偏僻的佛坪山区工作,他来到我西安家中,谈起来,愿把我在报刊上发表的诗词及过去写的还没有发表的诗词,编印一本小册子。这样,我的诗就不仅是一首《过佛坪》、而是众多的拙作同佛坪发生关系了。我感谢佛坪的同志,尤其感谢郭鹏同志。因此,这个《前言》就从佛坪说起。我的诗词没有什么价值,我认为佛坪的情意更珍贵,于是便向不了解佛坪的省内外读到这本小册子的同志,首先讲了上面有关佛坪的话。
至于我的诗词和这本集子,可说的不很多。有些同志很奇怪:说老马是搞外国文学的, 读到过他翻译的外国诗, 没想到他还写古典诗词, 有些还断续发表出来?传统诗词是一种青年人不易掌握的艺术形式。我能懂得一点,是有赖我祖父和读高中时一位叫田直僧的国文老师。他们写诗,也给我讲过诗词格律。现在有些讲诗词格律的书或电视讲座,说得太复杂,反而把人弄胡涂了。其实,可简化:即要记住“平平仄仄平”和“仄仄仄平平”两个律句。对近体诗而言,这是两种收句的格式,一对应,就有了出句。一配合就有了两种五绝,加一倍就是五律,每句上加相反的两个平或仄的字词,就有了七绝或七律,就会“二四六分明”。一句中的第二、第四、第六这三个字很重要:二与六的平仄要一样,而同第四字要不同。一联内相对的两句的“二四六”的平仄要相反,两联间接续的两句的平仄要相同或叫“黏连”。至于“平水韵”,北方人多记不住入声字;其实,复合韵母[an][en][ang][eng][ong][ai][ei][ao] [ou] 是没有入声字的,只要区别[i][u][ü][a][e][o][ê] 里的平声与入声就大体上掌握了。如“一”是入声,“衣”是平声,等等。“平水韵”里还有个“邻韵”,词与古风可以通押,诗不能通押。如“东、冬、更、青、蒸”是五个不同的韵,这五韵部中的字之间,不能押韵。这些韵字不好区别,大致说来,不同介母的字各属一韵。如“萧”音,在声与韵之间有[i]的介母,而“豪”就没有,它俩不是一个韵,写近体诗,不要通押。这些劳什子,说说容易,实践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提笔一写,出韵拗律的事常常发生。只有那些非常熟悉的专家里手,才不在困扰时查韵书。
我写诗词,历史短,产量少,构思也常犯难。1976年,带毕业班去华县实习,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文艺创作班,让我去讲创作,并给我油印了一本诗词小册子。我送给了傅更生老师一册。1977年,省上开文艺创作会议,我俩住在一个房间里,他指评了我那小册子,并谈过写诗的窍门。可惜,我很鲁钝,对他这位专家的高见,领会不深,以后,依然按自己的习惯性去写作诗词,所以,至今水平不高。
在华县印的小册子里,也有一个《前言》,这里抄出,以表达某些意思:
匆匆一二十载,成就辉煌,自有佳诗高唱。开门办学几年,硕果累累,当出好歌畅吟。自知德浅才疏,未敢问津;偏逢下乡实践,讲述创作。农村文艺骨干挥笔上阵,理论联系实际,新作遍地;广大工农战士热情洋溢,歌唱革命建设,诗文成林。“知识里手”,述而不作,自惭相形见绌,立即急起直追,平生虽好诗词,长久不谙音律。逢年过节,上山下乡,偶有感触,捻须苦吟拙句;东奔西走,外地风光,增广见闻,凑合连缀半阕。水平低而格调浅,诗情竭而文章疏;失黏脱对不少,句拗韵出尤多。间或学生抄去,谬种流传;偶而请教挚友,愧见世人。县上同志鼓励,勉强滥竽充数,拣取一些,劣中剔劣,其余由老鼠批判。现抄以汇报衷肠,不敢冒充文学,也算心路历程。修修补补,不为杀青;镌刻数册,非是推广,俾便征询高见,敬请读者斧正。
现在抄来,自己也暗中好笑,在那十分“革命” 的年代, 却如迂腐学究般哼四六骈文, 冒充高古, 是颇不合时宜的。它既不首先引“最高指示”,也不用时兴的语录和“文件”的批判精神作外衣,真是“诗令智昏”。不过,它确实讲了我的某些心里话。
1988年8月20日去霍松林先生38楼新居,他告诉我:最近成立了陕西省诗词学会,他被选为会长,我被选为常务理事。这无疑对我是个鞭策。
我没有无病呻吟的本领,坐在家中面对春夏秋冬、风花雪月就能写出诗、填出词来。“偶感”式的东西也有,但不多。多的是东奔西走的见闻。故而写客观的多,抒个人喜怒哀乐的少,或曰“主体性”不强。就是有些给友人、学生、青年的赠答诗,也多为勉励而非关个人私情。在诗词写作方面,我名不副实,即不是骏马,而是一匹驽马。写出的东西,也就是杂乱奔跑的足迹了。这本诗集,实际应叫《骛迹集》。已往的诗,存留着时代的痕迹,这也就随它去吧!
无产阶级革命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诗中(恕我又回到自己的专业里去了)说:他的诗, 赞美祖国的现在, 更三倍地赞美祖国的未来。又说:他用自己诗歌写作的劳动,参加了祖国的建设。这些意思也表达了我的想法。但主观愿望是空的,究竟在诗词写作的实践中,在多大程度上体现这个愿望,以及体现的艺术水平如何?这只能由读者和专家来品评了。
最后,我要写几句话,特别表示对郭鹏同志的谢意。郭鹏同志于1965年考入陕西师大中文系,刚好在我上课的那一班。我给他们讲的是《文艺理论》课,当时规定主要讲《毛泽东文艺思想》。郭鹏人诚恳,学习努力,给我印象很好。
1966年夏,发生了所谓“文革”。郭鹏所在班秋天由乡下“四清”回来,这时极“左”狂潮沸腾,而郭鹏反对“打砸抢”,不介入派性斗争,多是偷偷阅读古今作品,有时找我讨论学问。这在当时的学生中是不多的。1968年5月,学校中刮起一股抓斗惨打不同观点的同学和教师的恶风。一时间,学校里不少教师被打伤致残,有的甚至被逼死。没想到这股妖风刮到了我这个“消遥派”头上。一天,派头头找了些外系打手,白天抓我挂上“井冈山分子”游街,晚上于人不去处私设公堂,既不向毛主席致敬,也不读毛主席语录,拳打脚踢、弹簧鞭、钢板尺齐下,对我严刑逼供,我交待不出对立派的内幕,故而挨了一顿。郭鹏白天见我被抓游校,晚上来我家,未见到我,返回时经过“公堂”,听见打手们的审问喝斥,立即回他班上叫来一些主持正义的同学,把我抢救出来,并对派头头宣布:此人由他们六九级三班红卫兵“兵管”了。我在同学宿舍被保护了好几天,学校打人风平息了,我才得以安全的回家。这次历险,多亏了郭鹏和他的同学们,不然,当时生命如何,实难预料。看来,同是“文革”中的学生,有干坏事的,也有主持正义、保护无辜的。我曾在《教师报》上写过一篇文章,其中说“文革被救”就指此事。郭鹏勤奋好学,毕业后,断续有书信来往;到西安办公,也常来家交换学问上的看法。他近年主持编修《佛坪县志》,工作很有成绩。这次,由他来编辑我的诗词,如同二十多年前他救我一样,我仍对他由衷感谢。
这里我还要特别感谢两位同志:
一位是霍松林教授,他作为陕西省诗词学会的会长,在这本选集内部印刷时,不但应郭鹏之邀给题了字,而且慷慨应允可作学会成员成果,落款用学会的名义。
另一位是镇巴县志办公室的主任吉晓夫同志。我的《忆江南·过巴山》一词,三十多年前发表在《镇巴日报》上,但长期存题缺词。这次多亏了郭鹏请吉晓夫同志从档案中抄寄来,令人感动,故在此一并致谢。
马家骏1991年5月于陕西师范大学
初 版 后 记
——《马家骏诗词选》编后
郭 鹏
有幸为马老师编辑诗词选, 实感欣慰之至。
1965年9月2日,尚不满19岁的我,踏进了陕西师范大学的校门,从陕南农村来到这高等学府,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激动、新奇。然而,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使人不觉惶惶然。此日下午,我正在宿舍整理行李,突然门被推开,进来一位身材高大、四十左右、满带笑容的人,把我看了一眼,出口就问:“你叫郭鹏,是洋县人吧?”我愣住了:这是谁?怎么就知道我的名字?我忙回答:“是。”心里正在纳闷,来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便来了个自我介绍:“我叫马家骏,今年要给你们班带文艺理论课。”我平生第一次见大学老师,更为惶恐了。马老师坐下来与我闲聊,热情地给我介绍刚到学校要办的一些事情。临走时,我大胆地问:“马老师,你咋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是洋县人呢?”马老师笑着说:“你们这些学生是我参加录取的,你们高考登记表上不是有照片、籍贯吗?”说完又到别的宿舍去了。我被这位慈祥而热情的老师感动了:一位带课老师,既不是班主任,又不是级主任,这么及时地看望我们,又能在这么多学生中,一一记住学生的照片模样、籍贯!这第一面,马老师就给我留下了极为亲切、极为神秘、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幕,虽然过去二十六年了,但一直历历在目。
马老师给我班带“文艺理论” 课。在讲台上,他那潇洒自如的学者风度,他那滔滔喷涌的知识洪流,他那微笑中带着严肃的神情,甚至一个比喻,一个眼神,一扬手,一投足,都在人的脑海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讲台下,自习时间,他常来教室向学生辅导,休息时间,他常出入学生宿舍,主动给我们讲授、介绍各门各科知识,谈天说地,五花八门,有时还同大家打扑克、下象棋,兴趣来了,还给大家来几段京戏。他是那样的亲切、和蔼、诚恳,完全不像讲台上的老师,而像一位热情的朋友,与那些上课上讲台,下课从不见面的其他老师完全不一样。就是为这,马老师在我们的心目中,既是一位尊敬的师长,又是亲密无间的益友。
“文化大革命”狂潮袭来,极“左”泛滥,许多教师被他的学生揪斗,而马老师却一直受他的学生(不管哪一派、什么观点)的爱戴、保护,这在当时是较少的(就是1968年5月社会上和学校打人风猖獗,马老师被揪被打,是一伙对马老师不了解、受人唆使的物理系学生干的)。因为他不以才傲人,不摆架子,待人以诚、以情,视学生为子女、为朋友,诲之不倦,至精至诚,学生同他,他同学生,心是在一起的。我深深地认为,马老师的为人,不愧为我国教师的楷模。
马老师主要是研究外国文学的,但他学识广博,对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都有深深的研究。记得1970年,中文系“战备疏散”到永寿县常宁镇上邑村,夏夜,坐在生产队打麦场上,在徐徐的凉风吹拂下,马老师手持手电筒,用光柱对着星空,他拿出记得厚厚的几大本天文学笔记,这实在令我惊异,简直认为马老师的头脑是浩瀚的大海,不,是个深邃莫测的星的宇宙。
对于诗词,我虽然有时也胡凑几句不合平仄的句子,但钻研不深。而对马老师的诗词却爱之甚切,每于报刊中,发现刊有马老师的诗文,即剪之贴之,欣赏学习。这些年搞行政工作,有时出差到西安,常爱往马老师的藏书室钻,寻阅马老师已发表或未发表的诗文。得知其诗词未结集时,便萌发了为其编辑出版诗词集的想法。同马老师一谈,即获应允,他便将其诗词稿全部奉送,使我欣喜之至。其情其感,超乎师生之上矣!
反复阅读马老师诗词,是一种美的享受,是感情的交流,是知识的润泽。在那“左”的年月中,象马老师这样的大手笔几无发表诗文的园地,他的诗词除部分在报刊上发表外,有的只能登在县城的墙报、板报上,有的一直静躺在笔记本中。但古今中外,优秀文艺作品的价值,不在于发表的形式如何,而在于内在的份量,在于情感的直切淳厚,有谁见过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年代,有什么报有什么刊呢?
“人过花甲犹豪杰”,这是马老师的一句诗。前天我去西安红十字会医院看他时(今年4月28日春游秦岭时跌伤,脚踝骨折住院),他坐在病床上,腿上固定着石膏,仍手不释卷,坚持写文章、看书。还谈到他今后的著述计划,确使人感到,这位年逾花甲的尊师,实是中国文坛、教坛上的一位“豪杰”。
写了以上这些话,算是对这本诗词集的结语吧!
编者 1991年5月25日于佛坪
[注]郭鹏,编审,汉中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著作多种。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独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