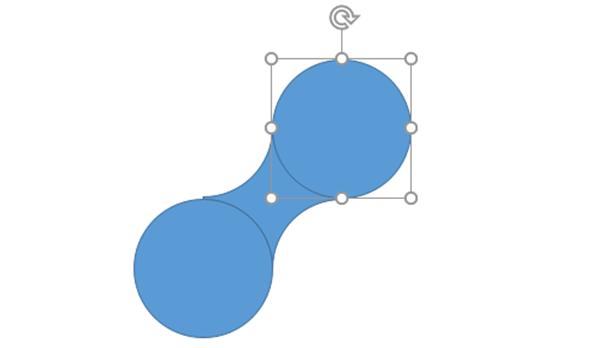人工智能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人工智能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 蓝江,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人工智能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人工智能在信息社会的重要性
作者:南京大学哲学系 蓝江
摘要:人工智能与现代社会,以及与社会主义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将人工智能看成一种技术的应用,人工智能技术也十分深远地影响着人类的未来社会。首先,人工智能技术并不是对人类社会的彻底取代,在赫拉利等人看来,人工智能会形成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状态,即“无用阶级”。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看,今天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并不是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人工智能,将无产阶级当做新时代的“卢德分子”,而是打破资本主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垄断和占有,成为帮助无产阶级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工具。最后,人工智能对社会主义的意义在于,它们可以打破哈耶克批判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的局限性,通过新控制论的方式来模拟出更确定可靠的社会主义模式,为未来社会主义提供可靠的基础。
基金:2018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项目编号:18ZDA017)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通信技术、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甚至基因工程、人工神经网络和脑科学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问题已经不纯粹是一个局限于计算机和数字科学领域内的话题,它的影响也逐步扩展到其他学科,如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工业领域中广泛的智能机器人应用,以及智能家居,无人驾驶汽车、无人机、智能手机和智能平台上的无形的人工智能的应用,带来的不纯粹是一场科技领域的革命,也会冲击社会生活。这样,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哲学在今天已经不能忽视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
不过,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来说,摆着面前的问题不仅仅是探讨人工智能对人类当下日常生活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究竟在人类日常生活中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人工智能带来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同样值得探讨:随着这种技术革命的发展,究竟是我们能借着人工智能的加速冲击波,突破资本主义的藩篱,还是人工智能成为资本主义奴役普通大众,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工具呢?在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最初设定的社会主义的目标,究竟是离我们更近了,还是更远了?的确,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判断,并没有变。但是,我们所面对的具体情境,并不是马克思所在的19世纪,甚至与20世纪最后20年都有着霄壤之别,面对这些新的历史状况,尤其是面对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和人工智能革命的浪潮,我们需要从现实社会的片段中寻找到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
一、无用阶级:无产阶级的新形态?
2005年,美国的未来学家、人工智能专家、谷歌工程总监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将自己多年来关于未来人工智能技术的思考结集出版,并将这本集子命名为《奇点临近》(The Singularity Is Near),在这本书的开头,库兹韦尔就提出了一个十分令人震惊的论断:奇点将代表人类的生物思想与现存技术融合的顶点,它将使人类超越自身的生物局限性。在人类与机器、现实与虚拟之间,不存在差异与后奇点。1也就是说,我们在技术发展上处于一个指数级的增长阶段上,这不是普通的线性发展的量变,在这个爆发性的指数级别的增长中,可能会达到一个增长的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奇点。具体到人类社会现实之中,奇点的意义在于,速度的高速增长终有一天会突破人类的生物学极限,以至于人类的生物性的大脑和身体已经不能承受这样的高速增长,这种增长不仅超越了人类大脑生物性思考的界限,也超越了人类想象力的界限。这样,奇点代表着人类生物性身体的极限状态,一旦超越了这个极限状态,生物性大脑将会让位于人工智能。
实际上,库兹韦尔的奇点理论依赖于他的另一个定理,即加速回报定律。而这项定律是对半导体行业的摩尔定律的一次矫正。摩尔定律认为,我们可以使集成电路上集成晶体管的数量每24个月增加一倍,电子传导距离随之减少,电路也将运行得更快,从而提高整体的计算能力。摩尔定律带来的后果是计算的性价比以指数级增长,其翻倍的速度(以12个月为基本单位)比人类社会范式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也就是说,在摩尔定律中,信息技术的指数级的增长,让发展的曲线更接近于一个反向的L型,而且反向L曲线的前部越来越接近于陡峭的直线。不过,库兹韦尔认为,摩尔定律的指数级增长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因为存在人类的生物学极限,而这个生物学极限正在接近奇点,一旦接近奇点,这个反向L型曲线就会变成库兹韦尔的S型曲线,库兹韦尔称之为加速回报定律。加速回报定律的关键在于,存在一个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取代了原来基于人类生物性的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模式凭借与智能机器结合的方式,在跨越了奇点之后,迅速向新的增长模式前进。对于这种变化,库兹韦尔保持一种拥抱的态度,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人工智能的未来》中十分明确地谈道:“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与不断发明中的智能技术融为一体。我们血液中的智能纳米机器人会保护我们的细胞与分子,进而维持我们的健康。这些纳米机器人还会通过毛细血管进入大脑,并与我们的生物神经元互动,直接扩展为我们的智力。这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2或许这个在库兹韦尔看来并不太遥远的奇点,正是所谓的人工智能时代的降临。
不过,各个领域的理论家们并不一定都像库兹韦尔那样来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加速回报定律,也不可能盲目地去拥抱一个代表不确定未来的奇点。实际上,无论是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家,还是普罗大众,对于可能代替人类甚至反过来支配人类的人工智能都带有着深深的忧虑。如以色列年轻学者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在《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一书中讲道:由计算机算法构成的人工智能会将人类驱逐出所有的就业领域。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看到了工人将那种取代他们工作的机器称为“铁人”,工人发现,原来可以用他们的体力来完成的工作,甚至一些他们体力所无法完成的工作,现在已经完全被机器所取代。3马克思曾引用过纱厂工头和工厂主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指出:“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别的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这样快这样大量地得到。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4在马克思的时代里,低级的重复性体力劳动会被机器所取代,机器成为一种“铁人”;在今天,赫拉利看到了一个更为广泛的事实,即人工智能进化到一个更高端的区域,将人类的思考性劳动也一并取代了。对于这种取代的后果,赫拉利并不像库兹韦尔那样保持乐观,而是给出了一个十分黑色的论调:“在过去几千年里,人类已经走向专业化。比起狩猎者,出租车司机或心脏病专科医生所做的事更为有限,也就更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我已一再强调,人工智能目前绝对无法做到与人类匹敌。但对大多数现代工作者来说,99%的人类特性及能力都是多余的。人工智能要把人类挤出就业市场,主要在特定行业需要的能力上超越人类,就足够了。”5赫拉利的这个论点,对于从马克思主义角度来研究人工智能十分重要。
第一,赫拉利认为,在现阶段,人工智能还达不到完全取代人类的形态。人工智能或者自动化的算法所取代的只是人口中的一部分,也就是偏重复性和低端性的一部分,这部分本身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们是重复性工作的体力工作者,在人工智能时代,他们是办公室的白领文员,甚至是写代码的码农。这样,和马克思分析的作为“铁人”的机器一样,人工智能所取代的是一种特殊的专业化的群体,这种群体所拥有的技能单调重复,所以很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超市的收银员逐渐被自动扫描支付程序所取代。随着无人驾驶技术的广泛应用,专业司机的职业地位也岌岌可危。这些被人工智能所取代的群体,成为赫拉利笔下的“无用阶级”。
第二,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沦为“无用阶级”,在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产生了更深刻的两极分化。掌握着高端算法、资本和权力的特权阶级,拥有着用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改造自己生物学身体的可能性。库兹韦尔描绘的“智能纳米机器人”的想象实际上只能被少数拥有巨大财力和权力的阶层所享有,这些经过智能改造后的生物—机器合体人,由于经过生物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改造,他们从一开始就拥有着超越一般人的体能和智力,拥有更长的寿命,身体衰老得更为缓慢,这种经过人工智能改造过的身体使他们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拥有了特权,也在生物学身体、基本体能和智能上拥有了特权。所以,人工智能社会的未来景象并不是人工智能彻底地取代人类,而是形成了被人工智能技术加强的合体的赛博格和体能、智能都处于劣势的“无用阶级”的区别。如果说在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里,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还只是经济和政治上的区别,那么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这种阶级区别直接体现在了智能和体能上,“无用阶级”再也无法通过自己身体性的打拼或者智能上的努力来超越自己平庸的地位,因为这条道路已经被新的数字技术、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所堵死。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作为精英阶层仍然将无产阶级作为剥削的对象,从而使无产阶级能够得以存在的话,今天的“无用阶级”的地位更为悲惨。赫拉利说道:“至少部分精英阶层会认为,无须浪费资源为大量无用的穷人提升甚至维持基本的健康水平,而应该集中资源,让极少数人提升到超人类。”6
第三,“无用阶级”就是数字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无产阶级的新形态。一方面,人工智能取代一部分专业化技能,从而造成普罗大众与精英阶层的分化,使之成为人工智能时代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另一方面,随着自身拥有技能的无用化,“无用阶级”进一步陷入“系统性愚蠢”(systematic stupidity)的状态之中。在法国思想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看来,这种在数字化和自动化社会中产生的替代,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化,在《自动化社会》中,斯蒂格勒十分明确地指出:“从1993年开始,随着所有人都可以借助网络,借助万维网技术进行网络式的阅读和书写,数字技术已经让超工业社会走向了无产阶级化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里,超工业时代成为系统愚蠢的时代,也可以称之为功能性愚蠢的时代”7。在斯蒂格勒看来,人工智能是一种药,在给精英阶层和社会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在社会功能上,让那些只能从事专门劳动的个体变得愚蠢,也就是感受性的(sensuel)无产阶级化,因为在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中,作为人的思维智能和感受性(sensibilité)的正常功能也被剥夺了,人类只能按照数字化和自动化的人工智能技术框架来运行自己的功能。他们没有感受,没有智能,只有一味地迎合固定的话语套路,充满躁动情绪,在资本的眼中,他们是最理想的消费者,因为一句“黑色星期五”的口号,就能让他们填满购物车。而另一方面,感受性和智能上的无产阶级化也造成了政治上的盲动,他们手中的选票不再是经过理智思考的产物,而是被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控制的票仓。一旦无产阶级在功能上变得“愚蠢”,即被技术剥夺了自我思考的能力,成为感受性的“无用阶级”,他们自然会沦为右翼民粹主义利用的工具。在欧美民粹主义极富煽动性口号的蛊惑下,他们会像自动机器一样,选出人工智能算法所预测的选项。
问题在于,人工智能导致的“无用阶级”的出现,是否就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中提到过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大军”?这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也有学者指出“‘无用阶级’在本质上是它不能为资本价值增殖所需要和利用,从而沦为‘多余’或‘过剩’的人口而已”8。但是,在马克思那里,这种“过剩人口”是周期性的。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到下一个正循环周期,这些失业的产业后备军会再次被纳入到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体制中来。但是,被人工智能淘汰的“无用阶级”不是诞生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换言之,对“无用阶级”的替代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危机循环周期之内,而是在正常的生产范畴之内诞生的概念。这样,“无用阶级”不会像“产业后备军”那样重新看到再次被雇佣的希望。对于这样的现象,需要我们重新思考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的应用形成的宏观层面的社会架构。
二、人工智能与传统计划体制的局限
作为新无产阶级的“无用阶级”带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究竟是更有利于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超越,走向社会主义,甚至共产主义,还是成为通向更高社会阶段的障碍,成为资本的同谋,而新无产阶级使用这些技术实现解放的希望无异于与虎谋皮?
事实上,从赫拉利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赫拉利并不认为人工智能技术是所有人的敌人,一部分处于高端的精英阶层因此而获利,获得更长的寿命、更完备的知识能力和体能、更丰富的经验、更协调的身体。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围绕人工智能的争论,往往陷入一个误区,即人工智能的诞生,在不久的未来会反过来凌驾在人们之上,这种趋势进一步被新闻媒体、大众读物、电影和艺术作品,甚至电子游戏所夸大,一些并非真正研究人工智能的专家宣布要想避免出现这种状况,避免人彻底地沦为人工智能的奴隶,就需要为人工智能立法,甚至有人主张直接将人工智能“绝对遵从人类”写入人工智能代码之中。且不说今天的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已经将人为编写的代码对人工智能的限定作用降低到了一个比较次要的水平上,即便人工智能带有“绝对不能伤害人”“绝对不能奴役人”的代码,难道不会发生在美剧《西部世界》中谈到过的冥想程序让带有“绝对遵从人类”编码指令的人工智能觉醒吗?在许多人工智能的从业者看来,这些看似言之凿凿的论断,实际上都出自对新技术无比恐慌的“鲁德分子”9(Luddites),他们将人工智能技术直接置于人类生存的对立面,认为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无限度发展,最终将使人类毁灭。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看到,机器的应用是以取代工人的劳动为代价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故意将工人置于机器(“铁人”)的对立面。马克思指出:“为了进行对抗,资本家就采用机器。在这里,机器直接成了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手段。同时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在这里,机器就它本身的使命来说,也成了与劳动相敌对的资本形式。棉纺业中的走锭纺纱机、梳棉机,取代了手摇并纱机的所谓搓条机(在毛纺业中也有这种情况),等等,——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10事实上,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不过是资本家玩弄的一个伎俩,他们成功地将无产阶级对资本家的憎恨和不满转移到机器上。问题并不是真正出在技术和机器上,而是出在资本家对机器和技术的占有上,他们利用新机器和技术来对抗工人,以至于工人认为他们的敌人就是机器,这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鲁德运动”的根本原因。
同样,如果用马克思的相关结论来理解今天的人工智能问题,结果也是一样的。智能家居和无人驾驶都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良好应用,随着社会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工智能的智能增强体系还可以用来延缓人的衰落,甚至直接服务于人类,这些并不是画饼充饥,而是眼下可以实现的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认为,人工智能技术至少在现阶段是一把双刃剑。而一旦这些技术与资本进行媾和,成为其牟利的手段,并将绝大多数人排斥出去,将他们当成“无用阶级”时,问题才会凸显。这样,当人工智能时代的“鲁德分子”将口诛笔伐的矛头指向人工智能技术本身的时候,实际上,今天的媒体和政客也玩弄了同样的伎俩,本来是极少数阶层垄断社会资源,从而使绝大多数大众阶层陷入赤贫的境地,却被媒体和政客转化为人工智能即将取代他们的职业,将他们变为“无用阶级”的话语。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分析在今天仍然是有效的,即面对机器,面对人工智能,问题不在于退回到一个没有机器、没有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就在这个时代,我们没有办法回避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给现实生活带来的实际冲击,真正的问题只有一个:打破资产阶级对新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绝对垄断,无产阶级应该勇敢地利用这些机器来为我们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即走向未来的社会主义生活。
于是,关于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问题变成了这样一个问题,人工智能是否有利于在平等的解放的环境下创造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社会,来满足大众的共同福利。对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描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曾给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在社会范围内有计划地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迄今为止的人自己的生产资料对人的奴役。不言而喻,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替它们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11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不仅仅被看成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而且是彻底的人类的解放,在这里,恩格斯十分清楚,未来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消灭了劳动,而是社会劳动成为一种快乐。同样,我们也可以设想,恩格斯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并不在于消灭机器,而是在机器大生产运动中将生产劳动变成人类的解放活动。将这个语境移植到当下的人工智能时代来看,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不会是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拒绝,而是在人工智能技术、通信技术、数字技术的发展中使人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
不过,在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对分配问题的考察。恩格斯继续说道:“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这里特别是劳动力也要考虑在内。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2恩格斯认为,在未来的社会主义阶段,已经不需要用“价值”这种形式来分配各种资料,而是按照一种计划来安排,这是后来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雏形。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哈耶克对计划经济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有意识地权衡所有必须顾及的因素,它们关系到如此众多的个人的决定,因而使分权成为必要,很显然,要完成这种调节,不是通过‘有意识的控制’,而只有通过具体安排,向每个企业单位传播它必须获悉的信息,以便使它能够有效地调整自己的决定以适应其他人的决定。”13哈耶克之所以反对社会主义计划,反对集中控制,除了他本人对市场竞争调节作用的绝对信任之外,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处于集中控制的计划中央的人有着绝对的智能和信息处理能力(哈耶克还怀疑这些人的道德水平,认为人天生的自利倾向会使公正的调节失效,从而影响中央计划的公平性和合理性),来行之有效地在各个部分、各个个体之间完成最合适的调节。如果我们进一步梳理哈耶克的反对意见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哈耶克并不是真正彻底地反对计划经济,而是提出,那种拥有管控社会所有环节的能力的中央计划者不存在。恩格斯的社会主义设想和哈耶克的批评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是否存在着一个绝对智能的中央计划者,能处理庞大而繁复的信息,同时兼有绝对公正的立场,来完成中央计划的实施。的确,无论是在恩格斯的时代,还是在哈耶克所处的时代,我们都找不到绝对智能的中央计划者来公正地实施社会主义计划,这样,我们将哈耶克的批评理解为退而求其次,在没有绝对智能和绝对公正的中央计划者的情况下,只能依赖于市场竞争的看不见的手来进行调节和实现平衡。
一旦进入人工智能时代,随着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的实现,随着5G的通信技术的市场化,是否可以假定一种可能性,即哈耶克所批评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的缺陷,会被新的技术手段加以弥补。在计算和学习能力得到指数级增长的人工智能面前,我们或许可以期望,有朝一日,如此庞大的信息和数据量,如此复杂的调节和分配运算,可以在人工智能的统筹计划下完成。而且,人工智能也不会具有道德上的问题,即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人工智能拥有自己的意识,从而在资源和生产的调节与分配上,沦为满足于个别人私利的工具,从而使计划陷于腐败和不公正。即便在今天,这种面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新计划经济仍然停留在一个十分模糊的层次上,但这种未来仍然是可以冀望的。
三、新控制论与未来的社会主义
为何说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新计划经济是一个可行的选项?这并不是今天的互联网商家或者某些狂热的未来学者的突发奇想,其具有一定的理论依据。实际上,从20世纪开始,不断有信息理论的科学家和计算机领域的专家试图从技术层面上解决信息传播和数据处理的瓶颈问题,他们也相信,随着通信技术的进步与改善,会为我们提供一个更美妙的未来社会的模型。
在诸多信息科学的理论家中,起到奠基作用的是美国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他将克劳德·艾尔伍德·香农(Claude Elwood Shannon)的信息理论纳入到其所提出的控制论(cybernetics)之中。简单来说,香农把热力学上的熵(entropy)的概念纳入到信息论当中,在香农看来,信息空间与热力学空间有着一定的相似性。熵是热力学上表示混乱度的概念,由物理学家路德维希·玻尔兹曼(Ludwig Edward Boltzmann)提出,熵的值越高,意味着热量越高。那么,热力学表明,熵总是从高热量的区域传播到低热量的区域,这就是熵增的原理。香农观察到,在信息学上也有类似的情况,香农将玻尔兹曼的热力熵改变成信息熵,也被称做香农熵。1948年,香农在论文《通信的数学理论》中第一次从信息论的角度阐述了信息熵的原理,在这个时期,由于与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的二进位代码的发明相对应,香农将其转化为一个对数公式,这个公式计算出来的就是信息熵的值,这个值的单位是比特(bit)。那么对于香农而言,信息代表着不确定性的减少,也就是熵减,信息熵的减少代表着确定性的增加,即“信息是确定性的增加”14,而这个定义已经成为当代通信科学中关于信息的最经典的定义。
维纳的控制论显然是建立在香农的信息的定义基础上的。维纳说:“机器和生命体一样,是一种装置,它看来是局部地和暂时地抗拒着熵增加的总趋势。由于机器有决策能力,所以它能够在一个其总趋势是衰退的世界中在自己的周围创造出一个局部组织化的区域来。”15因此,维纳的控制论是一种自我控制,是机器能够作出对信息的反馈与决定,从而实现对各种复杂的熵的处置,以达到趋于稳定性的状态。维纳在《控制论》一书中再次强调:“整个流程由机器自动完成,因此,必须保证从数据输入到数据输出都没有人为因素的干扰,而所有的逻辑判定均由机器自动完成。”16维纳的控制机器的模型,使机器在人类的干预之外自动地实现对信息的处理和决定成为可能。
尽管维纳多次强调并不希望他提出的控制论模型被使用在国家管理和社会控制等层面上,因为维纳无法判断这种机器是否具有善恶观念,但是,仍然有不少尝试者试图从维纳的控制论模型出发,将控制论与社会主义计划联系起来。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智利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1970年11月,阿连德作为人民团结阵线的领袖参与竞选,并成功当选,在1971—1973年间,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阿连德总统试图用一种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实现他的中央计划的梦想,该计划旨在建立一种分散型决议支持系统,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该计划由四个模块组成:经济模拟器、检查生产表征的常用软件、操作室和远程电报机网络,这些模块都链接到一个电脑主机之上,由电脑主机自动地模拟出国际经济的计划的状况。之所以要实施这个“赛博协同控制工程”,正是因为阿连德看到了苏联和古巴在中央计划执行上的缓慢和平庸,无法有效地处理各种复杂的信息和状况,所以希望通过计算机和人工智能设备来实现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阿连德专门从英国邀请了控制论专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来协助他实现这个史无前例的规划。“智利为实现社会主义治理的技术性工作与英国精通管理控制论的专家的结合,产生了赛博协同计划,他们带着雄心壮志创造了庞大的计算机体系,实时地使用技术来管理智利的国民经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技术并不太尖端。英国的控制论专家与智利的社会主义的结合非比寻常,这不仅是因为英国与智利相隔千山万水,而且因为他们代表着一种非常特别的科学思想或政治思想的潮流。”171971年,最先开始实验“赛博协同控制工程”的阿连德雄心万丈,他认为自己实现了真正的“完美的计划经济”。通过电脑对各种信息的控制与决策,达到了“科学实现的完美经济平衡”,这也意味着智利会在他的领导下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然而,仅仅在一年之后,智利的通货膨胀率就达到了140%,物价飞涨。1973年,陆军总司令奥古斯托·皮诺切特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人工智能与社会主义的第一次邂逅就这样结束了。许多人将阿连德政府的失败直接归咎于“赛博协同网络”,并认为不能任由人工智能来实现计划的统筹和决策。正如艾登·梅迪纳(Eden Medina)认为的那样,阿连德和比尔的“赛博协同网络”实际上是一个很不成熟的产品,他们并没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和信息处理设备,他们创造的中心计算机处理信息的效率十分低下,根本无法处理智利国民经济的所有信息,由于信息量有限,导致智利国民经济系统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达到随机性和或然性的熵减,相反,该系统处于高度的不稳定状态,这也是阿连德政府和比尔等人的失败之处。18技术加速主义倡导者阿列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和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对阿连德和比尔的实验给出了十分公允的评价:“智利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就是这种实验态度的象征——将控制论技术与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民主平台融合起来,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是典范性的。……这些实验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归咎于早期控制论学者操作时面对政治限制和技术局限。”19
在新一代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专家看来,阿连德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并不是阿连德政治理念的失败,而是技术的失败。当时的控制论技术和通信网络都不能支持一个国家的总体规划,但是这种思路仍然是可行的。与阿连德同时期的英国学者斯蒂芬·博丁顿(Stephen Botington)就写过《计算机与社会主义》(Computer and Socialism)一书,他坚信可以用计算机模拟和智能的方式来模拟复杂的经济现象:“计算机收集和分析统计量的能力与解决设计模拟经济结构模型的问题密切相关,最终目的是模拟整个经济结构的各种活动,已作的各种努力还远不能实现这一目标。这类模型能够显示出成本变化的程度,测定新的程序对成本、生产时间等所产生的影响。人们开始使用计算机模型模拟真实情况,对现状进行研究,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可能成为一种实验科学,如同化学家做化学实验一样。”20博丁顿提出的理念不同于阿连德和比尔的“赛博协同过程”,博丁顿很重视对现实的模拟,从而以实验的方式来推演,而不是直接将国民经济的控制权交给电脑和智能机器。与之相对应,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已经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我们可以将这种方法称为智能体基模型或代理人基模型(agents-based modelling,ABM)。正如博丁顿所说,社会科学很难直接在现实领域中做实验,不过人工智能技术可以通过一定的智能行为体(agents)来模拟人类的行为,利用大数据计算和人工智能来模拟在不同模态下的异质性智能行为体的状态,“ABM方法采用了基于元素的系统视角,关注在系统中作为相关行动元的实体之间的行为和互动。ABM的视角试图用更现实的方法来表达社会和经济体系下的行动元,来克服仅限于忽视了异质性因素的相关定义下的代表性行为体的局限性,来体现各种互动的异质的智能行为体的关联含义”21。今天的ABM模型已经不是按照固定的明确属性来模拟设计者已经设想好的倾向,其中的行动元或智能体实际上是经过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具有人工神经网络的行为体,它具有自动的智能,能够尽可能产生出更多的行为结果。
我们可以认为,ABM实际上构成了一种新控制论模型,在今天计算速度和信息处理速度都大大高于阿连德时代的情况下,我们是否首先利用这种模型来尝试进行新社会主义控制论模型的实验,这种实验并不会像阿连德一样,不顾后果地在现实社会中强制推行计算机模拟出来的结果。今天,在大量数据收集和反馈的基础上,通过高度智能化的计算,我们是否可以在人工智能互动的界面上模拟出一种理想的社会主义结果来?一旦满足足够的条件设定,这种经过反复改变各种参数和环境,经过多重互动和试错之后的ABM实验结果,是否可以成为人类社会进行社会主义尝试的一种可能性?尽管今天的技术加速主义者对此十分乐观,如前文提到的威廉姆斯和斯尔尼塞克就十分明确地指出:“在社会网络分析,在ABM模型,大数据分析,不平衡经济模型中建立起来的工具,都是用来理解诸如现代社会这样的复杂体系的认知中介。加速主义左派必须熟知技术领域中知识。”22的确,今天的加速主义者和左翼人工智能学者,的确试图通过人工智能的尝试,找到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更可靠的道路,不论他们的尝试能否成功,他们的这种精神都是值得赞扬的。
注释
1[美]雷·库兹韦尔《奇点临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第2页。
2[美]雷·库兹韦尔《人工智能的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73页。
3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参考了安德鲁·尤尔在《工厂哲学》一书中的说法,将机器形容为“铁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301—302页。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302页。
5[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290页。
6[以色列]尤瓦尔·赫拉利《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314页。
7Bernard Stiegler,La Société automatique,Paris:Fayard,2015,p.51.
8巩永丹《人工智能催生“无用阶级”吗?》,载于《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6期。
9“鲁德分子”最初是对英国19世纪捣毁机器运动的参加者的称号。这一运动以传说中的工人领袖耐·鲁德(Ned Ludd)的名字命名,据说他是第一个捣毁机器的人。这一运动大约在1760年在设菲尔德和诺丁汉兴起,在1811—1817年危机期间扩大到整个英国。1812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保障治安法案》,决定对参加“鲁德运动”的工人进行残酷镇压。后来,“鲁德运动”被广泛地用于指捣毁机器运动。在人工智能时代,“鲁德运动”和“鲁德分子”被用来描述那些坚定地抵制数字技术、通信技术、互联网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人工智能时代的“鲁德分子”已经不分阶层,既包括最底层的没有太多文化的民众,也包括固步自封的政客、媒体人、人文学者,甚至不乏一些坚持传统科学的理工类科学家。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2009年版第300页。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第310—311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2009年版第327页。
13[英]弗里德里希·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14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83页。
15[美]诺伯特·维纳《人对人有用处——控制论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页。
16[美]诺伯特·维纳《控制论:关于动物和机器的控制与传播科学》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17Eden Medina,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1,p.16.
18Eden Medina,Cybernetic Revolutionaries:Technology and Politics in Allende's Chile,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11,p.224.
19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Robin Mackey and 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Accelerationist Readers,Windsor Quarry:Urbanomic Media Ltd.,2014,p.357.
20[英]斯蒂芬·博丁顿《计算机与社会主义》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108页。
21Matthias Müller,An Agent-Based Model of Heterogeneous Demand,Stuttgart:Springer,2016,p.27.
22Alex Williams and Nick Srnicek,“Accelerate: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in Robin Mackey and Armen Avanessian(eds.),Accelerate:Accelerationist Readers,Windsor Quarry:Urbanomic Media Ltd.,2014,p.357.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