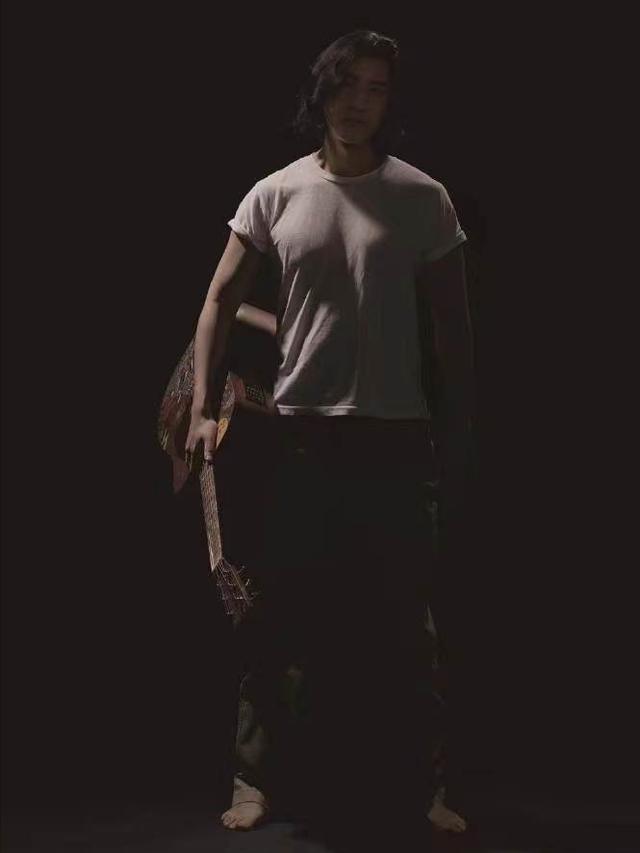小河流水哗啦啦是什么歌(小河流水哗啦啦)
作者:夜泊乡渡第三章 淘金之梦,今天小编就来聊一聊关于小河流水哗啦啦是什么歌?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研究一下吧!

小河流水哗啦啦是什么歌
作者:夜泊乡渡
第三章 淘金之梦
山村里岁月悠悠,日月如梭。转眼就过了十月,北方的天气开始转凉了。早上起来,霜晨满天。银白色的薄霜铺满了眼前的整个世界。长天雁叫,碧空如洗。一队队的大雁向南飞去,一会儿排成了个一字,一会儿又排成个人字。
王大久今天有空,就信步来到了陈集家。
陈集的家住在村东头,面朝东的两间厢房,院子不大。陈集是王大久一同回乡插队的同学,只不过他是农业户口。按照政策,农业户口的毕业生回乡,不享受知青待遇,如果说王大久是插队知青的话,那么陈集也就只能算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了。
陈集的父亲陈少庚,CD人,说话满口的川味。早年当兵,当过班长。抗战时期出川抗日,坐兵舰到过太平洋,也到过越南的沙湾同鬼子作过战。抗战胜利后,又随军到了东北。在一次大战的前夕,连长派他到抚顺东部的一个小村庄,找他们班里那两个还没有归队的战士。陈少庚只身带好了美制的卡宾枪就上了路。当他来到了村东头正待打听村公所的当口,突然从胡同里窜出了一只大狼狗,死死的咬住了他,陈少庚奋力的与这狼狗撕打起来,不得以就端起那卡宾枪开了火,“嘟、嘟、嘟,”一梭子打了出去,狼狗倒地死了。可是村民们和狗的主人也围住了这个带枪的外乡人。俗话说的好,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好虎斗不过群狼。再说了,这卡宾枪再历害,那也不能对百姓开枪啊。于是,乡党们就把陈少庚的枪抢了去,说是做为那只死狗的赔偿。那两个回村探亲的兵听到枪响也赶了过来,并趁机怂恿班长别回部队了。说当年打RB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这次打内战如果打死了多不值。再说你的枪还在人家手里,回到部队里也没法交待呀?我们三个人就都不回去了,班长,我们帮你安家吧------。这陈少庚觉得他的两个弟兄说的有道理,也就下决心不回去了。在两个战友的相帮下,陈少庚就在那个村里就此住了下来。后来,这三个当兵的都为当初的决定庆幸,因为过了不久,他们所在的那支部队就在锦州被歼。他们的战友中有很多人都死了。
陈少庚在家乡时就有木匠手艺,在村子里也就帮人盖房子赚钱。日子久了,手头有了点积蓄,两个战友就帮他在村里盖了房子。再后来又娶了老婆,就是陈集的母亲。据说陈集生下来时很好看,邻人们都喜欢。不料到了三岁时得了天花,左边眼睛被火毒蒙住,那时医疗条件落后,日久不愈,这只左眼便失明了。父母搂着儿子,常常泪流满面。唯一能做到的是对陈集更加的呵护了。这陈集至小就娇生惯养,不干活。挑水打柴所有的农活通通地不干,都是在他父母的安排下由他的两个妹妹们干的干干净净的了。陈少庚好喝酒,经常的在外边干完活回来时手里拿回斤把的猪肉,让老婆炒了下酒。那时陈家下屋里的大勺就会铛铛地响了起来,院子里飘满了肉香。然而能享受到这炒肉小灶的人,除了当家的陈少庚以外,就只有陈集了。这时的陈集就会理直气壮地坐在他老子的对面,父子两人慢慢的吃将起来。两个妹妹也会知趣的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王大久小时候常到陈集家里玩,对陈集在家里的地位和伙食等级时常羡慕不以。长大后的陈集倒也天性风趣,每每异想天开,幻想不劳而获,发笔横财。所以,时常的闹些笑话出来。
刚好今天陈集在家,王大久一走进去,陈集就热情的招呼他快坐下。口中急急的说到:“你来的正好,不然我还要找你去呢。”
“什么事?”王大久问。
“我昨天下午刚去汇钱回来,有一件事要告诉你。”陈集喜形于色的说。
“给谁汇?汇钱干什么?”王大久问。于是陈集讲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陈集前天在一本杂志的封底发现了一则报道,说是种植名贵中药叫什么红花的,种一年连收十年。这期间还不用田间管理,每年只坐等收成就行了。说是要想种这东西,把种子钱汇过去就行,很快的就能收到这神奇的种子。每斤260元,一斤起邮。于是,陈集便东借西凑的弄了260元,昨天就给汇走了。
王大久被吓了一跳。260元啊!这不是小数目,每天早出晚归的辛苦劳动一整天才能赚到八角钱。260元,这可是普通社员一年的收入呀!再说了,这杂志的消息能保真吗?王大久的直觉告诉他,陈集上当了,他被骗了!
“快去邮局!快去把你汇出的钱扣下!快去!你被骗了!”王大久对陈集喊道。陈集怔了一下,说:“不能吧?书上写的能有错吗?”
“快点去邮局封款,听我的!这可能都来不及了啊。”王大久急了,大声喊到。陈集这才重视起来,感到有些慌张了,急忙找邻居借了辆自行车就往邮局跑。王大久也不走,就站在陈集家的院子里等待他回来的消息。
好一会,陈集回来了,哭笑难辨的表情不知是喜是忧。
“怎么了?邮局把钱汇走了吗?”王大久急急的问。
“昨晚下班前就汇出去了,来不及了。”陈集悻悻地说道。接着又说:“也好,还许能寄来种子呢。”
“等着吧,看看能不能给你寄来金种子。”陈集这个蠢才让王大久很无奈。“等几天呢?”王大久问。
“等他个五天,我看能寄来,到时你就等着我发财吧,哈哈哈------”陈集并不知道发愁。
王大久眼前浮现出动画片里巴依老爷的样子,于是他就戏谑地说道:“种沙子、收金子,沙子一袋子,金子一屋子,哈哈哈------”他也大笑起来。
“王大久啊,说不定这种子来了,种一年收十年,一斤种子能种两亩地,每亩能收五十斤,每斤能卖一百多元啊!再连收它十年,我陈集就从此就发迹了啊!当年成立共产国际的时候,谁能想到中国红军打下了天下?这人活在世,就要敢想敢为,说不定哪次碰对了,我就当他个碾盘公社的首富!到时候你也跟我借借光啊,我请你天天吃大鱼大肉!”他嘻嘻地大笑起来了,已经忘乎所以。
“等五天看吧,天下哪有这种好事,种一年收十年?你就等着上当吧,只怕是血本无归。”王大久说。
树叶黄了,庄稼收了,深秋的山风越刮越凉。一九七零年的初冬就要到来,北方农村基本上进入了冬闲季节。但是天闲人不闲,波澜壮阔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正浩浩荡荡的开展起来。板桥沟里的山坡上,人头攒动,红旗招展。山坡上耸立着几个红色的大字,“学、大、寨、大、会、战”。全大队的社员们正在战天斗地,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王大久和几个男知青正在山坡上修梯田。
忽然,不远处聚起一堆人来,还有些人正不断的拥向那里。王大久和李维翰也放下手里的活,去看看发生了什么。挤到跟前一看,原来不知是那个生产队里的人在修梯田时,挖出了一具骷髅,由其是那个脑袋,两个窟窿甚是恐怖。可就在人们争着看的时候,不可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只见那个骷髅脑袋,瞪着两个大大的窟窿眼睛,在众目睽睽之下,一点点的移动起来,开始时大家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很多人都把眼睛揉了又揉,以为是看走了眼。随着众人的尖叫声,那骷髅脑袋动的更加频繁了!幸亏是在大白天里,又是人多势众,不然,谁还敢看!王大久就站在这个诡异骷髅头的最近处,它的每一点移动他都看得清清楚楚。仗着人多,大多数人都没有逃走,想要看个究竟。可是这个骷髅头非但没有停下,反而运动的幅度越来越大,并且开始慢慢的旋转起来------这不是活见鬼嘛!
这时,天上漂过一片黑云,光线陡然暗了下来。一阵阴风从人们身后吹来,大家都不由得打了个冷颤!人们再也支持不住了,四散逃开。王大久和李维翰这两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随着人流逃开了。大家都无心再干活了,谁都不敢再呆在这里,管他什么学大寨不大寨的,回家再说!不论队长怎么叫喊,逃离的人群像洪水一般,谁也挡不住。
只是王大久心有不甘,他感到太离奇,不可置信。他停下脚步,对李维翰说道:“维翰,我们不走,我们要弄清楚这倒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我们发现了什么未知的东西,这将是最有价值的,说不定可以改写教课书。”于是,他俩人仗起胆子,一步步的回到了骷髅头的地方。这时的骷髅头,以经从原来发现的地方,移动了大约有两米远了,它没有停止,还在左右的摆动着,仿佛在向他俩示威。李维翰拿出火柴,划着了一支,他听说鬼怕火。王大久心里一动,跑到山坡拾了些干柴用火柴点燃,然后把着火的干柴纷纷投向正在摆动着的骷髅头。这骷髅头被火一烧,竟然发出:“呱!”的一声鸣叫!李维翰掉头就跑,王大久没有动,他下决心要看个究竟,弄个水落石出,这是他的性格。一件不可预料的事情发生了,足以让全世界为之无奈。只见一只青蛙从骷髅头眼窝的窟窿里爬了出来!王大久恍然大悟,原来是这只青蛙在骷髅头的里边蹦跳戏耍,以使得骷髅头不停的动弹。李维翰回来了,两个人此刻就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此前好事探奇的心以被揪到天际,结果结局竟是这样的让人涕笑皆非------
这件事情后来被人们传的越来越远,以至于整个公社都知道了。所不同的是版本变了,都说是王大久避邪,一把火烧跑了鬼魂。至于那天学大寨修梯田被搅散被破坏的事,县里的工作组下来调查,认为王大久所反映的情况很有价值,很有说服力。晚上开社员大会时,就让王大久把当时看到青蛙的情况向大家说一说。不曾想社员们听了后,却又惊恐的振振有词起来。
“怎么没有鬼魂?那只青蛙就是!青蛙就是鬼魂的化身!”大家都这样说,七嘴八舌。倒底是村民们的先知,还是他们的无知,这让王大久哭笑不得。工作组的人见说不明白了,越抹越黑,也只得干脆作罢了事。
青蛙事件过去了之后,大寨还是要继续学的。像所有的运动一样,一窝蜂。SX省的大寨公社大寨大队梯田修的好,这种经验被硬性的推广到全国农村学习,也不论山势地貌环境,也不管地理条件适不适合,就必须要学着干。好不容易种熟了的熟土被翻到了土地的深处,新土、生土却被翻了上来,来年什么都不长啊。但有谁敢说呢?农民们吃不饱,自留地少的可怜,种点菜只能勉强够自家吃的。不让开荒种地,不准养大点的家畜,就是鸡也有限制,割资本主义尾巴把家家户户都割的干干净净。年底工分的收入本来就少的可怜,扣除了往来账就不剩什么了,农民很穷。大家都在想,怎么能弄点钱花呢?村子里有几个不太安分的人,置被法办于不顾,偷偷地到锦州的大虎山贩点大蒜回来贩卖,据说是赚到了钱。这消息很快的就在村子里漫延开来。钱这东西让人眼热,让人心动,由其在贫穷的时候。可这是“投机倒把”呀!如果被人抓到,轻者被没收,血本无归不说,还要进学习班里“学习”,重者那就是直接被抓进班房。
初冬里的一天,王大久和社员们在修梯田。休息的时候,李维翰走了过来,递给了王大久一只红梅瑰牌纸烟,这种烟二角八分一盒,在男知青中很流行,但王大久在更多的时候是买不起。
“歇一会,聊聊吧。”李维翰说道。
“好,唠一会。”王大久说道。
“你听说了没有,我们队有几个人投机倒把都赚到了钱。”李维翰一脸神秘的说。
“我们也干!”王大久猛吸了一口烟,狠狠的说道。他以经很穷了,连买烟的钱都没有。
“好,晚上我们核计核计,你来知青点找我。”李维翰把烟头一丢,走了。
吃完晚饭,王大久和李维翰来到队里场院的草垛上,开始秘密的商量起投机倒把的事情来。这种事是坐监犯科的,保密那是最当紧。俩人首先是选择贩什么?到什么地方去贩?即然别人都能成功的贩大蒜,那我们也就跟着学呗,也贩大蒜。说实在的,像王大久、李维翰这种刚走出校门的知青,说白了,其实还都是个孩子,能跟别人学就算不错了,还能要求他们什么呢?走别人走过的路,风险就会小一些。怎么去呢?摸不着门路啊。去求那些干过的人带着我们?不用问那是肯定不行的。王大久此刻想起来陈集曾说起过,他在大虎山那有个远房的亲戚,于是就和李维翰说好了找陈集一同去。两人商量好了时,以是繁星满天了。
那异想天开的陈集至打把钱汇走了之后,又经王大久的一通责备,心里也着实的没了底。260元呀,不是小数目,都快够娶个媳妇的了。这要是没了影、打了水漂,那可都是西拼八凑借的啊!五天等过去了,又是五天过去了,陈集开始寝食难安了。怎么办?,再等它五天!又是五天过去了,还是没有消息,只能再等五天。就这样,几个五天都过去了,那神奇的种子,就像他的钱一样神奇,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毫无疑问,他必须为他的天真、为他的异想天开付出代价!此时的陈集,一会像热锅上的蚂蚁,在自家的院子里转来转去。一会又如遭霜打的秋草,垂头丧气,把头深深的埋入胸膛,蔫的无声无息。
“陈集,陈集------”是王大久来到了陈集家。
陈集一下子站了起来,“来了,大久。哎!当初听听你的意见就好了啊!”他唉声叹气的说。
“你告诉我时就已经晚了,在你还没有汇出钱时,为什么不与我商量一下?”王大久责备道。“报案吧。”王大久又接着说。
运动初期,公检法都以被砸乱,这两年也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恢复,说是报案,只不过是了却心思而已。陈集最后到底报没报案,王大久就不得而知了,反正是这件事从此再无声息。
王大久接着就对陈集说了打算偷偷的到大虎山贩大蒜赚钱的事,陈集正愁找不到赚钱的地方呢,王大久的话正中下怀,两人一拍即合。好在贩大蒜所用的本钱不算多,每人本钱加车费、吃饭等费用,有五、六十元就够了。
“大蒜我看行,我都好几年没吃到过大蒜了,市场上也看不到卖的,缺货呀!”陈集的声音提高了很多。
抚顺这个地方不产大蒜,最近的地方也是辽西平原上才有。计划经济时期,加上特殊时期运动,农副产品不流通,大蒜就从抚顺百姓的餐桌上消失了。陈集又提出带上赵宝安,那是他的亲戚,好事不能忘了他,他自己负责通知。王大久也不反对,赵宝安平日里与他的关系也不错,还算合的来。这样的算起来,李维翰、赵宝安、陈集,加上他王大久总共有四个人。人就这些了,不能再多了,要先开个会,王大久此刻心里盘算到。
当天晚饭后,四个人约好了开会。家里人杂,为了保密,几个人来到了队里的草垛上。这草垛真正的好,可以坐卧自如,不冷不累不脏,还柔软还僻静,还可以抬头看月亮,是个开这种会的好地方。四个人紧张的有些兴奋,七嘴八舌的定好了从明天就开始筹钱,钱备好了就走。由于陈集的亲戚就在产蒜区大虎山,他便自报奋勇要带领大家投奔而去,所以,陈集也就自然的成了这次站役的总指挥。
那天晚上,在初冬惨淡的月光下,四个人谁也不可能想到,这仅仅才是一场苦难旅程的开始。
赵宝安大王大久三岁,别小看了这区区的三岁,在人这种高等动物的发育史上,由其是在青春期,那就是有很大的区别了。王大久每天劳动,快乐也好、烦恼也罢,他想的尽是些理想、前途。他才十八岁,对于异性,只能说是刚刚有一丁点的小感觉,就这一点点也是过后就忘了,说到底,他还没到那个年龄。赵宝安就不同了,他已经懂得了爱已经开
始关注异性,对异性产生了强烈的需求感。他的心里,总在想着一个美丽俊秀的姑娘,她就是李玲。离村子不远的小镇上有一家电影院,正在放映朝鲜电影【南江村的妇女】。前晌有空,他怀着忐忑的心情偷偷地去买了两张晚上的电影票,想与李玲两个人一起去看。可是他手拿着那张电影票,就是没有勇气交给她,他怕遭到她的拒绝。下午派工时,他来到知青点,真是天公做美!女宿舍里只有李玲一个人。赵宝安鼓起勇气,把一张电影票递到了李玲的面前,颤声颤气的说道:“李玲,我、我想,我想请你看电影。”李玲一怔,脸一下子就红了,她一时手足无措。
“大、大家都去吗?”李玲低声的问道。
“不是,就、就我们俩。”赵宝安终于勇气了。
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默。
“我不去了,我------”李玲把头埋的更低了。担心以久的事情最终还是发生了,李玲拒绝了他!赵宝安先是沉默,然后昂起头,再就是一脸的羞愧和愤恨。
“我不配啊,地主不配啊------”赵宝安悲哀地说道。他把那张电影票恼怒的扔在了地上,转身离去。
李玲手捂着脸,哭了。她捡起了地上的电影票,小心地把它踹进了衣袋。
晚饭前,赵宝安来到王大久家,送给了王大久一张晚八点开演的电影票并告诉他演是【南江村的妇女】。这个电影是王大久早就想看的了,只是一直没有机会。
“你也去?我们两个?”王大久高兴的问道。
“我不去,就一张票,别人送我的,我有事,去不了了,扔了白瞎了,所以,你去看吧。”赵宝安遭到李玲的拒绝后,就已经没了再去看电影的雅性了。他不忍让电影票作废,就送给了王大久。
“好就是好,遗憾的是没有个伴,就我自己。”王大久说。没等说完,抬起头,看到赵宝安已经走了。
小镇上的电影院不算远,王大久骑上了爸爸的自行车,在傍晚的凉风中,半个小时就到了。八点,电影开演了,当电影院里响起那朝鲜民族特有的舒情、悠扬的旋律时,王大久发现身边原来一直空着的座位,此时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李玲!
当赵宝安愤恨地离去后,李玲偷偷地哭了很久,她想起了他和赵宝安的一切。李玲的父亲远在“三线”工作,所谓三线就是国家从战备考虑,把需要重点保密的军工、冶炼企业调离都市,迁往边远农村山区,这是七十年代的国策。李玲的母亲患有严重的风湿,几乎是长年卧床。她是家里的老大啊,每次回家,她都发疯的干活,她想把她不在家时所有的活都干完,然后再走。对于赵宝安,说实话,她喜欢他。她喜欢他清秀白皙的脸,也喜欢他肯干憨实的样子。他对她好,她知道。队里干活时,只要是赵宝安在身边,一准能帮着她干。苞米成熟时,他总是趁晚上开社员大会时偷偷地给她带来两穗。多少次她接触过他那深情又火辣的目光,她怎么能不知道他的心呢。可是,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是阶级敌人呢。跟了他,不但自己回不了城,把家里也坑了啊。家里还指望着她呢,她是家里的顶梁柱。她手里捏着电影票,就这样的想着。去不去呢?不能去!她告诫自己。
傍晚时分,望着村里袅袅升起的炊烟,她想起了赵宝安,那个对自己一往情深的小伙子。如果他不是地主成分多好!他哪里不好?不就是地主家庭吗?这不是他的错啊!这不是他的错、这不是他的错,她这样的念叨着,猛的向村里疾步走去,她来到一个社员家,借了辆自行车,毫不迟疑的向小镇的电影院骑去。
王大久怎么也弄不明白,自己怎么就和李玲一起看了场电影,他整不明白为什么李玲会坐在自己的身边。难道是巧合?那她一个年轻姑娘为什么晚上看电影不约一个同伴?她能自己一个人来?想来想去,他明白了,他的这张票是赵宝安给的,一定是李玲或赵宝安买的票,结果是赵宝安没来,这其中定有原因。管他呢,呵呵,先看了电影再说。散场回村时,俩人分别各自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回了村,一路无话。至于电影票的原由和自己的经历,王大久没有再对谁提起过。他想他应该对赵宝安和李玲两人负责,所以一直守口如瓶。他只是偷偷地告诉了赵宝安,那晚李玲去了。
当陈集找到赵宝安对他说了要约他一同前去贩大蒜时,赵宝安很感意外,也很感动。说实在的,有谁能愿意联系他这个地主出身的人呢,更不用说干这种坐监犯科的事了。赵宝安对王大久、李维翰向来是很钦佩的,也愿意和他们一起打交道,当即就一口答应,一起去,由其在他这么贫穷的时候。
初冬的天气有些寒冷,瑟瑟地北风卷起大地的荒凉抛向空旷的苍穹,又在电线杆子上发出呜咽地响声。田间农舍都冷飕飕地,显得一片萧条凄凉。入冬以后,落雪之前,这是一个灰暗的季节。
那天下午,他们四个人分头悄悄地出了村。为了掩人耳目,他们是分开走的,定好了在抚顺的南站汇合。然后,他们再坐火车到沈阳。开往大虎山的火车是晚上九点多的,这时候他们已经买好了开往大虎山的车票,正坐在候车室里等着上车。按计划,火车夜里两点左右到达大虎山站,然后凌晨五点,再从大虎山站换乘开往青堆子站的短途火车,于明早八点多到达青堆子镇,再然后去赶青堆子的早集,在那集上买他们需要的大蒜。青堆子的集不是天天都有,而是每逢农历的三、六、九才有。他们是初五动的身,正好赶第二天初六的集。这么祥尽的计划,这样周密的布署,都承蒙于陈集的亲戚,为此,陈集专程跑了镇里给他亲戚还打了个长途电话呢。
此时的陈集有点兴奋,可能是暂时的忘了他买种子的事了吧,也可能是他头一次当大家的向导、首领。等车的时候,他就充满幻想的说起这次贩蒜如何的赚钱,再如何的接着干下去,再如何的怎么安排这些钱……,他已经想入非非了。王大久不时的提醒他注意,别让人家听到了,由其是乘警。他这才转变了话题,又说起他从前的经历来了。
有陈集在就是不会寂寞,他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陈老,讲个故事听听。”李维翰助兴的说道。由于陈集说话风趣,还总是揺头晃脑的有点古人之风,早在上学时,王大久就给他起了个外号“陈老先生”。谁料想却一路飘红叫的很响。只是日子久了大家又给简化了,直接称呼他为:“陈老”。陈集似乎对这个称呼感到很是受用,也就欣然地领受了。
“陈老,讲啊。”王大久也说道。于是陈老就讲了起来。
他说那是他的亲身经历。他十几岁的时候,晚上时常出去玩耍,有时玩到深夜回家很晚。一次半夜里回家,薄云遮月,阴森森惨白的月光洒在静悄悄的山村里。当他刚刚推开院子的大门,就发现有一个影子站在他家的院子里,模模糊糊像是背对着他,也看不清是男是女。起初他以为是他家人出来起夜,但走近了一看,那影子好像没有下半身,只是一个上半身浮在空中。这时他感到头发倒竖,浑身发冷,已经喊不出声了。他想跑,已经迈不动腿了。这时,只见这半个身子诡异地在院子里舞动了两圈,然后就升空不见了。
“外星人吧?”王大久打趣的说。“肯定是没看清,你眼神不好,哈哈。”赵宝安打趣的说。
“你胡说八道!我眼睛怎么了,告诉你,我眼神不比你差。”见有人说起他的眼睛,陈集不高兴了。
这样的胡扯着,不觉中开始检票了,四个人上了车。对面的木制座椅,很老旧,有点像铁道游击队打票车的那个车厢。王大久喜欢坐火车,喜欢旅途中的新鲜感和那种未知性,喜欢旅行中的偶遇和发现。但这次不能说是旅行,只能说是一次行动,一次冒险。如果说对于到达目的地的想往,还不如说是对钱的渴望,他太需要钱了。
李维翰、赵宝安、陈集,王大久这四个年轻人,怀着对现实生活的迫切改善的强烈想往,就这样的踏上了征程。他们中没有宽裕的人,每个人的身上最多也就几十元钱。他们省略了所有能省略的消费,路上几乎是不吃不喝。饿的急了,就吃口家带的干粮,渴了就到车厢的侧所里用手捧点自来水喝。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敢轻易的花钱,谁知这点钱买蒜够不够呢?他们的行装简单的不能再简单,每人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之外就只有两个大口袋了,那是他们打算用来装蒜用的。陈集最简单,连牙具毛巾都没有。
带着四个人对前方未知的美好与忐忑,列车奔驰在广袤的辽西平原上。蒸汽车头的喘息与车厢的震动声回荡在黑暗的原野里。下半夜,火车一声长鸣,大虎山车站到了。(待续)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