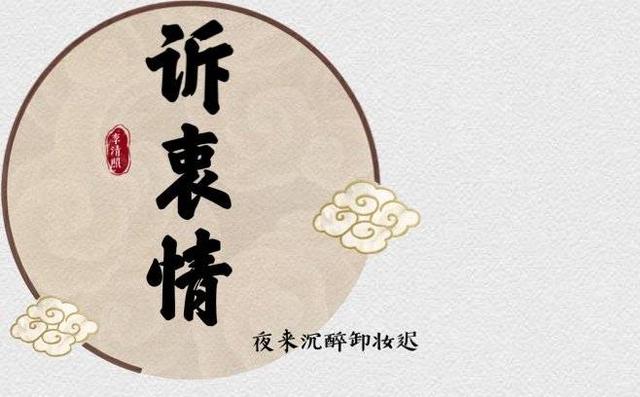一只大象的奇妙之旅(大象之路与荒原)


2020年3月,云南西双版纳的15头亚洲象组成的“大象旅行团”向北迁移,一度引起各国媒体热切关注。在相关部门的悉心呵护与全力推动下,“断鼻家族”终于于2021年8月8日返归故园。转眼一年过去,又值8月12日“世界大象日”来临,让我们再度将关注投向大象,思量人类与大象、与自然的相处之道。
“长者”
头象长久地伫立着,一动不动,凝视观望着远方。时间以不同的方式流逝,一小时像过了一天,一天像过了一季,一季像过了一生。在它的瞳孔里,在草木稀疏的远方,暴雨的痕迹有如沙漠中的绿洲一样明显。而头象所扮演的,正是为整个象群寻找绿洲、指引方向的“长者”角色。
这一年是1993年,坦桑尼亚的塔兰吉雷国家公园遭遇了半个世纪以来罕见的干旱。在不到一年间,三个象群的近百头幼象,竟有十余头不幸夭折,死亡率是正常年份的10倍。
但研究人员却另有发现:这三个象群的际遇不尽相同。有一个象群失去了10头幼象,而另外两个象群则损失不大。
原来,是它们面对干旱时做出的不同选择,导致了不同的命运。两个较幸运的象群,都果断离开了原来生活的地方,去寻找新的水源和食物。它们抵达之处,竟然有不少新生的绿色植物,还有很多泥沼和水坑。而损失惨重的象群,则因为没有勇气一走了之(即使离开,也不容易找到沙漠里的水源),不得不默默承领大自然的严酷天威。
为什么它们会做出不同的选择?研究者的目光最后集中在头象身上。
就在30多年前,塔兰吉雷公园也曾发生过严重的旱情。但是,未能走出困境的这个象群里,没有一头大象足够年长,也就不曾记得甚至也没有经历过当年的灾害。酷烈的生存记忆,显然没有深入刻进它们的骨血。而离开原地的那两个象群,头象分别是38岁和45岁——它们对曾经的那场干旱,有着铭心刻骨的记忆——虽然它们当年只不过是未成年的小象。大象有着令人称奇的记忆力:可以长时间记住某样事物,甚至长达几十年都不会忘记。干涸的恐怖记忆更是历久弥新,驱使它们未雨绸缪,果断行动,终于救下了整个象群的性命。
在一小片丛林之下,珍稀的雨水渗透至林木根部,过后又无迹可循。在寻常年份,荒漠上的某处水源可能每隔8个月才会出现。在缺乏水源的非洲,一个由三四十岁的“长者”带领的象群,兜兜转转,长距离艰苦跋涉,最后总能找到某个救命的水塘。相比之下,因为偷猎或意外死亡而导致只剩下年轻首领的象群,就经常找不到有充足草料或者水源的栖息地,导致死亡率急剧上升。
象群在代际转换中,在探索环境、争斗、防御、社交、安抚、繁殖、游戏等各类活动中,有着隐性的本土生态知识在神秘流转与传承——它们能高度精准地记住食物、水源和矿物质的位置,而正是头象,充当了“象群大学士”、象群生态知识掌握者的角色。所以亚里士多德就曾形容大象是一种“在智慧和思想上超越所有其他动物的动物”;现代动物行为学家也因此认为,大象是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在象群踏入安危莫测的领域之时,母头象或年长雄象行走在象群前方的情况居多。饱经世变的老年头象都是非常敏感谨慎的,在遇到险情前会本能地发出预警。它们知道与人类保持距离的重要性。它们见识过大量头颅被砍掉、象牙被掠夺的亲族尸骸,虽然不明就里,但冥冥中仍是意识到:人类喜欢象牙。
在陆生哺乳动物中,大象的大脑是最重的,神经元数量也非常惊人。人类分布在海马体的神经元约占0.5%,大象则有0.7%,可见大象的智力活动超出人类的想象。所以,哪怕是几十年一遇的严重旱灾,只要群体里有足够年长的老象,它就能带领后辈沿着多年前的路线,经过艰苦卓绝的跋涉,最终重获新生。
神秘的交流
大象的脊椎犹如一座拱桥,非常机巧地支撑起身体的重量。这数以吨计的庞然大物,实际上是用足尖走路的。
大象的奔跑速度非常快。在我们的印象中,它们行动迟缓,不会跑,顶多只会健步疾走。但实际上,它们的行进速度可轻易达到每小时24公里;速度最快时,甚至可达到每小时30公里。
大象的四肢粗大如圆柱,脚掌里有一块很有弹性的海绵垫,能有效减轻行走时所产生的冲击力。这个“减震器”使大象走路时像猫科动物一样无声无息。在雾气弥漫的丛林,它们常常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身后,给人一种突然降临的错觉,无形中增添了更为迫人的气场。
脚底的海绵垫除了减震,还能敏锐感知地面震动。通过次声波,大象可以向30公里外的同伴传递信息。比如说同伴失联时间有些长了,它们就用跺脚的方式给同伴发信号。而它的同伴,居然也能用脚来“收听”远方的信号,如果这声音来自自己的象群,它还会做出回应。
大象还可以发出几十种不同的鸣叫,有时是高声尖叫,有时则低沉压抑。二十年前曾有科学家进行观察,大象发出的是一种低频声音,与几公里以外的同伴进行交流全无障碍。它们从喉咙里发出的这些低频声波或次声波,尽管人的耳朵无法捕捉,但却能传播很远。
在杂乱不堪、相互干扰的声波频率中,大象还能准确区分方圆一公里内上百同伴的差异,准确识别出自己最关切的声音。如果是熟悉的声音,象群一般会情绪如常。但如果声音有异,它们通常立即就警觉起来,聚到一起,躁动明显,有时候甚至会集体扑向声源地,一探究竟。
凭借非同凡响的听力,视线之外的雷雨声都会被它们尽收耳际。
大象体积大,但同时浮力也很大,它能够轻松渡过宽阔湍急的河流。有的地方,大象甚至能在浅海边游泳。这时象鼻就发挥了另一个顺理成章的功能——当完全潜到水面之下,可以通过鼻子呼吸。
相比于亚洲象,在非洲生活的野生大象,它们在迁徙途中,站着睡觉的时候更多,因为站立能更快地在危急时刻做出反应。为了确保安全,象群里的成员还会实行轮流睡觉的制度,轮流站岗,稍有什么危险的苗头,就会发出示警。
“大象地图”
奔走在荒野大漠,象群只是在被动地适应着环境,说走就走,一意孤行,挥洒着自然界不可羁绊的野性、自由和被生存本能驱动所释放的能量。它们穿越密林,翻山越岭如履平地,迁徙能力之强令人咋舌。
大象的智商相当于6~8岁的人类孩童,它们能精准记住大面积区域内食物和水源的位置。它们有着独特的思维能力,记忆是它们的地图,经验是它们的智慧。
在漫长的旅途中,象群经常要穿越沼泽地。许多身形灵巧的动物,都会将沼泽视为恐怖的葬身之地,而身材庞大的大象,是怎么做到如履平地的?
其实,大象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族群的“路标”。
每一群大象在穿越沼泽地时,都会用它们的象鼻,将沿途树丛一边的枝叶,进行明显的折损行为。于是在危险的沼泽地上,常有一行树丛,一边枝叶茂盛,而另一边则几乎没有任何树枝和树叶。沿着这样的树丛走,可以避开不少险境丛生的泥潭。
鸟类、鱼类和两栖类动物都可以使用地球磁场导航。地球的磁场,形状好比一个巨大的磁铁棒放置在地球中心,铁棒两端大致指向南极和北极。它既可以帮助动物确定自己运动的方向,又可以帮助动物精确定位。
2020年“断鼻家族”北上,就有学者提出,这些亚洲象一路向北,有可能是烙印在其基因中的迁徙本能偶然间被激发,这可能与太阳活动有关。而在事实上,此次象群开始北上的时间,正与太阳风暴、地磁暴发生的时间吻合。
对于象群而言,只要是它们行经的路线、嬉戏过的池塘、用过的水源地,都会被它们清晰地印在脑海里。它们的地理感,得益于数代相传的经验,迁徙的路线会成为记在心中的“大象地图”,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友情
大象是一种社会程度非常高的动物。它们生性天真,极具智慧,如藏牙、役鼻、泣子、哀雌等,这些习性无不显示出很高的灵性。它们与人有交流感应,能领悟人的意图,也具有知恩图报的意识。
大象和人一样,有自己挥之不去的伤心记忆。人类育象员们有时就会睡在小象身旁,当它们在梦呓中喊叫的时候,育象员的安抚让它们有了睡在母象身边的感觉。非洲有一头孤儿象,在分离近40年后,还能轻易认出自己幼年时期的育象员。
在肯尼亚研究非洲象的科研人员达芙妮曾收养过一头3星期大的小象,临时充当它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它长到6个月。然而,就在达芙妮短暂离开它的10天里,小象出人意外地绝食而亡。达芙妮深受震撼,她得出一个伤感的结论:“当幼象对某个人过于依赖,这种依赖就会变得生死攸关。”
“地球组织”创始人劳伦斯·安东尼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有一次他去探望象群,妻子凯瑟琳娜和他的新生孩子维嘉陪在身边。安东尼忽发奇想,举起自己的孩子给头象看。只见头象“转身消失在树丛里,没过多久又重新出现,身边是她新生不久的孩子。她也来给我看她的后代了。我是一个科学家,但这件事情我想了很久也无法解释——就像是魔法般的一瞬间。那一刻我们之间有了特殊的连接。”
有专家研究了南非西开普省克尼斯纳大象公园中大象与人的“交往”,最后得出结论,尽管他们的野性气质从未通过选择性育种得到改变,尽管现今多数野生大象都很难控制和驯养,但总体而言,从小驯服的大象可以轻松地与饲养员形成亲密的关系,并优先与对他们有更大善意的人类互动。尽管大象对人类的反应可能仍有难以预测的一面,但仍可看出,它们一旦与人类形成某种温暖而亲切的联系,就会很珍视这样的关联,甚至可以成为照看人类婴儿的保姆。
至于其他生活在荒野中的大象,它们对人类仍怀有敌意,但是当它们一旦认定人类不会伤害它们时,便会信任人类,愿意主动来到人类的营地附近,喝水觅食,同时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破坏。有些大象甚至会有保护自己的“人类朋友”的冲动,在其他野象或其他猛兽想要伤害人类时阻止对方。比如在中国,傣族先民刚刚迁徙至澜沧江畔时,在新辟的村寨旁,会广植翠竹、芭蕉,诱大象来食。象群一到,张牙舞爪的虎豹就会退避三舍。
创伤记忆
虽然大象的仁义和温驯人所尽知,但这并不意味它是逆来顺受的性格。如果人和象在丛林里迎头相遇,双方都是猝不及防,就可能出现以命相搏的局面。如果有成员被杀死,它们会集体报复。现代生物学家认为,大象是为数不多会表现出创伤后应激障碍特征的动物之一,会出现反应异常、行为难以预测、侵略性增强等症状,出现比如掀屋倒树等不加选择的破坏行为。
在西方,有关大象复仇的记载有很多。墨西哥驯兽团有一头名为珍宝的大象,在多年后杀死驯兽师托雷兹的故事,听上去像是小说,但却是20多年前真实发生的事件。
托雷兹长年酗酒,生性残暴,驯象时经常用尖棒和电棍殴打动物,珍宝也深受其害。后来托雷兹终于退休,动物们获得了一段较为平静的岁月。然而有一次,当托雷兹偶尔在驯兽团出现时,瞬间勾起了珍宝的创伤记忆,它直接上前,一脚使其命丧黄泉。人们这才多少明白,在珍宝憨厚迟缓的外表下,其实压抑着一片极度痛苦的惊涛怒海。一旦达到心理承受的临界点,就会勃然爆发。
族群
即使化成尸骨多年,非洲象也认得出亲人的味道。一头大象逝去之时,家庭成员会围聚在亡者的身边,有的试图唤醒它,还有的会往亡者身上播弄泥土和枝叶,良久之后,象群才会恋恋不舍地离开。这与人类的葬礼仪式颇有些类似。
这种亲情伦理多方位地体现在象群的社会关系上。公象成年以后一般会独立生活,但它们会通过尿液来识别个体,牢牢记住兄弟姐妹的味道数十年,这样无形中避免了近亲繁殖产生不健康的后代。
在经历一些突发事件后,比如荒原征战或与另一个象群竞争后,家族成员常会集中在一起,相互磨蹭触碰。这种行为有助于家族成员增进感情,让家族更团结。当感受到其他同伴的不安时,大象会用象鼻去触碰同伴的头部,以示安抚。
幼象在两岁前完全依靠母乳喂养,有些甚至到4岁才断奶。在它生命的前8年,几乎与母象寸步不离。亲子教育和技能培训,则会一直延续到小象长到十几岁的时候,这一点几乎和人类没有区别。
幼象对母象的依赖程度和在群里的受宠程度,超出人们的想象。大部分小象都有好多个姨妈充当“养母”角色,当小象遇到难题时,母亲和养母都会尽量帮忙。哪些是与危险有关的信号,如何寻找远方的食物和水源,盐巴可以在什么样的土壤里获取,这是它们共同的教学内容。拥有3个以上养母的小象,其健康成长的概率,数倍于类似动物园等环境里那些没有养母的小象。
扩展到整个象群,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组织严密的母系社会。
象群首领通常由最年长的母象担任,首领的姐妹、堂表姐妹以及这些亲戚未成年的后代,也会待在同一个群落里。它们关系紧密,彼此忠诚。这样的“社会”,我们可以想象为一组组相互交错的同心圆。每个成员几乎都认识群体中的所有伙伴,头象甚至能同时掌握30名家族成员的踪迹,这样卓越的才能,无疑非常有利于群体的管理。
象群的规模,一般从10头以下到30多头不等,在非洲一些地区,或迁徙途中,有时会有来自多个象群的上百头大象聚在一起。
而公象则游离于象群之外,它们似乎无忧无虑地在外游荡,随着年龄增长而越发独立。它们独来独往,落得悠闲自在。但相较于性情温和的群象,独象显得敏感易怒,毫无征兆就对人畜发动攻击的可能性更大。群象因为有保护幼象的重任在身,一般不会主动挑起“边衅”。群象如果与人类发生冲突,一般都是因为幼象。
当然,到了交配时节,独象也可能会收敛一点“个性”,纡尊降贵地在群里短暂停留。这个阶段对象群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他们这些在外漂泊的“社会象”,会对群里的年轻公象起到良好的管教作用。
可以看出,大象难以在圈养的环境下得到很好的养护,一旦离开族群和熟悉的生活环境,它们甚至会终生郁郁寡欢。
比如在动物园中,大象无法获得必需的运动量,身材肥胖(很多圈养非洲象则容易营养不良)。而且终其一生,它们都必须在混凝土上行走,导致关节都不健康。更不用说对群体生活的心理需求,那更不是人类所能给予的,动物园远非它们的理想家园。
进化与退化
象牙上残留着的重要信息,那是来自大地、母亲、山林的味道,是大象身份的可靠标记,即使尸骨仅存,相应的身份特征仍保留得相当完整。然而,象牙曾经是推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海上贸易往来的重要货物。在经历了数万年的猎杀、数百年的象牙产业和30年的国际化偷猎走私之后,大象得到了国际上广泛的保护。但是很多影响深远的恶果,却不是说停就能停。
牛津大学的动物学家前几年发现,由于体型更大、象牙更长的成年雄象遭大量捕杀,象群繁育行为有所改变,体型较小、象牙较短的雄象得以繁衍更多后代。这一趋势不断持续,导致非洲象的象牙平均长度已经缩短。
就像达尔文的感悟一样,进化并不必然导向更高级的事物。进化之路实际上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是其所是、应其之命就是其本质,就是最高的法则。只不过物种一般历经数千年进化后,才会出现明显进化结果,但非洲象的象牙长度出现显著变化,仅用了大约150年。
非洲大象被迫进化的后果,正是源自偷猎者大肆猎象以获得象牙的行为。人类对大象的屠杀,正在逐步改变它们的性征,并遗传给了后代——长有漂亮象牙的公象是盗猎者的垂涎之物,当这些公象被屠戮殆尽后,长有粗短象牙的母象开始成为猎杀目标。那些没有象牙的母象侥幸得以存活,但无牙的特征,却以遗传的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后代。于是不再长牙的小象越来越多,它们以此表达着自己免受盗猎之苦的生存意愿。
自19世纪中叶以来,非洲象的象牙平均长度已缩短一半。在莫桑比克戈龙戈萨国家公园里,那些幸存下来的、现已迈入老年的象身上有一个特点——它们很多都没有象牙。幸存下来的无牙母象,生育了更多无牙的后代。
从理论上讲,猎人应该等到大象自然死亡后获取象牙。但当哪怕最小的象牙都能卖出很高的价钱时,迫不及待、利欲熏心的当地人,早就无法抵御巨大利益的诱惑。非洲象牙的平均重量,也早就从1970年的24磅降到了20年后的6磅。无论是小象还是母象,只要它们长出了牙齿,哪怕象牙再小,它们都会成为捕猎的对象。
这令人感觉有些心酸的“进(退)化史”,还不能道尽人类对野生象的所有影响。
如前文所述,象群可以通过声音,告诉同伴自己的位置;听到声音的大象,则有能力分辨这声音源自敌人还是友朋。然而,当研究者对那些经历过偷猎和扑杀、失去年长同伴的“孤儿象群”播放试验声音时,得到的却是各种紊乱的反应。象群可能对熟悉的声音感到惊慌,夺路而逃;也可能对危险的异响浑然不觉,充耳不闻,完全不懂得该如何正确应对潜在的威胁。盗猎的影响并没有随着盗猎行为的被禁而止息,相反,那些不恰当的行为和反应,作为混乱不堪的基因指令,仍在无声无息地传递给下一代。
当野兽向人类走来
2020年3月亚洲象北迁的新闻,一度引起各国媒体热切关注,成功地将全球观者的视线引到山林薮泽,让我们在对自然的沉思中,重新把握世界的真实容貌。对人类与亚洲象关系的深远思量,也蕴涵着人类对家园梦想、对人类历史与未来走向的领悟与追问。在大象沉稳缓慢的步履中,人与野生动物的互动模式正在悄然更改。
在非洲,当地人和野象共生在同一片稀树草原的生态系统之中,人与象彼此反馈,协同演化,常常互为因果,显然并不总是简单地由一方决定另外一方。有些当地人的生活和大象很像,逐水草而居。大象的迁移,可以为贫瘠的土地提供肥料、吸引来各类小动物为其松土,对植物间的更快演替、缓解荒漠化大有益处,对维持种群的遗传多样性也很重要。由于大象们吃进的各种植物种子大多不会被消化,于是吸引、滋养了大量的食虫鸟类,随大象的粪便在各处安家滋长。
象群行经之处,能够在密林中踏出象道,为其他很多动物提供了很大方便,让它们都有路可走,对动物的有效扩散起了促进作用;有的物种就靠着大象夷平的树木挖洞取水,还有一些动物会把被大象挖过的地方当作自己的栖身之所。在非洲就有一种蜥蜴,喜欢选择被大象推倒过的树木作为栖息地。在亚洲的某些雨林地带,亚洲象的足迹就像蝌蚪的幼儿园一样温暖可人。
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描绘的那个诗意世界,死亡和复活成了生命不断循环与再生的象征。人与动物之间的界限不存在了,自然物种与人类社会之间的边界被打开了,由此涌现出一种洗尽铅华、震撼心灵的力量,那是大自然心脏充满力量的律动。在那里,大自然不再抽象,而是以恣肆奔涌的生命浪潮表达澎湃心声。酒神狄俄尼索斯通晓自然的各种秘密,“在他的魔力之下,不仅人与人之间重新修好,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与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慷慨地奉献出它的献礼,危崖荒漠中的野兽也安静地向人类走来。”
这样飞瀑千寻的领悟与想象,像潮水冲破堤岸,超越了往昔对自然与人事的固有认知,是对自然神性和生命终极意义的抽象思考。眺望象群远去的背景,大自然呈现出了最瑰丽的惊世之美,蝼蚁蚍蜉,伟人巨匠,万千众生,一样在它怀抱中,和光同尘。
(作者:刘东黎,系作家,中国林业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