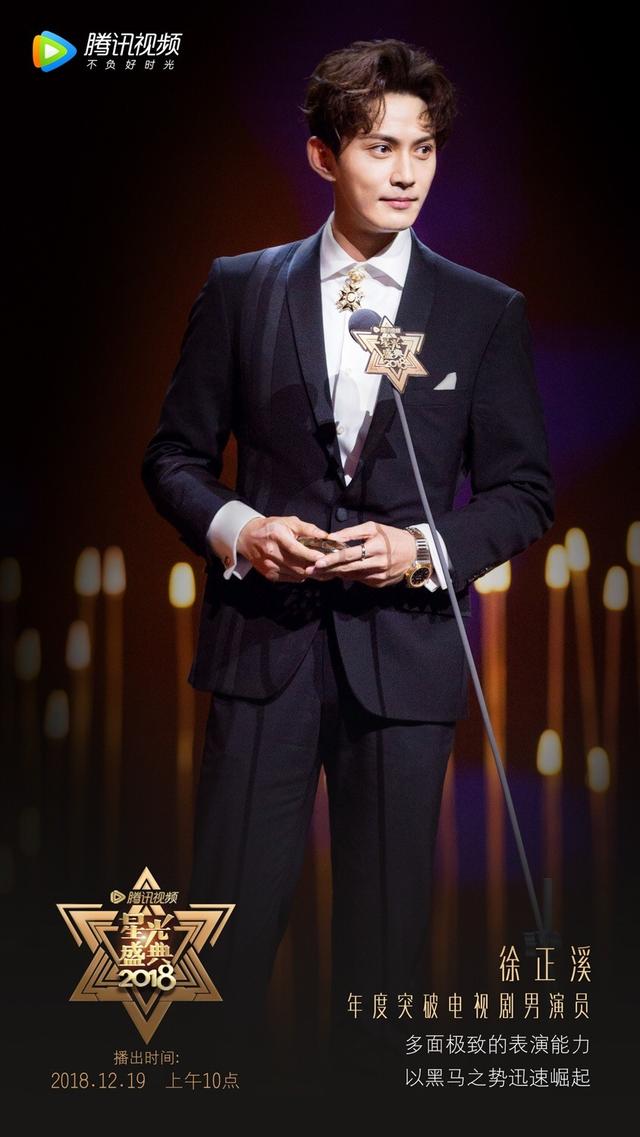有史以来最好的科学书籍(一份科学史书单)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6期,原文标题《一份科学史书单》,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主笔/薛巍
西方近代发生的科学革命深刻改变了世界,引发了世界观的变革和工业革命。英国哲学家格雷林在《天才时代》一书中说:“17世纪最有学识的人在短暂和动荡的时间内完成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转变。”科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威力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科学与知识和真理的关系却充满怀疑和争论。学者陈嘉映写道:“科学似乎给我们提供了世界的真相。但在这幅从大爆炸到基因的严整画面中没有哪里适合容纳我们的欢愉和悲苦、我们的道德诉求与艺术理想,事实上,科学研究要求排除这些……科学所揭示的宇宙是一个没有目的、没有意义的宇宙……关于科学是否代表真理,这一开始就有争议。”
科学之外还有什么知识呢?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说,求真的方式有五种:技艺(手艺和艺术)、科学(知识)、明智或实践知识、努斯(直觉)和智慧。其中科学的对象是由于必然性而存在的,是永恒的。科学可以传授,科学知识可以学得。“只有当一个人以某种方式确信,并且对这个结论依据的始点也充分了解时,他才是具有科学知识的。”但智慧是各种科学中的最为完善者。“有智慧的人不仅知道从始点推出的结论,而且真切地知晓那些始点。所以,智慧必定是努斯与科学的结合,必定是关于最高等题材的、居首位的科学。”

《人类的攀升》
[英]雅可布·布洛诺夫斯基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15年
布洛诺夫斯基 (1908~1974)是波兰裔数学家、历史学家,1973年为BBC的科学史纪录片《人之攀升》担任主持解说。他说:“理论发现通常看上去就不同凡响,独具匠心。而实用性的发现,即使影响深远,看上去也较为平庸,易于被人忘却。”比如以椭圆形而不是以圆形为基础的新型拱,突破罗马式拱形建筑局限的结构,看起来这似乎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变革,但它对于建筑物连接部位构造方式的影响却是十分惊人的。墙壁的负载减轻了,人们可以在上面开窗户,装玻璃由于骨架安在建筑物的表面,内部空间变得宽敞而开阔。
他提到青铜器的制作在中国得到最完美的表现。中国人使用铜和锡的比例非常精确。在铜中加入5%~20%任何比例的锡,都可以制成青铜。但商朝最好的青铜器包含15%的锡,刃口极其锋利。按照这种比例制成的青铜要比黄铜差不多硬3倍。“商朝的青铜器是祭祀、敬神的用品。从此青铜成为一种适合于任何目的的材料。但是,在中国人的技艺到达炉火纯青的顶峰时,青铜器所表现的尚不止于此。这些中国人制成的盛酒和食物的器皿(一半是为了赏玩,一半是为了敬神)之所以让人感到赏心悦目,在于制作者会构想和设计器物形状和纹饰,执着地提高手艺,达到娴熟精湛的水平。”
《历史上的科学:科学萌芽期》
[英]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著,科学出版社,2015年
贝尔纳是分子生物学家,他说科学从观察开始,再继以实验。任何人不论是否科学家,都会观察事物。重要的是观察什么和如何观察。“艺术家进行观察,要通过个人经验和感情,把所看到的转变为新颖有召唤力的创作。科学家进行观察,为的是尽量脱离个人情感而寻求各种新事物和新关系。”
关于科学和技术的关系,“在拣取和改造物质以制造工具来满足人类主要需求的过程中,首先产生技术,随后产生科学。技术是个人创获而由社会保持的操作方法,科学是使人懂得如何操作,以求操作得更好的方法”。
《现代科学史》
[英]彼得·J.鲍勒著,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
作者认为,知识有很多种形式。体现在手艺中的实用知识,不同于对现象进行各种抽象了解而得到的知识。例如,更换一个汽车轮胎,驾车者需要的是直接指导或亲自动手的经验,而不是关于机械或材料强度的专业知识。一名侦察兵在野外取火,用力摩擦两根木棍或打击燧石发出火星去点燃易燃物,他也不用懂涉及氧气的燃烧理论。相反,光有理论知识,一个人还是无法取到火。
书中专有一章讨论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科学和技术的联系”。西方社会传统上认为用大脑劳动的科学家在地位上高于用双手劳动的人。科学是为了寻找真理,而不是为了产出技术。科学可能带来了实际应用,但那只是在探寻真理时偶然出现的副产品。到19世纪上半叶,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胡威立认为技术先于科学,科学不是技术创新的稳定来源。

《哲学·科学·常识》
陈嘉映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
作者承认,现代科学、理论化的思维是西方独有的,但没有产生现代科学的地方不等于没有理性态度。理性态度和理论态度是两种东西,不仅于此,在通常意义上,理智和理性是非理论的,甚至是反理论的。把理性和理论结合在一起,并非普遍情况,而是属于希腊和西方的特例。“在中国,理性态度大约在周朝逐渐兴盛。商朝重鬼神,周朝重人道。理性这个词有多重意义,不过,在我们的日常用语中,理性这个用语的意思是大致可辨的。我们说某人理性,是说他着眼于现世,重经验、重常识,冷静而不迷狂。理性态度是一种重常识、重经验的态度。子产、孔子这些人代表着理性态度在中国的兴起。整部《论语》简直就是理性态度的范本。”
不光孔子,老子、墨子、庄子、法家,他们整体地兴起了理性态度。“先秦诸子各家各派的理性转向的程度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都相当彻底。在我看来,诸子的导向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理性的民族。”
理论是一般的东西、普遍的东西、抽象的东西,是和具体情况相对的。普遍性对于理论家是重要的,对于务实家却没什么用。先秦诸子只不过没有希腊人那种建构理论的热情。先秦的各个学派都不怎么重视对宇宙的整体解释,后来成为中国主导传统的儒学尤其缺少对世界提供整体解释的理论兴趣。那些注重实际的理智人往往对理论没有兴趣,甚至轻蔑。
作者说,跟其他文明比起来,中华文明是个特别富有理性态度的传统。这种理性态度,尤其体现在中国的政治治理方面,中国两千年前就建立起相当健全的官僚制度,一千多年前就建立起相当完备的科举选拔制度。余英时概括说,近代以前,“中国一半的政治和社会状况不但不比西方逊色,而且在很多方面还表现了较多的理性”。

《思维简史:从丛林到宇宙》
[美]伦纳德·蒙洛迪诺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
作者分析了妨碍科学进步的社会因素。在西方,科学研究也曾经中断过,“现代科学作为一种形而上学体系是建立在自然世界依照某种规律运行这种观念之上的,古希腊人最早开始接受这种观念;但直到17世纪之前,科学并没有利用这些规律获得让人信服的成功。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以及亚里士多德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变为伽利略和牛顿的观点,是一次巨大的飞跃。并且,这种转变并不需要花费两千年的时间来完成”。
科学在古希腊萌芽之后,要到17世纪才发生革命,部分是因为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对希腊,以及公元前64年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征服。罗马的崛起是人们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对哲学、数学和科学兴趣衰减的开始——甚至在那些讲希腊语的知识分子当中也是如此——因为实用主义至上的罗马人并不重视这些领域的研究。西塞罗的一句话很好地表达了罗马人对理论研究的轻蔑。“希腊人,”他说道,“给予了几何学家很高的荣誉;当然,数学取得了无与伦比的辉煌进步,但我们证明了这项技术在测量和计算用途上的局限。”在罗马共和国和其继任者罗马帝国统治的约一千年里,罗马人的确建设了巨大的、让人印象深刻的工程,它们毫无疑问都要依靠测量和计算;但据我们所知,罗马没有产生一个有名望的数学家。这个事实让人震惊,它证明了文化对于数学和科学发展的巨大影响。
作者认为,中国很早就有科学的萌芽,但受到了教育体制的妨碍。“和伊斯兰世界一样,中国的教育系统被证明远远不如欧洲,至少在科学方面如此。这种教育系统受到严苛的控制,主要集中在文学和道德修养方面的学习,几乎不重视科技创新和创造力。这种情况从明朝初年(1368年左右)一直到20世纪也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和阿拉伯世界一样,中国在科学(相对于技术)领域只取得了适度的发展,尽管这些进步发生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但它们不是这种教育体制的产物。对于学术现状持批评态度,并试图通过发展必要的学术工具将其系统化来推动精神生活向前发展的思想家们把数据的使用当作一种推动知识进步的途径,但他们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在印度也是如此,基于种姓结构的印度社会坚持以牺牲学术进步的代价来换取社会的稳定。结果,尽管阿拉伯世界、中国和印度的确在其他领域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但他们并没有产生可以和创造现代科学的西方科学家相提并论的人物。”
《科学的诞生:科学革命新史》
[英]戴维·伍顿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
作者指出,对科学的理解曾经非常广泛。Science(科学)一词源自拉丁语“scientia”,意为“知识”。有一种观点认为,真理和知识就是人们认为它是的东西。这一观点既源自巴特菲尔德对辉格史观的拒绝,也源自维特根斯坦。按照这种观点,占星术曾经是一种科学,神学当然也是如此。在中世纪的大学,核心课程由7种拓展心智的“艺术”和“科学”构成,包括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学(其中包括占星术)。它们现在通常被称作7种拓展心智的艺术,但其中每一种最初都既可以被称作一种艺术(一种实用技能),也可以被称作一种科学(一种理论体系)。举个例子,占星术是应用技能,天文学是理论体系。
《世界历史上的科学》
[美]詹姆斯·特赖菲尔著,商务印书馆,2015年
这是一本只有170页的科学史入门书,作者说:“在日常用语中,科学和技术几乎可以互换使用,但要对它们之间的重要区别做出说明。科学是对我们生活世界的知识的追求,技术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的知识的应用。这两种活动之间的界限顶多算模糊的,有着大面积的重叠。这两个术语指的是不同种类的过程。”
作者概括了科学研究的各个环节,从观察到预测再到观察的循环:“现代科学的方法是观察世界,从这些观察中提取规律,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些规律,用理论进行预测,然后观察世界来看看这些预测是否都被证实了。”在前科学时期,人们的认识使用了科学方法的一部分。“原始人就在观察世界和认识规律,如果狩猎和采集群体的成员不知道什么时候鱼会在某条河里游动,或者坚果什么时候成熟,狩猎和采集就不能持续很长时间。”
天文学是最早发展起来的科学分支,许多古老的文明在定期观察天象的基础上发展出了复杂的天文学。“中国是有着长期肉眼天文学记录的文明古国,中国的天文学有几个方面吸引了现代科学家的注意,他们细致地记录了超新星事件(中国人称它们为客星)。对地球上的观察者来说,表现出来的是在之前没有星星的地方突然出现一颗星星,徘徊几个月后消失。中国天文学中有一则记录关注了太阳黑子的出现。正常情况下,人类不能用肉眼看太阳,然而在中国北方有沙尘暴,这阻隔了足够的光线,使得观察太阳圆面成为可能。中国人除了保持天文记录外,还发展了天空运行的理论,即宇宙模型。”

《给世界的答案》
[美]斯蒂芬·温伯格著,中信出版社,2016年
美国理论物理学家斯蒂芬·温伯格是197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说古希腊的“早期科学家”都是诗人,他们挑选字词时考虑的是美感而不是传达信息,他们也没有努力用证据去证明他们的理论。就像罗素所说,亚里士多德说女性的牙齿比男性少,他完全可以让他的夫人张开嘴他去数一数,就可以避免这个错误。
相对而言,温伯格对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希腊化时期的科研活动的评价比较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要建立宏大的形而上学方案,试图囊括全部现实,希腊化时期的学者则比较谦逊,他们选择的是比较小的、更加容易处理的问题,如计算地球、月亮和太阳的大小,他们取得了真正的进步。
之后温伯格讨论了非西方的科学,他说虽然西方人从其他地方借了许多科学知识——从埃及借了几何学,从巴比伦借了天文学数据,从巴比伦和印度借了算术,但它独立发展出了科学的方法,比如提出假设并用实验检验这些假设。中国虽然给世界提供了杰出的技术,如指南针,但科学不同于技术。“科学和技术相互促进,但在最基本的层面,科学不是为了任何实用的理由开展的。科学的目标是解释纯粹的自然现象,它是积累的,每一种新的理论包含之前成功的理论。在古代,科学家还不知道需要证实他们的理论。科学的技术应用非常重要,因为在把理论付诸实践而不只是谈论它时,理论是否正确就很重要了。如果阿基米德通过对引力的测算,说一个镀金的铅制王冠是金子做的,他就不得人心了。”一种为了实用目标的技术发明能够带来新的科学发现,比如有了晷针就可以计算每个季度有多少天,苏格拉底的同时代人优克泰蒙发现每个季度的长度是不完全相等的,这跟太阳绕着地球做匀速圆周运动相矛盾。
更多精彩报道详见本期新刊《再问“李约瑟之问”》,点击下方商品卡即可购买,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