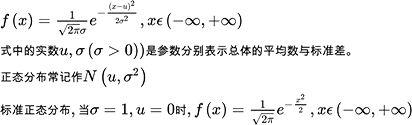洋芋咋做好吃(我的洋芋情怀)
我是吃着洋芋长大的,每次看见洋芋,总觉得它眉开眼笑得像是给我打招呼,于是有关洋芋的往事便历历在目。
从记事起,家里每年都要种上十几二十亩的洋芋。洋芋就是土豆,它的学名是马铃薯,只不过是各地的叫法不同而已。在七、八十年代,由于粮食的短缺,我们就把洋芋当作主食来吃,它既是经济作物又成了粮食作物。

五月春风掠过大地,小草探出脑袋,就到了种洋芋的时候。我们将储藏在窑里的洋芋吊出来。那时的窖是地面打直坑,向下二、三米再挖左右偏洞,一口窖大概能盛七、八吨洋芋。吊种子要有一个人下到窖里,一般都是父亲将二妹妹放到大一点的筐子里吊下去,我是不下去,因为里面黑乎乎的又阴又潮,散发着腐烂的霉味,只有窖口透进来的一点光亮,让人本能的心生恐惧。有次心里装着“毛鬼神”的我下去吊洋芋撞见了癞蛤蟆,怕的要死,扯着嗓子拼了命地哭喊,上来后就病了,发高烧说胡话,把父母折腾的够呛,此后就仗着这次害病的由头赖着不下窖。

洋芋吊出后摊在院子的地上用菜刀切种子,将一个完整的洋芋按芽眼子切成三角状,分成若干块。太小的不用切,直接削了顶端的集聚芽就可以当种子。切洋芋的手被淀粉含量极高的汁水浸泡得发白,摘了手套风一吹就黢黑黢黑的,又脏又难看。
种洋芋要好几家人搭伙,不然人少了拉不开栓。最开始是二牛抬杠的犁,一人牵牛,一人扶犁,犁铧尖子豁开土地,形成一条沟,犁深犁浅全凭扶犁人的经验,我们提着筐子或者水桶盛满籽种,向沟里点种,种子株距大概20一25厘米,二牛抬杠一圈后顺着沟再犁,这一遍不点种,作为行距,翻起来的土将种子埋了犁沟填平,这一圈我们可以休息一会儿,一天也就种个两、三亩地。没有牛的人家会借用他人的牛,都不会付报酬,但会给牛主人家干活或者送去贴膘饲料表达谢意。后来有了拖拉机,种洋芋双犁铧,一圈种子点完接着第二圈点,人累得连轴转,速度提高了,一天种个十亩地不在话下,但必须点种的人越多越好,那时种洋芋家家谝工便成了一曲远去的和谐之歌。

半个月后,洋芋一朵朵从地面探出头,杂草也不甘示弱地追着洋芋苗吸食土地的营养。洋芋和麦子在南山都属于大田作物,可洋芋比麦子的种植要多出几道程序:刨草、施肥、壅洋芋、浇水……
刨草是个苦活累活,其实就没有哪样农活是不苦不累的。顶着个大太阳,骑着洋芋刚显现出来的行子,用锄头把杂草刨死,没有草的地方也要刨,只为松土。雨水越广洋芋长势越好,杂草也就越茂盛,总之,一切都是相辅相成的。父母刨三行,我和二妹刨两行,三妹刨一行,刚开始我们是紧随父母左右的,谁也不说话,伴着锄头落地与石子碰撞时发出清脆的“嚓嚓”声,奋力向前赶,一抬头父母已遥遥领先。一亩还没过半,清晨的凉爽就被艳阳取代,每个人脸上的汗珠都淌成了小河流,衣服也黏在身上,还好这时节的南山有微风拂过。父母总有使不完的劲,时刻激励着我们。坐下来休息时,我们姊妹仰着被太阳晒得通红的小脸,看着刨过的洋芋地,一脸的成就感。头一两天,胳膊、腿没有一个地方不疼,等到全身筋骨因劳动而舒展开来,酸痛就会好很多。

刨完草,上完肥料,就用马或者牛拉着犁给洋芋壅土,两行洋芋中间单犁开沟,土壅向两侧洋芋苗,用铁锨把沟培瓷实,还得把压在土里的洋芋苗掏出来。
我人生中挣得第一笔钱就是掏洋芋苗得来的。放学后我和再乃拜两人从东滩打截路去一队商店,路过了尤布子阿爸的洋芋地,他一个人在掏苗,我俩向往常一样问候他,他说:“你俩挣钱不挣钱”?“挣呢!”我俩急切表态,又问到“咋么挣钱呢”?阿爸说:“你俩把剩下的洋芋苗子掏出来,我腰疼得干不动了,掏完我就给钱”,说完他一屁股坐在地埂子上卷起了莫合烟。我和再乃拜也不问多少钱就扑倒地里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天麻麻黑的时候终于干完了,尤布子阿爸一人给了两块三毛钱,把我俩高兴的商店也不去了,蹦蹦跳跳地回了家。母亲看见我捏在手里的毛毛钱打问出了原委,非要我把钱还了去,说是给人帮忙哪有要钱的道理,妈妈一直就是这样一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可我就是没有听她的话去还钱,我觉得那是我的劳动应得的。

盛夏的骄阳炙烤着大地,湛蓝的天空下,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田地,洋芋杆子上激情绽放的洋芋花亦是农民绽放的笑容,有紫色的、白色的……一朵朵洋芋花连成片片花海,这油画般的景色一直留在我记忆中,装扮着我的童年。在垄起的洋芋沟捉迷藏,每人装一口袋洋芋花结的果实“骚蛋子”,当武器打来打去的,成了那是最着迷的游戏。
九月底的阳光中掺杂着一丝凉意,这时的南山没有春天的生机勃勃,也没有夏的绿意盎然,更没有冬的死气沉沉,有的只是在金黄又萧瑟的季节里对一年收成的期许。

阵阵秋风吹枯了洋芋叶子,这时南山的天气真的是早穿棉袄午穿纱,大早出门穿上厚重的的棉衣,干到中午就得穿单衣。犁开洋芋沟,白花花的洋芋就躺在了地面上。先把洋芋装满筐子再提的倒成堆,五亩地一般可堆三大堆,方便蔬菜公司调拨洋芋的车来拉。洋芋堆上头摆一些大的漂亮的洋芋装门面,为了让拉洋芋的人能看上。有时候,正在拾就有拉洋芋的单位来人看上,赶快叫来邻居帮忙装车,装车时以鸡蛋大小为标准,比鸡蛋小的全部筛下。车装好后把自行车放到拉洋芋的车上去永丰地磅过吨数,过完磅,手里拿着一张过磅票据,就是将来调拨款下来核对的凭据,再骑着自行车回到地里。没有人来拉的大洋芋堆,要压上洋芋叶子或者麦草,再覆盖上土,这样就可以避免风把洋芋吹绿。我家一直有父亲曾经服过兵役的部队来拉洋芋,称作“关系户”,不愁销路,只是那时的调拨价格一公斤只有一毛几分钱。而且还不是现钱,要等到调拨款打到信用社由大队出面领回来,扣了乡统筹、村提留,余下才是个人的,这时还要清算老超支、机耕费、电费,到头来丰产不丰收,几家欢喜几家愁,这种日子说不苦那是假的。


灿烂季节随秋而去,收获丰盈了从容的季节,洋芋也曾在南山大地上作为“以物易物”的商品流通着。收成结束,会有米泉的人来换大米、有吐鲁番的人来换葡萄、有安宁渠的人来换白菜萝卜、也有石河子的人换红薯,洋芋就这样让我们不出村子就换得了外面的世界。
1996年洋芋的价格从两毛钱一下飙升至一块两毛钱,这可激动坏了众人。场上的麦子还没有打完,就有菜贩子,俗称二道贩子进村收购,还帮着拾洋芋,现场过称现场结钱,让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父亲那年带领我们将洋芋地犁了三产(三遍),家里也重新购置了彩电、冰箱、洗衣机,妈妈也添置了金货。那是人们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传统经济落寞后新生经济复苏带来的喜悦。
小时候有个洋芋品种叫“七零一”,长得不圆是长型的,颜色发黄,我上高中的时候又有了“紫花白”品种。“紫花白”凭借着适应性广、丰产性好,在南山广泛种植。随之也出现了按照洋芋大小划分等级的新名词“大加工、二加工、大混合、小混合”,等级的出现是价格高低的体现。

父亲有独到的眼光,他早早从四大队(萨尔乔克牧场)的“马铃薯种子培育基地”购得良种,提前试种,农家肥的合理使用,使种的洋芋又白又大品相极好,西山农场的连队职工慕名而来早早预定种子,到了收获的时候都不用我们割洋芋叶子、拾洋芋,他们开着拖拉机,自犁自拾,你争我抢的帮我家减轻了不少劳动负担。父亲眉开眼笑的在地头数着钞票,计划着来年的光景,身后是黑色的土地。
印象中,洋芋二产(第二遍)拾完,我们放羊娃就把羊群赶到地里抢茬子,烧洋芋就成了放羊娃子在孤寂中寻求慰藉的一件事情。大伙合理分工,年龄小的看羊群,年龄稍大一点的捡柴火和拾牛粪,最大年龄的刨地坑、用土块盘炉子。炉子盘好,炉膛里火光燃起,待火将炉壁烧红、烧黑再烧得发白时,有经验的大孩子抽出未烧完的柴火熄灭,朝里面扔进洋芋,然后把土炉子踢翻,踏平,覆盖上厚厚的泥土,剩下的交给时间。在起开土层和土块的一刹那间,一股浓浓的香味扑面而来,烤熟洋芋散散得像花一样地出现在眼前,冒着热气,沙沙的口感,真让人回味无穷……

南山的土种出来的洋芋面、沙、而且香醇,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美食,大盘鸡、红烧牛排、胡尔炖……哪个都是洋芋成就的经典,更不用说洋芋擦擦、洋芋丸子、洋芋凉粉等招人的特色美食了。经过加工,它除了可以做成淀粉外,还可以加工成各种速冻方便食品和休闲食品。
父亲给洋芋取了一个“高、大、上”的名字“国菜”,早晨的洋芋汤他叫“国菜汤”,中午的洋芋丝拉条子他叫“国菜拌面”,晚上煮的洋芋端上桌,他又戏称“国菜蛋蛋”。虽是父亲的玩笑,但也毫不夸张地说明了洋芋的价值。
洋芋是南山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祖辈们用坚强的意志、勤劳的双手种洋芋,填饱了肚子活了命,靠着洋芋养家糊口、供养学子,又靠着洋芋过上富裕的生活,洋芋一路不离不弃陪伴着南山的劳苦大众!
我相信有很多人与我一样依旧对曾经伴随我们走过艰苦岁月的洋芋不离不弃,有着一份难以割舍的情怀,我从未忘记南山的每一棵生长在泥土里的洋芋苗,也无法忘记每一朵盛开田间的洋芋花。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