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都有一个悲惨的童年(看了作家们笔下的童年)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祝每一个孩子及童心未泯的大人们节日快乐。
你是从什么时候告别童年的呢?如果回到儿时,你想做什么呢?童年美好而珍贵,那时候,我们总是充满探索的热情,总是做着一个又一个梦,好像有无限的可能。童年不仅是我们过去留下的痕迹,也是通往我们未来的隧道,它影响着每个人的一生。老舍先生有篇文章篇名是《小时候真傻,居然盼着长大》,或许每个长大的人在某一天都会发出一样的感慨吧。
我们为大小读者摘选了莫言、迟子建、贾平凹、毕飞宇和蒋韵这五位作家回忆童年的文字,读者或许可以看到他们是如何在时间中成长的。
童年读书
莫言丨文
我童年时的确迷恋读书。那时候既没有电影更没有电视,连收音机都没有。只有在每年的春节前后,村子里的人演一些《血海深仇》、《三世仇》之类的忆苦戏。在那样的文化环境下,看“闲书”便成为我的最大乐趣。
我体能不佳,胆子又小,不愿跟村里的孩子去玩上树下井的游戏,偷空就看“闲书”。父亲反对我看“闲书”,大概是怕我中了书里的流毒,变成个坏人;更怕我因看“闲书”耽误了割草放羊;我看“闲书”就只能像地下党搞秘密活动一样。后来,我的班主任家访时对我的父母说其实可以让我适当地看一些“闲书”,形势才略有好转。但我看“闲书”的样子总是不如我背诵课文或是背着草筐、牵着牛羊的样子让我父母看着顺眼。
人真是怪,越是不让他看的东西、越是不让他干的事情,他看起来、干起来越有瘾,所谓偷来的果子吃着香就是这道理吧。我偷看的第一本“闲书”,是绘有许多精美插图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那是班里一个同学的传家宝,轻易不借给别人。我为他家拉了一上午磨才换来看这本书一下午的权利,而且必须在他家磨道里看并由他监督着,仿佛我把书拿出门就会去盗版一样。
这本用汗水换来短暂阅读权的书留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那骑在老虎背上的申公豹、鼻孔里能射出白光的郑伦、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眼里长手手里又长眼的杨任,等等等等,一辈子也忘不掉啊。所以前几年在电视上看了连续剧《封神演义》,替古人不平,如此名著,竟被糟蹋得不成模样。其实这种作品,是不能弄成影视的,非要弄,我想只能弄成动画片,像《大闹天宫》、《唐老鸭和米老鼠》那样。

后来又用各种方式,把周围几个村子里流传的几部经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儒林外史》之类,全弄到手看了。那时我的记忆力真好,用飞一样的速度阅读一遍,书中的人名就能记全,主要情节便能复述,描写爱情的警句甚至能成段地背诵。现在完全不行了。
记得从一个老师手里借到《青春之歌》时已是下午,明明知道如果不去割草羊就要饿肚子,但还是挡不住书的诱惑,一头钻到草垛后,一下午就把大厚本的《青春之歌》读完了。身上被蚂蚁、蚊虫咬出了一片片的疙瘩。从草垛后晕头涨脑地钻出来,已是红日西沉。我听到羊在圈里狂叫,饿的。我心里忐忑不安,等待着一顿痛骂或是痛打。但母亲看看我那副样子,宽容地叹息一声,没骂我也没打我,只是让我赶快出去弄点草喂羊。我飞快地蹿出家院,心情好得要命,那时我真感到了幸福。
……
北极村童话
迟子建丨文
中秋节过去了。天气越来越寒冷。霜花凝成了薄冰,嵌在低洼的土地上。
菜园一下子变得苍老了。枝残叶败,果坠花萎。蚂蚱不再蹦了,燕子也离开了北方。干巴巴的豆角架上,只零星盘挂着枯草的叶片。豆角丝晾干了,收进了仓房;胡萝卜未干透,把它请到炕头去了。
姥爷给小鸡垒了窝。它们的嫩翅膀受不了雪花和寒风的袭击。它们失去了奔跑和自觅食物的权利。它们将要伴着干菜叶,在闷葫芦一样的窝里,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傻子的窝是小舅垒的。用桦木杆支起个架子,苫上干草,再糊上黄泥,留个口儿。看上去,跟个躺倒的泥烟囱一样,别扭极了。
姥姥戴着老花镜,在炕上盘着腿,做起冬天的棉衣来。她给我安排了许多活:择线头、用弓子弹旧棉花、剥饭豆皮。尽管心中一百个不乐意,可我还是耐着性子做了。难有出去的机会,走一步姥姥都要问。干完活,我就用小舅使剩的铅笔头默写奶奶教过的字。专门预备给猴姥的卷烟纸被我独吞了。
我开始琢磨画画。画奶奶家的烟囱、她房后的牵牛花和那个紫檀木桌子。纸上满是歪倒了的烟囱、没立体感的牵牛花、瘸了腿的桌子、呆若木鸡的燕子和尾巴跟兔子一样短的傻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叠在一起,用一小块塑料布包好,藏在柈垛里。这样,它就不怕风吹、日晒、雨淋了。我打算要带这个去看奶奶。这回,我更精心设计一幅画了。因为姥爷给了我一张玻璃窗那样大的硬纸,让我叠纸飞机玩。纸飞机我玩厌了,我决心在上面画一幅画,我最喜欢的。
趁姥姥去买粮的当儿,我一个人伏在炕上,飞快地动笔了。一个老奶奶,交叉着双手仰头望着天。她的长裙曳地,自然打着旋,像一朵盛开的牵牛花。她的脸上宽下窄,皱纹纵横,前探的下巴上的嘴紧紧地抿着。她望着天,好像在寻找什么,以至于三角巾就要从肩头滑下去了,她的头顶是一颗小星星。
铅笔的黑色总嫌淡,我从灶坑里扒出一块木炭,涂在裙子上。古铜色的三角巾用松树皮擦上了。星星,应该是金黄色的。绞尽脑汁,我猛然想起了豆油。豆油,黄乎乎,黏稠稠,滴上一滴,星星准会眨眼睛的!
……
月迹
贾平凹丨文
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中秋的夜里,我们在院子里盼着月亮,好久却不见出来,便坐回中堂里,放了竹窗帘儿闷着,缠奶奶说故事。奶奶是会说故事的,说了一个,还要再说一个……奶奶突然说:
“月亮进来了!”
我们看时,那竹窗帘儿里,果然有了月亮,款款地,悄没声儿地溜进来,出现在窗前的穿衣镜上了:原来月亮是长了腿的,爬着那竹帘格儿,先是一个白道儿,再是半圆,渐渐地爬得高了,穿衣镜上的圆便满盈了。我们都高兴起来,又都屏气儿不出,生怕那是个尘影儿变的,会一口气吹跑呢。月亮还在竹帘儿上爬,那满圆却慢慢儿又亏了,缺了;末了,便全没了踪迹,只留下一个空镜,一个失望。奶奶说:“它走了,它是多多的;你们快出去寻月吧。”
我们就都跑出门去,它果然就在院子里,但再也不是那么一个满满的圆了,进院了的白光,是玉玉的,银银的,灯光也没有这般儿亮的。院子中央处,是那棵粗粗的桂树,疏疏的枝,疏疏的叶,桂花还没有开,却有了累累的骨朵儿了。我们都走近去,不知道那个满圆儿去哪儿了。却疑心这骨朵儿是繁星儿变的;抬头看着天空,星儿似乎就比平日少了许多。月 亮正在头顶,明显大多了,也圆多了,清清晰晰看见里边有了什么东西。
“奶奶,那月上是什么呢?”我问。
“是树,孩子。”奶奶说。
“什么树呢?”
“桂树。”
我们都面面相觑了,倏忽间,哪儿好像有了一种气息,就在我们身后袅袅,到了头发梢儿上,添了一种淡淡的痒痒的感觉;似乎我们已在了月里,那月桂分明就是我们身后的这一棵了。

奶奶瞧着我们,就笑了:
“傻孩子,那里边已经有人了呢。”
“谁?”我们都吃惊了。
“嫦娥。”奶奶说。
“嫦娥是谁?”
“一个女子。” 哦,一个女子。我想。月亮里,地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个地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
“有三妹漂亮吗?”
“和三妹一样漂亮的。”
三妹就乐了:
“啊啊,月亮是属于我的了!”
三妹是我们中最漂亮的,我们都羡慕起来。看着她的狂样儿,心里却有了一股儿的嫉妒。
我们便争执了起来,每个人都说月亮是属于自己的。奶奶从屋里端了一壶甜酒出来,给我们每人倒了一小杯儿,说:“孩子们,你们瞧瞧你们的酒杯,你们都有一个月亮哩!”
我们都看着那杯酒,果真里边就浮起一个小小的月亮的满圆。捧着,一动不动的,手刚一动,它便酥酥地颤,使人可怜儿的样子。大家都喝下肚去,月亮就在每一个人的心里了。 奶奶说:“月亮是每个人的,它并没有走,你们再去找吧。”
我们越发觉得奇了,便在院里找起来。妙极了,它真没有走去,我们很快不在葡萄叶儿上,磁花盆儿上,爷爷的锨刃儿上发现了。我们来了兴趣,竟寻出了院门。
院门外,便是一条小河。河水细细的,却漫着一大片的净沙;全没白日那么的粗糙,灿灿地闪着银光,柔柔和和地像水面了。我们从沙滩上跑过去,弟弟刚站到河的上湾,就大呼小叫了:
“月亮在这儿!”
妹妹几乎同时在下湾喊道: “月亮在这儿!”
我两处去看了,两处的水里都有月亮,沿着河沿跑,而且哪一处的水里都有月亮了。我们都看起天上,我突然又在弟弟妹妹的眼睛里看见了小小的月亮。我想,我的眼睛里也一定是会有的。噢,月亮竟是这么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
我们就坐在沙滩上,掬着沙儿,瞧那光辉,我说:
“你们说,月亮是个什么呢?”
“月亮是我所要的。”弟弟说。
“月亮是个好。”妹妹说。
我同意他们的话。正像奶奶说的那样:它是属于我们的,每个人的。我们就又仰起头来看那天上的月亮,月亮白光光的,在天空上。我突然觉得,我们有了月亮,那无边无际的天空也是我们的了:那月亮不是我们按在天空上的印章吗? 大家都觉得满足了,身子也来了困意,就坐在沙滩上,相依相偎地甜甜地睡了一会儿。
九月的云
毕飞宇丨文
有一种玩具你是不可能拿在手上把玩的,但这不妨碍你和它厮守在一起,难舍难分。
那是九月的云朵。这里的九月是公历的九月,如果换算一下的话,其实是农历的八月。在我的老家有句老话说,八月绣巧云。这句谚语是有语病的,是谁在八月绣巧云呢?不知道。那就望文生义吧,绣娘的名字就是“八月”。这样说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
在农历的七月,我的故乡有些过于晴朗,时常万里无云。正如《诗经》里说的那样:“七月流火。”都流火了,哪里还能有云?如果有,一定是遇上暴雨,那是乌云密布的,一丁点缝隙都不留。总之,七月的天空玩的就是极端。到了八月,天上的情况发生了奇妙的变化,总体上说,一片湛蓝,但是,在局部,常常堆积起一大堆一大堆云朵。因为没有风,那些一大堆一大堆的云朵几乎就不动,或者说静中有动,它们孤零零的,飘浮在瓦蓝瓦蓝的背景上。你需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目睹它们的微妙变化。
孩子都顽皮,没有一个人的屁股坐得住,可是,到了八月的傍晚,不一样了,猴子一样的孩子往往会变成幽静的抒情诗人,他们齐刷刷地端坐在桥上、墙头、草垛旁、河边,对着遥远的西方看,一看就老半天。

真正让孩子们关注的当然不是云,而是动物。平白无故的,一大堆的白云就成了一匹马。这匹白马的姿势很随机,有可能站着,也可能腾空而起。一匹马真的就有那么好看吗?当然不是。好看的是变幻。一匹马会变成什么呢?这里头有悬念,也可以说,有了玄机。
四五分钟的静态足以毁坏一匹马的造型,我们可不急。两三分钟,或四五分钟,一定会有人最先喊出来:“看,变成一头猪了。”
在通常的情况下,第一声叫喊大多得不到重视,一匹白马凭什么会变成一头白猪呢?可是,老话是怎么说的?天遂人愿——玄机就在这里,不知不觉的,一匹白马真的就幻化为一头白猪了,所有的眼睛都能见证这个遥远的事实。越看越像,最后成真的了,的的确确是猪。
我不知道“白云苍狗”这个词是谁发明的,他一定是一位心性敏感的倒霉蛋,他被人间的变幻与莫测弄晕了头,不知何去,不知何从。就在某一天,当然是“八月”里的一天,他的“天眼”开了,通过天上的云,他看到了苍天的表情,还有眼神。就在一炷香的工夫,他理解了大地上的人生。他看到了人生的短暂和不确定性,他看到了命运姣好的静,还有命运狰狞的动。他由此成了一个怀疑论者,或者说,相对论者。他一下子就“明白了”,由此获得了生命里的淡定与从容。就像虞姬在临死之前所吟唱的那样:自古常人不欺我,成败兴衰一刹那(为了押韵,这里念“nuó”),一刹那啊。
当然了,乡下的孩子是简单的,乡下的孩子看天上的云,不是为了“悟道”,更不可能“悟道”。我们只是为了好玩,怀揣的是一颗逛动物园的心。看了骆驼再看马,看了狮子再看熊,这多好哇。要知道,许多动物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因为云朵的飘移,我们认识了。你看看,云和天空所做的工作居然是“科普”与“启蒙”。也还可以这样说,在看云的時候,我们其实在看露天电影,天空成了最大的屏幕,生命在屏幕上嬗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天”和“云”就是这样神奇,难怪我们的先人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向大自然学习。我们观察大自然,研究大自然,其实都是学习。
如果你的启蒙老师是大自然,你的一生都将幸运。
“神马都是浮云”,这是前些年流行过的网络语言,颓废啊,颓废。唉,现在的孩子就知道浮云的虚幻,他们哪里能知道浮云的妙呢。其实呢,“浮云”要比“神马”神奇得多、有趣得多——全看你有没有那样的造化了。造化在天上,也在你的瞳孔里,在你的灵魂里。
北方的厨房
蒋韵丨文
而开封,则是我情意绵绵的乐园。
完全没有现实主义的清晰的记忆。比如,不记得住过什么样的房子,不记得家是什么样,不记得城市的面孔和模样,不记得任何一条街道和胡同的名字。所有的一切,都是碎片式的,残缺的,似真似幻的。但,记住的,永不磨损的,是那个城给予我的明朗和快乐,是小兽般的自由与欢腾,是某种珍贵的气息。
我的故乡没有阴天。隐约记得,姑姑们用火筷子给我烫了刘海。我觉得烫了发的自己成了一个外国人。收破烂的来了,姑姑带我去卖牙膏皮之类,我围着人家的车子转,仰着脸对收破烂的人一本正经地说:“叽里咕噜咕噜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噜噜噜哈拉噜……”一口气说出绕口的一大串。收破烂的自然听不懂,笑着说:“吔,这唱的是啥歌?怪好听!”我觉得他真是没有见识,只好用中国话回答说:“这不是歌,是外国话。你看,”我拨弄蓬松卷曲的刘海,“我现在是外国人。”一旁的人都笑了。
我不到三岁,姑姑们带我去看了人生中第一场电影,是日本影片《狼》。那影片,讲的是一群被生活逼迫、走投无路的小人物,合伙去打劫的故事。那不是一个适合孩子看的影片,悲惨而阴沉。但我安静地从头看到了尾。出了影院,姑姑们问我看的是什么?据说,我居然能讲个八九不离十。

姑姑们惊讶了,回来逢人就说我如何如何聪明之类。那应是属于我的小小骄傲,可我自己,对这件事这个电影,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记住了另一件和电影有关的事,是幼儿园带着小朋友去看的。演的似乎也正是幼儿园的故事,里面的插曲我至今记得:“好阿姨,好阿姨,阿姨像妈妈,宝宝听你话。跟你学唱歌,跟你学跳舞,亲亲热热笑哈哈,做个快乐的娃娃家……”回到家里我给姑姑们绘声绘色讲述电影情节,说到一个孩子发烧了,一量体温:“呀,九十八度!”我说。姑姑们笑喷了,说:“那不是发烧,那是烧开水!”我一点不明白她们笑什么,很气愤和委屈。
同样的事情,不久前,发生在我家如意身上。她来到一个新学校,认识了新朋友。朋友妈妈问如意妈妈,说:“我家孩子的生日是3月17号,你家孩子的生日是哪天啊?”妈妈还没说话,如意就抢着回答说:“我的生日是8月66号!”很骄傲,觉得那数字比人家的雄壮。
如意,比我小六十岁。整整一个甲子。我们都属马。老马和小马。我们祖孙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似并不奇怪,有些事却近乎神秘,我一出生,脸颊上有一个鲜红的血管瘤,听我母亲说,是医生给我注射了一种药,所以,在我一岁之后,它渐渐消失得无影无踪。六十年后落生的如意,脸上,竟然也有这样鲜红的一枚,红如朱砂,位置、形状,几乎和我消失的那个一模一样。有时,我会想,这是一个什么印记吗?是一种什么特殊的标识?类似族徽,标记着我们来自某一个共同的地方?标记着除了血缘之外我们还有另一种神秘的联系?
扯远了。
……
新媒体编辑:袁欢
配图:摄图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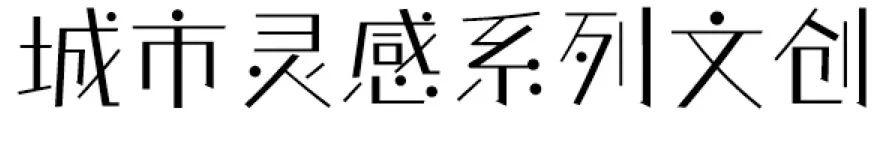

进入微店订购文创
秋季文创线上首批限量100份
报纸订阅线上渠道
中国邮政平台
→
本报为周报,周四出刊,通过邮局寄送,邮发代号3-22,全年订价61.8元
每天准时与我们遇见的小提示: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