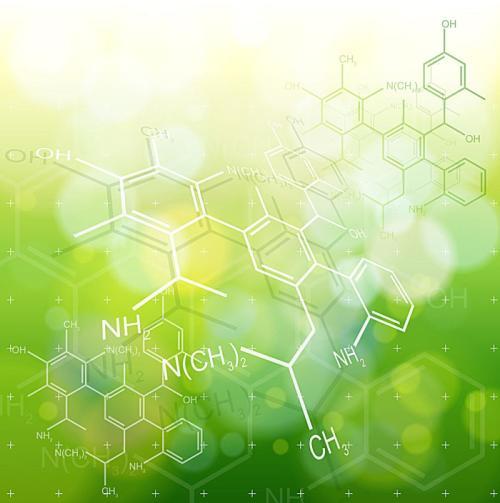不赞成容隐思想的是(为何古人不让亲人师生互相检举)
司法类的新闻一般都很受关注,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日常生活。绝大多数时候我们都会为罪犯被绳之以法而感到高兴和欣慰,但是有些新闻却会让我们心里感觉不是那么舒畅。
比如父母举报违法子女的藏身之地;夫妻之间互相检举斥骂对方的违法行为;儿女向社会、司法部门举报父母的违法阴私之事等等。这些新闻为什么会让我们觉得不舒服,因为它违反了我们心里日常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价值。

当年张红兵举报了自己的母亲方忠谋。方忠谋后被判死刑并枪决
把我们自己代入其中,如果我们的子女、爱人、父母等犯法,我们会去揭发么?无论大家具体在亲情伦理和国法面前如何选择,这都会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其困难和痛苦程度甚至会高于刑罚本身。
大部分国家为了让人们规避这种人性的挣扎,从法律上让出了一定的空间。原因并不复杂,如果法律不给人性留下余地,人性就自然会崩塌给法律看。而国家制定法律的一个目的不就是让人们保有人性么?
所以从古至今很多国家(包括那些已消亡的国家)法律上认为亲人之间不检举、不揭发、不举报并不违法,这就是“容隐制度”。(容隐制度在西方国家也被称为“亲属拒证权”)
中国的容隐制度起源于西周。在古代,维系一个庞大的皇朝,单纯地依靠强权和武力,自然是不可行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
通过构建共同的价值体系,将人们维系在一起效果更佳。所以周朝开始提倡和建立礼仪制度,以此来规范和统一人们日常的行为和价值取向。“亲亲”、“尊尊”是西周贯穿于周礼中的两条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宗法制度的萌芽。“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要求上命下从,不许犯上作乱。
到了春秋时期,亲亲相隐的观念正式形成。《论语·子路》中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句话出自孔子与叶公讨论“父亲偷了别人的羊,子女当如何”的对话中)

到秦汉时期,容隐制度正式被列入皇朝律法中。地节四年汉宣帝下诏:
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
规定“下”(妻妾、子女、孙)匿“上”(丈夫、父母、祖父母)无罪,“上”匿“下”除涉嫌死罪外无罪。
到了唐朝进一步扩大了容隐制度的适用范围-- “同居相为隐”。将容隐的豁免范围从至亲的祖父母、父母、子、孙,扩大到伯、叔、兄弟、姊妹等,还涵盖了师长、部曲、奴仆。
总体上来说“下”为“上”隐(知情不报、藏匿)皆可免罪或减刑。
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为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勿论,即漏露其事及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减凡人三等;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名例篇》
除此之外,唐代还出台了不得逼令亲属作证的规定。甚至为了防止亲属举报,还出台惩处举报亲人的律法,而且刑罚相当的重。
其于律得相容隐,即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皆不得令其为证,违者减罪人罪三等……诸告祖父母、父母者,绞……诸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唐律疏议·斗讼篇》
唐代以后各朝在“容隐制度”上基本都沿用了唐律的规则,异族入主中原的元、清也不例外。明朝太祖朱元璋虽然在律法上非常的严苛,但是也没有取消“容隐制度”只是缩减了“同居相为隐”的范围。
清帝逊位后,国民政府的律法也继承了“容隐制度”并且再一次扩大了容隐的范围。1935年《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将容隐的范围扩大至五等亲以内的血亲,三等亲以内的姻亲。
我们回看这段历史可以发现,中国的容隐制度的发展、盛行和儒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儒学构建的世界观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在儒学的价值体系中,皇朝不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人组成的,皇朝是由一个个独立的以血亲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组成的,所以血亲关系是皇朝的基础和基石。基于这种认知,所以保护血亲关系实际就是保护皇朝和“国家”。
两千多年来皇朝不断地更迭,皇权也更换着姓氏和族裔。但是我们这个国家总体上却一直可以延续而不分裂,原因是什么?并不是有一个强权在维系这一切。
是孝道、“君君臣臣”这些被当时绝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传统将我们的先人天然地维系在一起。既然大家志同道合,那为什么要分开呢?换句话说如果“志不同,道不合”,呆在一起不也是同床异梦么?
所以孝道、“君君臣臣”这些理念,皇朝自然要从律法上予以保护。中国历代律法不但鼓励“亲隐”,还会惩治违背这个原则的人。从汉代起,儿子若向官府告发父亲的罪行,不论父亲具体是什么罪行,官府都将以“不孝”对儿子处以重刑。
如果官员逼迫亲人互相检举,即便是最终犯人的罪行被证实,犯人会被减罪三等,相关的官员也会被严惩。
说到这里有些朋友也会提出疑问,容隐制度会助长不法行为,是封建恶习。确实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也不能过于片面的来看待这个问题。
首先即便是“亲隐”,绝大部分不法罪行还是会被人们或府衙获知并治罪。其次容隐制度重点是赦免“隐”,而不是赦免所犯的不法。这里笔者举个古代常见的事例来说明。
某人为朝廷官员,他的父亲仗着儿子的权势,横行乡里、欺压百姓。此人明知其父不法,却不向有司告发,并且在府衙追查时还帮助其父藏匿或者藏匿其罪证。这确实会提高侦查的难度,甚至是让案犯不能被定罪。
但案结判刑时,虽然依照“容隐”可以赦免此人知情不报、藏匿案犯的罪行,但是不会赦免其父的罪行,也不会赦免他纵容家人不法的罪行。
反之如果此人不是他的父亲,而只是他的朋友或者同僚。那他就逃不脱知情不报、藏匿案犯之罪。
我们的先人之所以这么做,只是让人能尽可能地保留亲人之间的血脉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出来最直接的现象就是无条件的援助。为什么要这样?
这个道理很简单,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父亲“不孝”,对自己的家族“不忠”。作为家人,家族成员如何再接纳这个背叛至亲的人?作为朋友,他人不会相信他会忠于朋友间的信义;作为臣子,君王也不会相信他会忠君体国。
我们的先人只是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选择了保护皇朝最根本的关系。
自宋朝儒学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壮大,尊师重道在社会上也成了仅次于“孝道”的行为准则。虽然律法上并没有相应的扩展,但很多时候“为师隐或为生隐”,人们天然地认为这就是“亲隐”,而且人们很多情况下也把主动破坏“师生”关系的行为和“不孝”划等号。
说明:这是东西方社会对容隐制度的态度和应用差异最大的地方,西方的容隐主要集中在家庭关系内。因为西方在历史中从未将师生关系提升到我们所达到过的高度。“师父”一词就已经说明了一切,我们曾视“师”以“父”待之。
在古代中国,官员们之间互相弹劾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是有一类弹劾是非常罕见的,就是“师生”之间的弹劾。
首先老师就不需要弹劾自己的学生,如果认为学生有问题,老师也首先应该想办法教育纠正。公然弹劾,为人师长的恕道何在?
张良拾履图
而学生呢?如果认为老师有问题,可以与其论道,指明师长的错误。也可以联络其它同门或师长至亲,一起规劝。公然弹劾,这被视为“叛师”,而且在不少人眼中这和“叛父”是没有区别的。
不论他是出于什么目的弹劾自己的老师,他这个行为本身在同僚眼中都是极其可怕的。因为连自己的“师父”都可以背叛,还有谁是他不敢背叛的呢?
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古代也推崇“大义灭亲”呀?
“大义灭亲”虽然在古代也是义举而非恶行,但我们的先人从来就不推崇,而且我们先人的“大义灭亲”只相当于我们现在认为的大义灭亲的一半。古代的“大义灭亲”只是单向的灭亲,专指“上灭下”。“下灭上”不叫大义灭亲,那叫不孝、忤逆,十恶不赦之罪。
允许“大义灭亲”的原因并不是希望“上”揭发“下”的罪行,而是我们古代的价值体系里“上”拥有对“下”的支配权,所以自然也有处罚权。
皇帝虽然也被臣子们称为“父”、称为“师”,但是大家都明白这是没有什么实际感情基础和联系的场面话,是为了凸显皇权至高无上的阿谀奉承。虽然有些人确实是把生养自己的父母、教育自己的师长抛之脑后,以皇帝代之。但是皇帝们但凡是读过点书,明白一些道理的,都知道这些人是“奸佞”。
皇帝们也明白,这些人虽然日常如忠犬一般,驱使起来非常方便。但是真到了危难时刻,他们都会以“大义灭亲”为名,出卖自己的“君父”。
综上,容隐或亲隐制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人们萌生了反司法的乌托邦思维。而是基于社会、国家是由一个个家庭为紧密联系的小群体组成。维护皇朝的长治久安,理智的做法就是维护这些小群体内部关系的稳定。
片面地追求律法的严苛,而去破坏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纽带关系,实际上会动摇整个社会的基础。这严重违背了律法设立的初衷。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