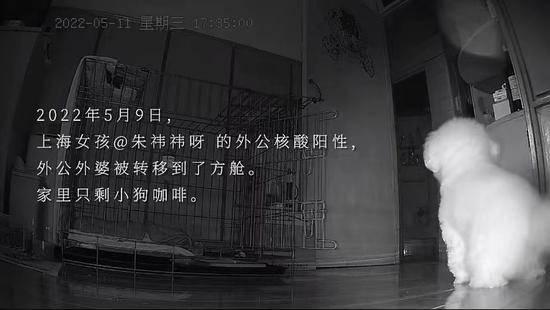再见雁北(苦寒的雁北)
雁北自古系苦寒之地,青芨丛生、白碱茫茫。明初兵部尚书王越有诗云:“雁门关外野人家,不植桑榆不种麻。百里并无梨枣树,三春哪得桃杏花。六月雨过山头雪,狂风遍地起黄沙。说与江南人不信,早穿皮袄午穿纱。”
昔日万历朝内阁首辅王家屏还乡时有感于乡民生计之苦,潸然泪下。太子太保曹文诏归乡省亲时说:“吾见桑梓刮碱为食,每忆之,泪不能禁。”
清朝时山西一个读书人,在谈到山西时也曾痛心疾首地说:
“无平地沃士之饶,无水泉灌溉之益,无舟车渔米之利,乡民唯以垦种上岭下坂,汗牛痛仆,仰天续命。”
“汗牛痛仆”的意思就是说牛已经累得浑身大汗了,主人仍要使劲抽赶。在传统社会中,耕牛对于农民来说,不仅是家里最值钱的家当,还是他们劳作的伙伴,不到万不得已,轻易不会这样拼命使唤。但是即使这样拼命地干,田里产出的粮食仍不够糊口。
一个叫任启运的人说:“江南二百四十步为亩,山西千步为亩,而田之岁入,不及江南什一”。大同的地方志甚至说大同地区“岁丰,亩不满斗”。
莜麦是雁北的主要农作物,当地流行的谚语是这样描述莜麦生长情况的:“种一坡、打一车、收一簸箕、煮一锅、吃一顿、剩不多。”
听母亲说,解放前在得胜堡,就是地主家的日子也过得捉襟见肘。地主家比贫农家好在莜面能吃饱,但也不敢放开了肚子任性地吃。哪像现在电视剧那样,地主家的妇女,个个穿金戴银,一身锦绣。头发梳得油光,苍蝇站上去都能劈了叉。
那时候地主家的女人也是要干活的,要给全家人做饭,当然包括长工的饭啦。还有的后来被评了富农的,家里女人刚生完孩子就给牲口铡草,说出来人都不信。
听五舅说,得胜堡土改时,贫农斗地主,吃玉茭面窝头也算一桩罪证。一个贫农在控诉会上说,有一年冬天他去某地主家,看见家他家炉子下面烤着一个黄愣愣的玉茭面窝头。
那时候平常农户家很少有人吃得起玉茭面,吃玉茭面也是一种炫富的表现。直到七十年代,有的队干部表态时还把“带领乡亲们都能吃上黃窝头”作为口号。
地主则辩解说,那年冬天,他家天天都吃糠窝窝。那几个玉茭面窝头是亲家送来的,快烤焦了才舍得掰成几瓣儿让几个小孙子解解馋。
地主家尚如此,穷人家就更凄惶了。
得胜堡地板子薄,靠天吃饭,一亩地最多打几十斤。有点莜面,全凭和山药掺合起来吃,不掺山药粮食根本不够吃。平常人家,这一顿饭,吃粗粮还是吃细粮,吃干的还是吃稀的,都会精打细算。
所谓巧妇,就是要将有限的粮食,做成尽可能膨胀占肚子的食物,目的是求饱,不管营养。谁家要是无故吃一顿纯莜面,邻居就会议论:这家人不过了!年轻夫妻要这么过日子,长辈也会出面干预。

解放前,舅舅家在得胜堡算好人家,炕上能铺得起大毡。大多数人家就连席子也铺不起,用糨糊、蛋清拌着草汁,把一盘炕刮浆的光溜溜的。
有的人家穷的连行李也没有,即便冬天也直接睡在光板子炕上,身上盖着随身的衣裳。炕烧得热了,只好不停地翻身;到后半夜炕渐渐凉了,会冻得瑟缩发抖。雁北有民谣曰:“穷汉的炕,四面烫,烫了脊背,烫脊梁,子冷了爬起来唱。”
听舅舅说,有的人家一家人就一床盖窝。娃娃们因为你揪我拽,能把盖窝面子扯得粉碎,烂棉花套子百孔千疮,棉絮四处洒落。那时人早起起炕,身上肉多处都是炕席的印记。有时脸上也有,半天不肯散去。娃娃哭时,两脚在席子上乱蹬,脚后跟磨得鲜血直流。
解放前的雁北,女孩子属于赔钱货,大多人家生下女孩都摁在尿盆子里溺毙了,然后扔在山坡里,让野狗吃了。此事现在老人们提起来都很平静,绝无悲戚的神色,倒是史载外国修女目睹此事,哀伤地泪不能禁。
从我有记忆起,得胜堡的人都没有内衣,所谓的内衣也就是个红主腰子。裤衩?没听说过。许多人家两代人睡在一条顺山大炕上,黑夜公公下地尿,也是光身子。
听五舅说裸睡省衣裳,裸睡为甚能省衣服呢?因为农家的炕席有点粗糙,容易磨损衣裳,所以男人一定要裸睡。裸睡,其实是有一点儿危险的。火炕热时,睡到后半夜,容易撩开盖窝,裸睡者的那点儿零件就会全部曝光,很不雅。
在我的记忆里,得胜堡的冬天非常冷。家里的水缸晚上都会结冰,早晨起来要凿冰才能舀出水来。只有队干部家里才有炉子,炉子砌在炕沿边上。
炉子的烟气有两个走向,暖家时移用炉筒子;烧炕时拉开插板烟气直通炕里。为了省炭,炉膛搪的就像一个成人的拳头大小,没有多大的热量。
一般灶镬紧挨炕头,灶镬上都稳一口七勺锅。做饭、煮猪食,甚至洗衣裳都用这口锅。有时候,猪食刚刚煮好,还没有盛到盆里来,猪就拱开门进来了,撵都撵不走。舀完猪食,用一个小笤帚把锅里的残渣往外一扫,再用搌布一擦,就可以给人做饭了。
天凉的时候,女人们想用热水洗衣裳。锅里的水一热,就把衣服泡进去了,也许还有孩子的尿布。我儿时就亲眼目睹过此事,现在想起来还反胃。
得胜堡人虽然守着大同煤矿,却无缘消受兰炭。做饭、烧炕全靠柴草。那时,农民一年到头缺吃少烧,不仅肚子填不饱,连灶镬也总是饥饿的。
得胜堡的人出门经常带一个耙子,用它来搂柴。男女老少,不管在哪,见了柴草就搂揽,即便如此也满足不了灶镬的血盆大口。天阴下雨没柴烧的时候,得胜堡的人一天就做一顿饭。多做些放在瓦盆里,用褥子围住放在炕头。早晨剩下的饭,到晌午还温温乎乎。

得胜堡没好饭,早饭一般是稀粥、炒面。喝完多半碗小米稀粥,碗底还剩点,就把炒面舀进碗里,然后就用筷子使劲地拌。拌成酷累状,就等于干饭了。
炒面是用莜面炒的,放在一个纸筋笸箩里,搁在炕中央。做纸筋笸箩是雁北村妇的一项绝技:
把烂纸浸泡、捣碎,拍在一个倒扣的瓷盆上成型。等纸盆彻底干透,轻轻地揭下来,然后用平常积攒的香烟盒里外糊裱出来就能用了。在没有塑料制品的年代里,这是居家过日子的重要物什。
得胜堡的晌午饭一般以谷面窝窝、毛糕、烩酸菜为主。为了省粮,得胜堡的谷子、黍子都是连皮磨的。吃时拉的嗓子疼,拉时暂且出不来,憋得脸通红。莜面鱼鱼、山药丸丸、莜面囤囤偶或才吃一次,用烂腌菜汤汤调着吃。
晚饭一般是熬稀粥、蒸酷累。酷累的做法是,把山药煮熟、捏碎,然后拌上莜面上笼蒸。酷累蒸熟了最好用锅炒一下。但炒酷累需要油,因此许多人家免除了这道工序。年景不好时,天天晚饭都是小米粥煮山药蛋,这种吃法叫“猴耍水”。我见过一家最穷的社员,山药蛋不洗,用搌布擦擦就下锅了。
入秋,得胜堡家家户户齐腰深的大瓮里,腌满了酸菜。腌酸菜的主要原料是崧根(苤蓝)的叶子,俗称“kuo子菜”。崧根在大同卖了,叶子舍不得扔,只好自己吃。这样又老又硬的菜叶子,腌之前必须用开水焯一下。吃时还需用铁锅烩,否则咀嚼不动。尽管吃起来满嘴乌黑,牙齿酸痛,也一直要吃到数伏。里面起了蛆,也舍不得倒掉。
来了客人,最隆重的待客饭是烙油饼、炒鸡蛋。鸡蛋一般人家都有,白面常常还要绕村去借。新女婿上门一般是跌鸡蛋、下挂面。挂面五十年代还没有,进入六十年代得胜堡才有了挂面。
1964年四清运动时,大同市郊区
政府派来的干部都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有两个队员轮到五舅家了,五舅给他们压荞面饸饹吃。由于准备的饭少,五舅五妗妗只顾敬让着叫客人吃,并向客人诳称他们已经吃过了。
当时,五舅的几个孩子都小,也都特别怕父母,所以,未经大人许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但一个个还是禁不住诱惑,围住人家,眼睛直勾勾地瞅人家吃饸饹。
五舅觉得娃娃们过于日眼的样子给他丢人了,就先是低声地、后是“恶狠狠”地喊着让娃娃们“往外滚”。几个娃娃灰溜溜地出去了,藏在院墙后面,期待着客人走后,能剩下些饸饹头子圪节节和调和之类的残羹冷炙,好让他们尝尝鲜,只有蓝梅一个待在家里哭着咋也不肯出来。不一会儿,只见五舅把蓝梅抱出家门,径直走到院墙跟前,把她倒提着一把扔进院墙后面的垃圾坑里了……
得胜堡的女人不上桌吃饭是传统,饭熟了给男人娃娃舀饭是天职。女人就在风匣旁边坐着,大家吃一碗给舀一碗。女人总是最后吃,打扫战场,大人娃娃剩下的胡乱吃几口。尤其困难年代,到最后往往盆光碗净,锅里剩点菜汤也要用谷面窝窝蘸干净。

听说共产前,土财主夫妇一般也在灶镬圪嶗里吃饭,长工们反而很隆重,都盘腿在炕上。也许有人不信,会问:凭啥?
其实也不凭啥,就像你现在雇了几个装修工人,你招待不好,人家不给你好好做,会偷工减料,甚至会暗害你。地主打骂长工?长工会给你半夜把粮垛草垛点着,然后就跑的没影了,你去哪寻?更有甚者会给你引来土匪,那就鼻子比脸也大了。在雁北,没听说过地主敢虐待长工的事情,就是为人鄙吝也不行。名声不好,今后就再也找不到愿意为你帮工的人。
直到七十年代末,得胜堡人还用石磨碨面。碨磨是个苦营生,需要不停地绕着磨盘转圈圈,既枯燥又费力,用不了多久,就会感到头晕眼花。粮食碨完了,磨膛里总会残留半斤到一斤的粮食碎粒。就是这半斤到一斤的粮食碎粒,也经常引得贼娃子光顾。记得儿时的一个夜里,舅舅家的磨被贼娃子扫了膛。妗妗呜呜地哭了,他们全家的心情阴沉了好几天。
合作化前,得胜堡半数人家都有一口大柜。大柜是生活必需品,家里的衣物都要用包袱皮子包好放在大柜里。好人家的大柜是榆木、水曲柳的,普通人家是落叶松、杉木的。
有钱人家的柜上摆着镜子及女人们用的梳头匣子;条件再好的人家还有掸瓶,里面插着鸡毛掸子。舅舅每年秋天总要编两个草圈子,放在柜顶上,每个草圈上放一颗西瓜。妗妗每天都要仔细地擦抹这两颗西瓜,据说这样可以放至深冬也不坏。
进入六十年代,木材属于国控物资。娶媳妇搞不到木材做大柜,人家不嫁,为了把媳妇哄进家,于是聪明人发明了用水泥来做大柜。
水泥做大柜的程序是,在平地上预制好水泥板材,没有钢筋就用废铁丝来代替。等到干燥固化,再搬到家里组合起来。一个大柜一块底,四块帮,下面还有四个水泥做的腿子。组合时,把交接处预留的铁丝拧在一起,然后再把里外缝隙用水泥抹平。待干燥后,里外打磨光。外面上漆、里头糊纸,就算大功告成了。
唯有大柜的柜盖是木头的,因为水泥的掀不动。如此制作的大柜可以乱真。
那些年,得胜大队分红时,每个劳动日还要倒贴一毛钱,干活越多,倒贴越多。后来有些老汉说死说活不下地了。他们说,反正是个吃不饱,我不相信大队能眼睁睁地看着我饿死。
得胜大队600多人,有七八十条光棍。舅舅对门院的刘老汉有4个儿子、11个孙子,全家共有5条光棍汉。有一些已经成年了仍是光棍汉。
有个四类分子的长子,快四十岁上还没说上对象,他有个小妹妹才16岁。正好五台洼也有一户这样的人家,经人出面介绍,让这个16岁女孩退了学,嫁给那户人家,把那户人家的女儿换过来与她哥成亲。硬扭的瓜不甜,这两家常闹别扭。
得胜堡还有一户人家,哥哥残废在家,妹妹为了服伺哥哥,始终不肯出嫁。想为哥哥换个对象,哪怕是聋子瞎子,她也情愿跟人家走。可就是没人肯嫁给她哥。一拖再拖,她已经二十六岁了。
那年堡子湾公社妇联召开全公社优秀妇女大会,得胜堡硬是把她作为优秀女青年给推荐上去了,说全村人都夸奖她是好闺女。公社妇联了解清楚情况后,哭笑不得,说,这该咋宣讲呢?但是,为了给村干部面子,她们把她留下了,还给她颁发了奖状。

直到八十年代,得胜堡人洗脸都用瓷盆或瓦盆,搪瓷盆村民买不起。无论家里几口人,都共用一块洗脸手巾。这种手巾多半是再生布的,又粗又涩。即便这种类似搌布的手巾一般也要用到发黑、发硬,千疮百孔时才可能换新的。只有社队干部家才有备用毛巾,客人来时使用,之后珍藏。
我没见过村里人刷牙。一方面没有刷牙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刷不起。只有个别复员兵,因有从部队带回来的牙膏,头几个月还刷,用完之后就再也不刷了。
那时,得胜堡的大闺女小媳妇们没有化妆品。讲究点的也就是买一盒海钵儿油,用于擦脸擦手。海钵儿油的油盒外形如同海蚌,故而得名。我至今也不明白,装海钵儿油的壳儿是人造的还是天然的。你说天然的吧,大小咋就能那么一致?
所谓海钵儿其实是海边的一种小动物,学名叫做蚌。鹬蚌相争中的蚌应该就是它。蚌就是蚌,咋叫做海钵儿呢?估计是蚌、钵读音相近,雁北人说话又不标准,就把海蚌误读为海钵儿了。
海钵儿油是不是从海蚌肉中提炼而成,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雁北乡间特别流行这种油。海钵儿油不值钱,一盒只卖一毛钱。可那年月在雁北乡间,10分工只挣八分钱,能花一毛钱买上一盒子海钵儿油,已属于中上等人家了。
大闺女小媳妇买上一盒海钵儿油,藏着掖着地节省着使。逢年过节用一用,出门走亲戚擦一下,当然相亲时那更是必擦不可了。也有家里穷的就连一盒海钵儿油也买不起的,出门时,只好找相好姐妹借用一下了。
说实在的,那海钵儿油并不怎么香,别说和现在女人们使用的名贵化妆品相比了,就是和现在一般的润面油相比,也差之千里。1968年,表妹粉兰来呼市,母亲送给她一盒两毛钱的“万紫千红”,粉兰欣喜若狂。回村后拿给闺蜜们看,嫉妒死一片人。
六十年代末,大量知青来到得胜堡,才给当地村民带来了一些文明和科学思想。刚来时女人们见到知青用香皂洗脸就说:“这洋胰子可香哩!洗完水别倒,给我娃洗下。”
开始村民还搞不懂知青早起刷牙时为啥会吐白沫沫,有人还当成新闻到处说:“这些大同娃娃不知日鬼啥,早起用个一头有毛毛的棍棍在嘴豁豁里来回擦,像擦沟子一样,还鼓撅撅地冒白沫沫。唉呀,真日怪!”
后来女生刷牙时,一帮娃娃在旁边齐声高喊:“擦沟子!擦沟子!”开始她们不知道喊的是啥意思,等明白过来,气得叼着牙刷满街追打这些娃娃。
得胜堡的产妇生产,要撩起席子,垫上过了罗的细土,以吸收血水。三天后,才清理血土,放下席子——称作“起肉刺”。
得胜堡的女人们很羡慕大同女知青成卷的卫生纸,她们就连草纸也用不起。得胜堡小学的女孩子们常常任由红潮汹涌,将裤子、凳子,染得一片血红。大太阳的上午,体育课,站在男生的前方,那种窘困与羞耻,你可以想见。
那时,村里人有病很少有去医院的,一来路远,二来看病得花钱。一般哪疼就在哪拔个火罐子,有的脑门上同时有三个紫红印印,看着都吓人。一旦病人拔罐吃药还不见好时,老乡就以为魂被鬼勾走了,深更半夜满村遍野地叫魂。一人叫:“××……回来……回来。”一人答:“回来咧……回来。”一声高一声低的让人听得毛骨悚然。
以前,人们把第一次煎煮的药汤叫作正剂,第二次煎煮的则叫作落(读lào)渣,第三次的叫三落渣。煎过三次以后,已无有效成份,就把药渣倒掉了。不过事有例外。
小的时候,我家有一个亲戚,家境较差,有了病吃不起药。平时他就到处收集人们家倒掉的药渣,拿回家后晒干存放,遇到有个头疼脑热时,他也不请医生看,就把收集下的这些药渣抓上点儿倒在砂锅里煎着吃。
在他的脑子里,所有的病都是一个“病”,而所有的药也都是一种“药”,是“药”就能治“病”。于是,一次一次地也就把病抗过去了。当然了,这是过去那个年代的事,现在的人听来,简直是天方夜潭。

后记:
清·徐继畲曾作《啖糠词》,谆谆告诫在晋官员,晋俗俭啬,石岭关以北寒瘠尤甚,丰年亦杂糠秕,你们可要怜悯这里啊。他在诗中用通俗的语言写道:“富食米,贫啖糠。细糠尤自可,粗糠索索刷我肠。八斗糠,一斗栗,却是转来沙一掬。亦知下咽甚艰难,且用疗饥充我腹。今年都道秋收好,囤有余粮园有枣。一半糠,一半米,妇子欣欣同一饱。昨行都会官衙头,粒米如珠流水沟。对之垂涎长叹息,安作淘洗持作粥。”
徐在另一首诗《驼炭道》中,则对五台人民艰苦贫穷的生活深表同情,他这样描述道:“隔巷相呼犬惊扰,夜半驱驴驮炭道。驴行黑暗铎丁冬,比到窑头天未晓。驮炭道,十八盘,羊肠蟠绕出云端。寒风塞口不得语,启明十丈光团圞。窑盘已见人如蚁,烧得干粮饮滚水。两囊盛满捆驴鞍,背负一囊高累累。驮炭道,何难行,归时不似来时轻。人步伛偻驴步碎,石头路滑时欲倾。日将亭午望街头,汗和尘土面交流。忽闻炭价今朝减,不觉心内怀烦忧。价减一时犹自可,大雪封山愁杀我。”该诗可与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卖炭翁》相媲美,读来让人潸然泪下,体恤民瘼之情,油然而生。
唐·白居易亦有《村居苦寒》诗,凄婉,催人泪下:“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纷纷。竹柏皆冻死,况彼无衣民。回观村闾间,十室八九贫。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唯烧蒿棘火,愁坐夜待晨。乃知大寒岁,农者尤苦辛。顾我当此日,草堂深掩门。褐裘覆絁被,坐卧有余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
注:雁北及内蒙古西部把水瓢称作勺头,七勺锅指锅中能盛七瓢水。九勺为锅族序列之首。再大的叫做出勺锅,视需要定做。冬天村里杀猪退毛时用的就是出勺锅。如今雁北乡间生活水平提高,不再以糠菜为主,家庭人口也减少,大多数人家采用四、五勺锅。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听老绥远韩氏讲过去的事情”
作者丨韩丽明
编辑:虫子
投稿邮箱:laojiashanxi@qq
.com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