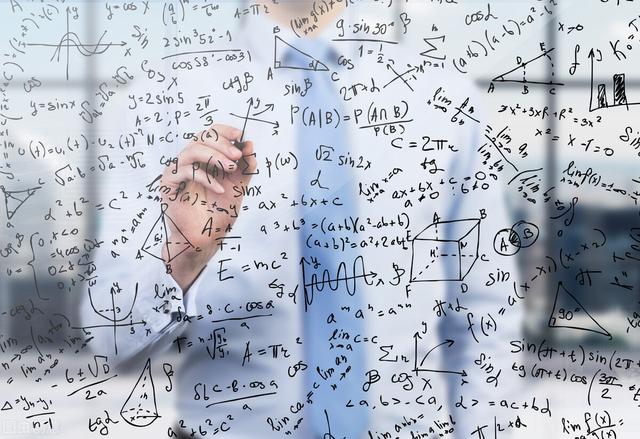乡儒吴泽源(乡儒吴泽源)
江 哮
2021年5月29日,泽源先生走完了他90年的人生历程,溘然长逝。
虽说耄年上寿,于吴老而言,已属奇迹。然而,噩耗传来,我仍不觉悲从心来。历历往事,如电影镜头在大脑沟回中一一闪过。遂展纸提笔,吟成一联,以寄哀思。联曰:
心萦桑梓作育英才痛遗泽已成千古
情寄诗文铸熔典册欣哀荣可慰此生
与泽源先生的交往,应该从1981年9月说起。其时,我在凉亭中学读初三。开学第一天,发现英语老师换了新面孔。他约五十岁上下,额头上两条展示人生沧桑的抬头纹特别显目,嗓音似乎有点沙哑,不紧不慢的语速倒是载满和蔼。让我大为惊奇的是,他的开场白居然是叽里咕噜不知所云的一段英语。可能觉察讲台下一片抓头挠耳的窘态,他立马用我们听得懂的汉语作了自我介绍,于是,我记下了吴泽源这个名字。

泽源先生全家福。
八十年代初的乡村中学,英语课被绝大多数学生视为畏途。社会上广为流传的一句话,一度成为很多英语成绩不佳的同学一个经典的借口:“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读English,照样可当接班人。”说来汗颜,我们学的都是地道的“哑巴”英语,新单词旁往往都是用自己能够看懂的汉字注音,比如English(应给利息)、good morning(古得摸您)、girl(格儿),如此等等,别出心裁。如果当今有好事者加以搜集整理出来,相信一定能够上热搜头条。英语老师的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有一天,一辆拖拉机翻在校外的农田,我们都跑去看热闹,等上课铃响起,好多学生才一窝蜂地往教室赶。值日的校长不明就里,正好碰上迎面走来的某英语老师。问:怎么这么多学生还没有进教室?答:tractor(猜克特儿)翻了。校长对英语先生望了两望,一幅云里雾里放光彩的模样。此情此景,至今想起,仍令人忍俊不禁。
进入初中后,我别的学科成绩还勉强过得去,唯独上英语课如同听天书,因此,每次考试成绩一直在班上十名之外徘徊。泽源先生的到来,消除了我对英语的恐惧。他一边上新课,一边教我们国际音标,一点一滴地纠正我们离谱的发音,我很快就从单词的拼读中找到了英语学习的感觉。他善于用归纳法教语法,比如:be动词的用法、肯定句和否定句表达、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用法、一般疑问句与特殊疑问句的结构、名词所有格式、冠词的应用、时态的变化(一般现在式、一般过去式、一般将来式、现在进行式、现在完成式的运用)以及主动句和被动句的变换,等等,反复训练,循循善诱。5月30日,在丧礼现场,我与夏中育校长忆起这些往事,他深有感慨地说:如果在泽源先生的班上英语成绩都提不上去,那只能怪自己的确不是一块读书的料了!泽源先生对我们要求极严,规定背诵的课文,他亲自把关,丝毫没有价钱可讲。偶尔听人议论,说他的英语是美国人教的,我虽似信非信,但还是在暗自仰慕中渐渐对他生出莫名的好感。也有在他面前调皮的时候。记得有一节自习课,泽源先生走进教室督促我们读英语,我突然萌生出捉弄一下他的想法。于是,胡乱写了几个单词请教他怎么读。泽源先生似乎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摸着我的头,笑了笑对我说,这些单词不符合拼读规则呀,你在故意蒙我吧?或许是亲其师才能乐其学,总之,初三一年,我真正对英语学习产生了兴趣,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泽源先生的学生看望他时合影。
我感恩生活的赐予,让我在攀登的樵途中找到了一根可资援手的劲藤!
一晃十年,我大学毕业后转辗回到了凉亭中学任教导主任,与泽源先生成了同事。在朝夕相处中,我对他的了解渐次加深。泽源先生出生于本镇月山村(现崇庆村)吴家门一个书香世家,幼时家境殷实,长兄吴泽煌曾毕业于黄埔军校成都分校,后随远征军入缅作战,不期喋血异域。泽源先生从小聪明好学,及长,负笈岳阳,于政权鼎革前毕业于湖滨中学,在这里,他受到了比较良好的美式教育,英语口语尤为地道纯正。据说,泽源先生尚在襁褓中,父母为其预卜前程。卦师断其时运不济,必将终老田园。其母不信,哈哈三声,最后将给卦师备下的厚厚包封减了大半。孰料造化弄人,泽源先生的命运竟被卦师一语成谶。土改过后,泽源先生就被贴上了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标签,在随后一波接一波的运动中,理所当然成了批斗对象,他只得夹着尾巴,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默默承受着生活的重压。一九八一年下学期,同村的荆作元老师受命主持凉亭中学的日常工作,考虑到英语师资力量极为薄弱,力荐他到这里代课。就这样,操了大半辈子牛鞭的他成了我的英语老师。

泽源先生与诗友论诗的场景。
泽源先生与世无争,他极少参与同事的酒局,也从不臧否人物,这或许与其民办教师的身份有关。除了一如既往的认真教书,业余爱好恐怕就是看书和下棋。当时,学校图书室每年都会购置一些新书,每有新书上架,泽源先生总是兴冲冲地过来借阅。我有时漏夜返校,发现年过六旬的泽源先生的宿舍还亮着灯,敲门一问,原来他还在津津有味地看书或抄写,一股敬意油然而生。一个冬日的清晨,我催学生起床做早操,路过泽源先生的窗下,猛听到他与人在激烈争论什么,心生好奇,伫立有顷,方知他与另一棋迷老师下了一个通宵的象棋。我推门而入,发现“棋迷”因悔棋不成脸色涨得通红,方知原委。泽源先生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与我打了下招呼,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天就亮了?
与泽源先生一年共事过后,我频繁地换了几个单位,与他的交往就随之相应变少。他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也许青年时高蹈过,自负过,但半世的磨砺和摧折让他学会了恬淡隐忍,安贫乐道。虽说只是一个民办教师,但看得出,他已很满足,毕竟生活境遇相比以前已大为改善。一九九七年下学期,我到区一中任校长,未几,竟意外收到他托人给我送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居然是一首七律诗。
七律·赠江哮
炎黄赤子龙传人,
正义存胸气寓神。
当有豪言追日月,
自无媚骨送公卿。
年华三十堪为范,
桃李八千多吐芬。
璞玉浑金经巨手,
风流潇洒步青云。
反复读罢,一股热流自丹田直往上窜。看得出,诗中不乏夸饰和溢美之词,但更多的是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何德何能,竟蒙先生如此垂念与厚爱?感激之余,我回赠了一首诗与他唱和。
七律·步吴泽源先生原韵并赠
五十始为执教人,
解惑传道显精神。
笔底文章辉日月,
胸中丘壑胜公卿。
不教白发催人老,
应似红梅傲雪芬。
回首桃李争妍处,
笑嘲功名付流云。
就在这一年,泽源先生告别了他心爱的讲台,回归他早已习惯了的农家生活。从五十岁出山算起,他已在这方讲台上站了十六年,时年也已届66岁,如果不是学校和师生一再慰留,他早就该退休颐养天年了。像深山中的一株幽兰,他寂寞地开过,却让芬芳溢满山谷,让蜂蝶在其身边既歌且舞。李义山有诗云:“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泽源先生当时的心境或许正与此暗合吧?当然,五柳先生守拙归田园时“乃瞻衡宇,载欣载奔”的心情,泽源先生是不会有了。因为,也是在这一年,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全部转公,在“关、转、招、辞、退”的政策之下,因年过六旬,泽源先生转已无望,退就成了必须。当年的同事江树甲老师撰写的挽联,就委婉地对他遭遇的不公寄予了深深的同情。联曰:
杏坛曾奋发,桃李多秀,正编难纳名师,学童常具情怀,生当其乐!
文彩亦豪放,诗联甚精,苍天不留耆老,遗著广传梓里,死应所安。
好在他有诗书相伴,闲散的日子竟被他侍弄得珠圆玉润,花团锦簇。泽源先生幼读私塾,打下了较为扎实的传统文化功底,对诗词歌赋尤为喜爱。运动年代,他的这点爱好被视为封资修的余孽遭到无情压榨。直到走上教育岗位,他才猛然发现,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如春草一样潜滋暗长。从此以后,每有会意,他必手自笔录。“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记不清与泽源先生有过多少次唱和,但每有满意的作品,他总是托人转交给我(他不懂网络发送),让我第一时间分享他的成就与快乐。记得我曾帮他在本地的报刊杂志上推荐发表过一些作品,例如《念奴娇·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
念奴娇·洞庭湖
洞庭湖上,白茫茫,水色天光融合。斗转星移波浪里,日月腹中升落。吞吐长江,流潴四水,气势壮衡岳。无边涟漪,曹操梦想横槊。
地设天造明湖,翠烟青螺,烟柳边新阁。玉立荷花舞百里,钓叟莲娃欢跃。桥卧清波,山衔好月,旭日红霞托。斯楼今上,深思范相忧乐。
自退休直至驾鹤西游,诗词作为他的真爱伴其一生,从这方面来看,泽源先生的人生暮年是无比快乐的。学生来访他写诗,老友相聚他写诗,胜日出游他写诗,盛典节庆他还是写诗……他用诗词描摹家乡的美景,讴歌眼中的盛世,抒发人生的感慨,也哀挽已故的亲友,用心用情,把余年吟成一首诗、一阕词,一幅联。例如,他的《六十抒怀》就禅意扑面,颇见性情。
六十抒怀
壮心已了慕田畴,世事营营任去留。
归里有情寻旧迹,听泉无意到源头。
深山野菊芬芳溢,流水闲鱼自在游。
酒醒诗狂难入梦,推敲南北对春秋。
同样,《村居》不事雕饰,洒脱自然,几疑得田园诗之真趣。
村居
村居自在人,烟霭锁柴门。
翠岭当屏画,清风扫俗尘。
山深花烂漫,林静鸟天真。
灵气生灵感,闲吟妙入神。
泽源先生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内,一任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他的诗词,大多格律工整,意韵悠长,迥异于时下所谓“老干体”。尽管年届耄耋,但在许市诗联协会,他可是公认的台柱。如果简单地对泽源先生进行盖棺定论,我觉得“乡儒”二字也许最为恰当。人生如寄,轰轰烈烈者毕竟寥若晨星,如果能像泽源先生一样,在世上留下这么一星半点微末的印记,我觉得也就够了。
哲人其萎也,呜呼!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