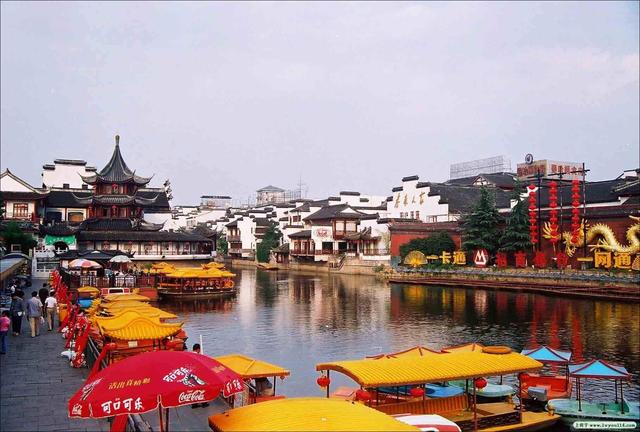冯骥才散文精选摘抄片段(阅读行动每周美文)
大概是我九岁那年的晚秋,因为穿着很薄的衣服在院里跑着玩,跑得一身汗,又站在胡同口去看一个疯子,拍了风,病倒了,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冯骥才散文精选摘抄片段?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冯骥才散文精选摘抄片段
冯骥才:我最初的人生思索大概是我九岁那年的晚秋,因为穿着很薄的衣服在院里跑着玩,跑得一身汗,又站在胡同口去看一个疯子,拍了风,病倒了。
病得还不轻呢!面颊烧得火辣辣的,脑袋晃晃悠悠,不想吃东西,怕光,尤其受不住别人嗡嗡出声地说话……
妈妈就在外屋给我架一张床,床前的茶几上摆了几瓶味苦难吃的药,还有与其恰恰相反,挺好吃的甜点心和一些很大的梨。
妈妈用手绢遮在灯罩上,嗯,真好!灯光细密的针芒再不来逼刺我的眼睛了,同时把一些奇形怪状的影子映在四壁上。为什么精神颓萎的人竟贪享一般地感到昏暗才舒服呢?
我和妈妈住的那间房有扇门通着。该入睡时,妈妈披一条薄毯来问我还难受不?想吃什么?然后,她低下身来,用她很凉的前额抵一抵我的头,那垂下来的毯边的丝穗弄得我的肩膀怪痒的。
“还有点烧,谢天谢地,好多了……”她说。在半明半暗的灯光里,妈妈朦胧而温柔的脸上现出爱抚和舒心的微笑。
最后,她扶我吃了药,给我盖了被子,就回屋去睡了。只剩下我自己了。
我一时睡不着,便胡思乱想起来。脑子里乱得很,好像一团乱线,抽不出一个可以清晰地思索下去的线头。
白天留下的印象搅成一团:那个疯子可笑和可怕的样子总缠着我,不想不行;还有追猫呀,大笑呀,死蜻蜓呀,然后是哥哥打我,挨骂了,呕吐了,又是挨骂;鸡蛋汤冒着热气儿……
穿白大褂的那个老头,拿着一个连在耳朵上的冰凉的小铁疙瘩,一个劲儿地在我胸脯上乱摁;后来我觉得脑子完全混乱,不听使唤,便什么也不去想,渐渐感到眼皮很重,昏沉沉中,觉得茶几上几只黄色的梨特别刺眼,灯光也讨厌得很,昏暗、无聊、没用,呆呆地照着。
睡觉吧,我伸手把灯闭了。
黑了!霎时间好像一切都看不见了。怎么这么安静、这么舒服呀……
跟着,月光好像刚才一直在窗外窥探,此刻从没拉严的窗帘的缝隙里钻了进来,碰到药瓶上、瓷盘上、铜门把手上,散发出淡淡发蓝的幽光。
远处一家作坊的机器有节奏地响着,不一会儿也停下来了,偶尔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货轮的鸣笛声,声音沉闷而悠长……
灯光怎么使生活显得这么狭小,它只照亮身边;而夜,黑黑的,却顿时把天地变得如此广阔、无限深长呢?
我那个年龄并不懂得这些。思索只是简单、即时和短距离的;忧愁和烦恼还从未有乘着夜静和孤独悄悄爬进我的心里。
我只觉得这黑夜中的天地神秘极了,浑然一气,深不可测,浩无际涯;我呢,这么小,无依无靠,孤孤单单;这黑洞洞的世界仿佛要吞掉我似的。
这时,我感到身下的床没了,屋子没了,地面也没了,四处皆空,一切都无影无踪;自己恍惚悬在天上了,躺在软绵绵的云彩上……周围那样旷阔,一片无穷无尽的透明的乌蓝色,这云也是乌蓝乌蓝的;远远近近还忽隐忽现地闪烁着星星般五光十色的亮点儿……
这天究竟有多大,它总得有个尽头呀!哪里是边?那个边的外面是什么?又有多大?再外边……难道它竟无边无际吗?相比之下,我们多么小。我们又是谁?这么活着,喘气,眨眼,我到底是谁呀!
我伸手摸摸自己的脸、鼻子、嘴唇,觉得陌生又离奇,挺怪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是从哪儿来的?从前我在哪里?什么样子?我怎么成为现在这个我的?将来又怎么样?长大,像爸爸那么高,做事……再大,最后呢?老了,老了以后呢?这时我想起妈妈说过的一句话:
“谁都得老,都得死的。”
死?这是个多么熟悉的字眼呀!怎么以前我就从来没想过它意味着什么呢?死究竟意味着什么?
像爷爷,像从前门口卖糖葫芦那个老婆婆,闭上眼,不能说话,一动不动,好似睡着了一样。可是大家哭得那么伤心。到底还是把他们埋在地下了。
为什么要把他们埋起来?他们不就永远也不能说话,也不能动,永远躺在厚厚的土地下了?难道就因为他们死了吗?
忽然,我感到一阵死的神秘、阴冷和可怕,觉得周身就仿佛散出凉气来。
于是,哥哥那本没皮儿的画报里脸上长毛的那个怪物出现了,跟着是白天那只死蜻蜓,随时想起来都吓人的鬼故事;跟着,胡同口的那个疯子朝我走来了……
黑暗中,出现许多爷爷那样的眼睛,大大小小,紧闭着,眼皮还在鬼鬼祟祟地颤动着,好像要突然睁开,瞪起怕人的眼珠儿来……
我害怕了,已从将要入睡的懵懂中完全清醒过来了。
我想——将来,我也要死的,也会被人埋在地下,这世界就不再有我了。
我也就再不能像现在这样踢球呀,做游戏呀,捉蟋蟀呀,看马戏时吃那种特别酸的红果片呀……还有时去舅舅家看那个总关得严严实实的迷人的大黑柜,逗那条瘸腿狗,到那乱七八糟、杂物堆积的后院去翻找“宝贝”……
而且再也不能“过年”了,那样地熬夜、拜年、放烟火、攒压岁钱;表哥把点着的鞭炮扔进鸡窝去,吓得鸡像鸟儿一样飞到半空中,乐得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还瞒着妈妈去野坑边钓鱼,钓来一条又黄又丑的大鱼,给馋嘴的猫咪咪饱餐了一顿;下雨的晚上,和表哥躺在被窝里,看窗外打着亮闪,响着大雷……
活着有多少快活的事,死了就完了。那时,表哥呢?妹妹呢?爸爸妈妈呢?他们都会死吗?他们知道吗?怎么也不害怕呀!我们能够不死吗?活着有多好!大家都好好活着,谁也不死。
可是,可是不行啊……“谁都得老,都得死的。”死,这时就像拥有无限威力似的,而且严酷无情。在它面前,我那么无力,哀求也没用,大家都一样,只有顺从,听摆布,等着它最终的来临……
想到这里,尤其是想到妈妈,我的心简直冷得发抖。
妈妈将来也会死吗?她比我大,会先老,先死的。她就再不能爱我了,不能像现在这样,脸挨着脸,搂我,亲我……
她的笑,她的声音,她柔软而暖和的手,她整个人,在将来某一天就会一下子永远消失了吗?她会有多少话想说,却不能说,我也就永远无法听到了;她再看不见我,我的一切她也不再会知道。
如果那时我有话要告诉她呢?到哪儿去找她?她也得被埋在地下吗?土地,坚硬、潮湿、冷冰冰的……
我真怕极了。先是伤心、难过、流泪,而后愈想愈加心虚害怕,急得蹬起被子来。
趁妈妈活着的时光,我要赶紧爱她,听她的话,不惹她生气,只做让大家和妈妈高兴的事。哪怕她还骂我,我也要爱她,快爱,多爱;我就要起来跑到她房里,紧紧搂住她……
四周黑极了,这一切太怕人了。我要拉开灯,但抓不着灯线,慌乱的手碰到茶几上的药瓶。我便失声哭叫起来:“妈妈,妈妈……”
灯忽然亮了。妈妈就站在床前。她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怎么,做噩梦了?别怕……孩子,别怕。”
她俯身又用前额抵一抵我的头。这回她的前额不凉,反而挺热的了。“好了,烧退了。”她宽心而温柔地笑着。
刚才的恐怖感还没离开我。这是怎么回事?我茫然地望着她,有种异样的感觉。
一时,我很冲动,要去拥抱她,但只微微挺起胸脯,脑袋却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刚刚离开枕头,又坠倒在床上。
“做什么?你刚好,当心再着凉。”她说着便坐在我床边,紧挨着我,安静地望着我,一直在微笑,并用她暖和的手抚弄我的脸颊和头发。
“你刚才是不是做噩梦了?听你喊的声音好大哪!”
“不是,……我想了……将来,不,我……”
我想把刚才所想的事情告诉给妈妈,但不知为什么,竟然无法说出来。是不是担心说出来,她知道后也要害怕的。那是件多么可怕的事啊!
“得了,别说了,疯了一天了,快睡吧!明天病就全好了……”
昏暗的灯光静静地照着床前的药瓶、点心和黄色的梨,照着妈妈无言而含笑的脸。她拉着我的手,我便不由得把她的手握得紧紧的……
我再不敢想那些可怕又莫解的事了。但愿世界上根本没有那种事。
栖息在邻院大树上的乌鸦不知为何缘故,含糊不清地咕嚷一阵子,又静下去了。被月光照得微明的窗帘上走过一只猫的影子,渐渐地,一切都静止了,模糊了,淡远了,融化了,变成一团无形的、流动的、软软而迷漫的烟。我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一个深奥而难解的谜,从那个夜晚便悄悄留存在我的心里。后来我才知道,这是我最初在思索人生。
(选自冯骥才《花脸》,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本道:寒山寺悟禅少时读张继的《枫桥夜泊》,还以为这寒山一定是个古木参天、风景佳秀的名山。许久之后,才得知寒山乃唐代一位高僧的名字。寒山寺始建于南朝,唐贞观年间,当时的名僧寒山和拾得曾在此主持。后拾得东渡日本,只剩下了寒山,后人便因僧命寺。平心而论,《全唐诗》中所收张继的40余首诗中,其他诗作称不上是上上佳品,惟独这首《枫桥夜泊》堪称唐诗中的精品。诗使寒山寺更加名重禅林;寺又使张继和他的诗远播重洋。今年暮春的一日,我有幸造访这千年古寺。
大雄宝殿的香火很旺,身着各色服装的善男信女们虔诚地顶礼膜拜着,众位高僧也手持木鱼,双目紧闭,肃穆地为膜拜者口诵经文。据说,寒山寺的古钟只有午夜时分才可敲响,千余年来,那108下钟声不知震撼过多少人的心扉。然而让我奇怪的是,眼下还是正午时分,伴随着大雄宝殿庭院里的袅袅青烟,钟楼里的钟声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寺内碑廊陈列的碑刻闻名遐迩,有《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对张继的这首诗,历来的注释一直比较低调,称其是一首抒发羁旅愁情的七绝。对此,我一直不以为然。特别是三四两句,以往普遍认为是凄楚的钟声使旅人的愁情更加浓烈。而我却以为,恰恰是这钟声使作者自省自警,从一腔愁绪中得到了解脱。按佛经的说法:“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生。”当年张继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归途羁旅枫桥,冷月西斜,栖乌惊噪,难免悲从中来。但作者的情绪并没有止限于此,当寒山寺夜半的钟声传来,他深受启迪,于是诗兴大发,留下了这千古绝唱。或许也正是这钟声才清除了他不第的烦恼,促使他继而刻苦攻读,再次进京应试,终于中了进士。果真如此,我想,那《枫桥夜泊》大概应该归于禅诗一类了。
本人并不信佛,也不谙禅事,但进得庙来也想体会一下个中的滋味。从张继夜泊枫桥的那段短暂的经历,可以悟出这样的道理,人在孤寂困窘之时,若能静心自虑,让思维产生另外一个亮点,想必会起到安抚心神,发人思索,寄寓对美好未来期待的作用。“禅”正是这样。但要学禅事进入禅的境界还真是件难事,只有靠自己的灵性去认识或领悟。古人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范例。唐代诗人王维曾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名句,意思是到了水穷之处不但不烦不恼而且产生了观云的兴趣。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现了作者被罢官后贬到边陲的心境,尽管孤独寂寞,却仍有“寒江独钓”的兴味。而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更是一种大境界、大超脱。正由于这样,我国历史上众多的知识分子尽管一生之中在宦海几经沉浮,但大多都能虚怀若谷,安之若素。
走出寒山古寺,朗日已经西斜,毗邻寺庙的古道之上,长街人流,裙带飘香,“人面桃花相映红”。许多人周身洋溢着朝拜之后的虔诚与满足。其实,这光怪陆离的人世间,正设置着种种诱人的机遇和恼人的坎坷在等待着他们。是春风得意抑或是厄运当途,任何人都无法预料。既然进庙烧香,就要有个禅的心态,否则,欲无止境,当了皇帝还想成仙,过高的期望值往往导致物极必反,喜极生悲。世事哪得诸般都占尽呢?凡人还是应该调整心态,安心静虑,平和地待人、待己、处事。即使是华盖当头又回天无力,那就学学庄子“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还能落得个“知足者常乐”的结局呢!
郭军平:家的情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只要你活在这个世界上,就不能不说名利。小到平民百姓,大到帝王将相,于永恒的宇宙而言,大家都是匆匆过客。永恒的宇宙送走了一批又一批过客,迎来了一批又一批新过客,历史于是在不断地翻转,人类于是在不断地在更新。在历史不断地翻转中,在人类不断更新中,哪些历史事件将成为永恒,哪些人将留下印迹,这些都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于现世的世界而言,我们都已经够忙碌的了,忙得像陀螺一样,有时都无法停止下来好好打量一下自己做的事情是否有意义,更何况于将来的世界?
因为,我们首先要生存。家是我们生存的基础,是我们灵魂与身心赖以停泊的港湾。我们的父母缔造了家,给予了我们成长的摇篮。经年以后,我们又要建立一个新家。为了家的幸福与温暖,我们劳苦奔波,不辞辛苦,无论大人还是孩子,都在辛辛苦苦地奔波,一代又一代,都在努力为这个家的未来和发展而忙碌不已。家是族群生命的延续,见证着这个族群的苦难与辉煌。
女儿小时候,看着鞋柜旁边的大大小小的鞋,随口说了句:“鞋是一只只停泊的小船,到了明天,又要驶向远方。”我为女儿新奇而新颖的比喻而诧异。我以为是女儿创作的,女儿一脸鬼笑,说“就是我写的”。我说:“如果真是你创作的,那你真不得了,快成诗人了。”妻子笑了笑:“难道娃就不能成诗人?”我想了想:“娃肯定能,不是有个名人说到‘孩子是天生的诗人’。诗人贵在童心,只有童心未泯的人才能成为诗人。”我又说到:“即使这句话不是孩子说的,但孩子能见景生情说出这么一句也值得点赞。”是啊,白天,我们都忙忙碌碌,哪里能那么诗意地看一下劳碌了一天的鞋子呢?
女儿说的那一句诗好啊!这一句诗道出了我们做人的不易,生存的不易。为了一个家庭的繁荣与幸福,我们不得不日日夜夜奔波忙碌不已,上班、交往、购物、走亲、访友、参加各类活动等等;孩子们上学,补课,学画画、舞蹈等等。大大小小的人都在忙忙碌碌,都在奔波不已。大人们奔波既为自己好,也为孩子的未来好,更为年迈的父母有一个幸福安度的晚年;孩子们也一样,为做着和大人们要做的事业在为未来而打基础。
生活不易啊!我们人类不仅是宇宙的匆匆过客,甚至也是家的匆匆过客。我们创造了美好的家,可是我们却常常难以平心静气感受这个家的美好。家里的花草浇了吗?书柜里的书读了吗?和孩子倾心谈话了吗?和父母爱人共餐了吗?......
今天你在家吗?无论再忙,还是多呆一会儿,让家成为温馨的港湾,心灵栖息的园地。
李娟:姑苏风情画杏花春雨里,走进苏州平江路的友苏美术馆,看着一幅幅充满生活情趣的工笔人物画,一瞬间被深深吸引。这些似曾相识的作品,不是在网络广为流传谢友苏先生的作品吗?
画中三两对弈的好友,或凝视或沉思,神情生动,惟妙惟肖。树下打盹的白发爷爷,水边垂钓的父子,光着屁股的小儿,人约黄昏后的一对羞涩的恋人。人物笔墨细腻,表情幽默诙谐,使读者会心一笑,笑过之后,还有悠长的回味。
在美术馆巧遇著名画家谢友苏先生,和谢老师聊聊赏画的感受,短短十几分钟,如沐春风。谢先生儒雅温和,乃是江南的谦谦君子。我买了他的画册《江南人物志》,请他签名留念。走出美术馆,坐在小河边的石阶上,看着漂在水上的小木船,听着木船“咿咿呀呀”的摇橹声,打开画集细细欣赏。风雅的姑苏城,枕河人家的人间百态、喜怒哀乐,都在画家的水墨丹青里。
《惊梦》一幅画中,阳光和煦的小院里,母亲脚下放着一盆清洗过的衣裳。她双手拧着湿漉漉的衣裳,竹竿上挂红花的被单,竹竿的一头,一个五六岁的小男孩替母亲撑着竹竿。忽然,裤子滑落在脚踝上,露出白胖胖的小屁股。孩子一声惊呼,将竹椅上打盹的父亲从梦里惊醒了,戴眼镜的父亲睁着一双小眼睛惊诧地望着儿子,手中的书也掉在地上。小男孩的表情最为传神,他歪着大脑袋,双手用力撑住竹竿,他张大了嘴巴,仿佛能听见稚嫩的声音,我的裤子!真是恬淡美好,一派天趣。想必赏画人和我一样咧着嘴乐了,多么温馨幸福的一家人,可爱的孩子、勤劳的母亲、读书的父亲,这分明是寻常人家最真实的写照。
杏花开了,穿长袍的父亲站在花树下赏花,微风飘过,杏花闲闲自落。父亲伸手接着翩翩的落花,姐弟俩在树下玩耍,男孩撩起衣襟去接风中飘落的花瓣,落花如雨。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杏花雨》是一位怀揣诗情的父亲与孩子们一起赏花的情景。画上有一行小诗,也是点睛之笔,与画相映生辉。画上题诗:“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看着赏花的父亲,令我想起丰子恺,只有这样的父亲教会幼年的孩子,学会去爱尘世美好的、值得爱的一切。
另一幅《祖孙情》中,白发如霜的爷爷坐在藤椅上,刚刚洗过脚。父亲坐在木凳上,怀里抱着老人的脚,他低着头,屏住呼吸,给老父亲修剪脚趾甲。头上留着一撮毛的小男孩手执一盏煤油灯,为父亲照亮。祖孙三代,一盏灯火,温暖感人的画面。一代代中国人,就是这样传承中华民族的孝道和美德。画上有诗:“一盏煤油火,三代祖孙情。 ”百善孝为先,孩子手中的那盏煤油灯,照亮祖父和父亲的脸,也映照着天下儿女的心。
《书中乐》中分明画了一位“书痴” 。穿蓝布长衫的老人,他跷着二郎腿,依靠在床头读书。他坐拥书城,枕边是书,书架是书,桌和地上也摆满了书。笼中的小鸟不叫不闹,静静望着主人。他手捧一本线装书,一双小眼睛睁得圆溜溜的,读得如醉如痴。他伸出舌头,手指放在唇边,蘸着口水将要翻开下一页。此刻,好书如佳茗,滋味悠长。
读书之乐要属五柳先生最懂得深意,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画中人也和五柳先生一样,读到一本令他欣然忘食的好书。书中佳趣,书中之乐,不可与外人道也。春风沉醉的清晨,空气微醺,洁白的琼花在水面摇曳。此刻,在江南的春天里,我只想做一个安安静静的读书人,多么幸福。
谢友苏先生的画,皆是一幅幅姑苏人家的风情画。画里弥漫着江南人家的烟火气,洋溢着生活的恬淡与妙趣,令人爱不释手。尘世里的脉脉真情,友情,亲情,爱情,都在他的画里。画里充满文人生活的闲雅之味,江南人家生活的趣味,洋溢着尘世浓浓的人情味。
段正山:秋天,也是一种开始许多人都喜欢礼赞秋天金色的收获,而就是在这种礼赞之中,秋天却悄悄给人们一个凄凉的空白。
秋天的果实对于春天的花蕾来说诚然是一种圆满,而秋天的落叶对于春天的芬芳来说却是一种终结。没有哪个季节比秋天更能让人感到生命的璀璨与生命的枯萎竟是戏剧般地连在一起,几乎就在一夜之间欣喜可能就会变为疑惑,甚至就在同一片风景里,这边是丰硕,那边却是落寞。
然而,这实在不是秋天的过错,而是看错秋天的人的悲哀。
当一种追求终于得到报偿,一种拥有足以成为辉煌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用满足衰减曾经的愿望,用得意吞噬往日的激情了。
于是,我们时常站在一个高度而无法逾越,时常徘徊在一种境界的面前而茫然无措。
其实,时光从不会停滞,季节也不会有断层,只要愿意并为之努力,我们什么时候都可以给世界一个惊奇,给自己一个惊喜。
既然秋天不会给我们永恒的完美和充实,秋天只能是更高意义上的开始。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沉醉太久,沉醉只能使我们在严冬中颤栗而不知所措。相反,鼓起壮志迎上去,即使在严冬的风雪中练就的也将是更厚实的勇气。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只是慨叹,金黄变为枯黄是一种凋落,也是一种新生,只为凋落唱挽歌,绝听不到新生的奏鸣曲。
秋天里我们毕竟不能有太多的失意,心中的灰暗太多,就是给你的都是朗日晴空,又怎能穿过厚厚的冻土,为春天献上一抹绿意?
秋天,也是一种开始。
不妨把或多或少的收获放进日记,不妨把亦真亦幻的追求交给岁月,不妨抖落掉满意的笑声也抖落掉不满意的愁云,不妨忘记徒伤的辛苦也忘记并不辛苦的幸运,迎着一天比一天强劲的西北风出征。
把秋天作为开始,四季才会崭新。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