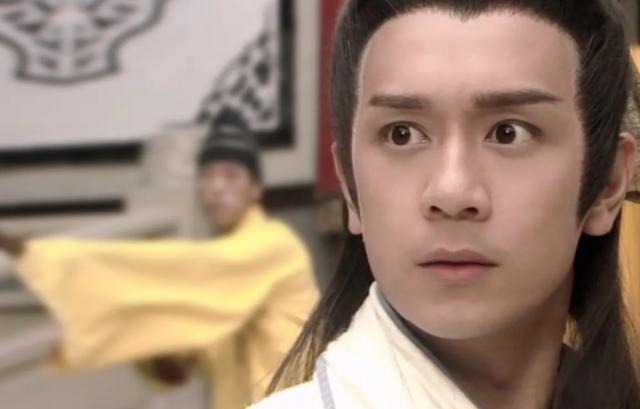厉以宁为张家界把脉(吟道夕阳山外山)
吟道夕阳山外山
——怀念厉以宁先生
王 超 逸
溪水清清下石沟,
千弯百折不回头。
兼容并蓄终宽阔,
若谷虚怀鱼自游。
心寂寂,念休休,
沉沙无意却成洲。
一生治学当如此,
只计耕耘莫问收。
——厉以宁:《鹧鸪天·大学毕业自勉》
一九五五年
时令“雨水”刚过,“惊蛰”即将来临。北国桃花正在吐蕾,南国已是杏花春雨。春节后,我第一次外出,到了福建的福鼎市。朋友们陪同我游览了太姥山地质公园。太姥山已溪流淙淙,山脚的玉兰花正楚楚绽放。下山后,朋友安排品竹洋白茶。谈天中,忽然得到了学校同仁章铮兄发我的一条意外的消息——厉老师走了。
我的心猛然收悚。
先生还是走了——离别他的亲人,抛开了他的弟子,抛开了故国家园,抛开了他的时代。
先生累了,他走完了长长的一生。
顿时,我脑海一片空白。
为存史实,我的回忆文章,重点征引先生的原话原文。
——忘不了,12年前,2010年7月11日,我与从美国留学归国省亲的小女王儒雅到吴越之地游玩。一天,我们正在宁波的天一阁驻足观赏,忽然接到了先生的电话:“超逸,我是厉以宁,书稿的序已经写完,抽空你来我家取走”。

——忘不了,先生以人为镜。时隔36年,两度吟咏老校长马寅初先生。叹时事沧桑,叹人间正道。
陈词滥调几时休,
笔伐口诛无尽头,
五四精神何处去,
燕园不是旧红楼。
(其一)
波中塔影正悠悠,
传统相承未断流,
处处夜深私语切,
人人心内有红楼。
(其二)
——厉以宁:《七绝·纪批判马寅初大会》
一九五九年
罢官遭黜寻常事,
难夺匹夫志。
当年何故不低头?
墙上芦苇摇摆实堪羞。
安危荣辱抛身外,
留得尊严在。
今生无愧是宗师,
亮节高风传与后人知。
——厉以宁:《虞美人·为马寅初先生铜像揭幕而作》
一九九五年
从“五九”到“九五”,“红楼”还是“红楼”,“马寅初”还是“马寅初”,厉老师守恒如一。
——忘不了,1988年,值母校诞辰90周年,您写下了《共同的心愿》一文。在文中您深情地回顾:
“哪怕是在50年代初,当本本主义的教学模式开始统治北大讲坛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在图书馆内仍然能接触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学术讨论的最新信息:在同教授们私下的交谈中,仍然能学习到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东西。哪怕是60年代初,当盲从已经变成了一种灾难,思想的禁锢已经越来越变为现实的时候,我作为一个青年教师,仍然能从同辈人那里听到对权威的观点的评论,仍然能从学生中间了解到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问题:不是个人的得失,而是社会的前途。也许60 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是一段最艰难的日子。‘经典中没有谈过的问题不容许讨论;经典中已经谈过的问题,不必再讨论。’但这场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的风暴,并没有把北大所固有的探索精神毁灭掉。讨论可以被扼杀,思考却无法制止。何况被扼杀的也只是公开场合的议论,每一个北大人总有那么几个知心的伙伴,小范围内的探讨,岂是禁止得了的?于是出现了两个北大。一个是外界看得见、听得到的北大,那是浮在水面上的北大;另一个是只有生活在北大,同北大的命运始终拴在一起,继承并发扬了探索精神的北大人才能察觉到的北大,这是深藏在北大人心中的北大。不了解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实际上存在着两个北大的人,是不了解北大的。结果呢?愚弄者被愚弄了,欺骗者被欺骗了,想铲除北大探索精神的人的打算落空了。北大依旧是北大。”
“为什么‘不断地探索’会成为北大的传统,我想,谁也不容易三言两语就回答这个问题。蔡元培校长的功绩、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民主广场……在北大的历史上,这些都是不可磨灭的纪事碑。但我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使北大的探索精神得以代代相传并且紧紧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的主要原因,是北大人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北大人是永远不会满足现状的。假定现实社会中一切都已经尽善尽美了,假定现实生活的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那么我们又何必学习、探索呢?那么我们在学习中又能追求到什么呢?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导致当年的北大人,冲出校门,同旧秩序展开斗争,发扬了五四精神、‘一二·九’精神。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导致现在的北大人,冷静地思考世界经济技术发展的大趋势,分析中国经济技术落后的根源,寻觅民族振兴的可行的方案。探索是为了革命,既包括当初的第一次革命,也包括今天的第二次革命。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使探索精神成为北大的传统、北大的生命力、北大的永远的骄傲。”
这是先生散文中的极品。在北大125年的校史纪念的散文中,堪与鲁迅的《我观北大》一文相媲美。先生的美文一出,在我校不同院系不同的纪念场合,有无数次被师生朗诵,暮鼓晨钟,春风化雨。

——忘不了,1998年,值母校诞辰100周年,您深切地回顾母校,言语中浸透了您对母校的深情。
“回顾北京大学的历史,优良学风的形成经历了多少曲折?但正像清清溪水流出深山那样,千弯百折也不回头。若干代教师和研究工作者的努力,终于形成了北大的学风。独立思考,自由探讨,这同教师的整体素质有着密切的关系。离开北京大学的毕业生,哪怕经过了好些年,一谈到当初在校时的情况,总会留恋过去。他们留恋的是什么?红楼,民主广场,未名湖,博雅塔?孑民堂,三院,图书馆,大讲堂?……不错,这些都值得留恋。也许更令他们难以忘却的是北大校园内独立思考和自由探讨的风气,是师生之间、同事之间、同学之间那种平等的学术讨论。这对每一个曾经在北大工作过和学习过的人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甚至可以认为是受益终身的。这不正说明北大教师的整体素质所养成的学风对后来者的深刻影响么?”
——忘不了,1994年9月的一天,您深情的寄语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教师同仁:
“单就教学工作而言,全体教师都应当懂得:能力的培养比知识的传授更加重要。这里所提出的能力的培养,是指让学生具有提出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直到开辟某一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新途径的本领。长期以来,我在同学生谈话时,喜欢用‘拓荒能力’四个字来概括这种本领。我感到,当我们采用‘拓荒能力’这四个字的时候,我们将会对我们工作的性质有比较深入的理解,因为这样就把研究本身看成是一件‘拓荒的’工作,许多资料由我们去收集,许多问题靠我们去发现,新领域将由我们去开辟,新道路将由我们去探索,新的解答也将由我们提出。躺在前人的书本上,或者迷信前人的经验,那是寸步难行的。”
……
“独立思考、假设、检验、创新,这些都是联系在一起的。通过独立思考,就会提出假设。一切新论点,在刚开始被提出时,都可以被看成是一种假设。但研究中的任何假设在提出后,都需要验证。研究将在不断的假设与验证中前进。在这里,一个提出假设的或对假设进行检验的研究者,自己应当成为自己的最不容情的质疑人。提出假设需要知识和勇气,进行验证需要科学方法和毅力。根据我多年来的教学经验,我感到,年轻人在这方面要克服急于求成的情绪。要使自己的新论点经得起检验,就一定不要急于求成。急于求成,是能力的缺陷,也是缺少毅力的表现。要反复告诉学生们,不要害怕挫折,不要总想一蹴而就。天底下如果有那么容易取得成功的‘突破’,那还叫什么‘突破’?”
——忘不了,2002年10月24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演讲时,言语之间,您一抒教师之志。
“我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一名教师。是教师,就有教学任务。”(《厉以宁北京大学演讲集》)

——忘不了,2003年9月,您在您的散文集《山景总须横侧看》后记《解悟人生已晚年》一文中,您向后人坦露了您的人生觉解,度人金针。
“解悟人生,重在一个‘悟’字。悟了,就心静了:悟透了,就心安了。2002年3月底,我从广东阳江去肇庆途中,路过新兴。新兴有一座国恩寺,是唐代名刹,六祖惠能出生在新兴,国恩寺又是他的圆寂之地。国恩寺内有一六祖堂。方丈请我题词,我即兴赋了一首《七绝》。
六祖堂前悟性生,
菩提明镜意中成,
此心长似清泉水,
处处无声即有声。
——厉以宁:《七绝·广东新兴国恩寺》
二○○二年
无声并非胜有声,无声就是有声。只要对人生有所解悟,任何回忆都不会引起伤感,即使是伤感时光流逝太快。只要解悟了人生,就会更加理解大自然的规律。日出日落,潮升潮退,花开花谢,谁能违背这一自然规律?山景总须横侧看,尽管同一个地点,日出的同时不可能有日落,潮升的同时不可能有潮退,但世界这么大,海洋这样广阔,此处日出,彼处不正日落吗?此处涨潮,彼处不正退潮吗?至于花开花谢,那就更有意思了。花的种类繁多,这种花已在凋谢,那种花正在绽放,这是常见的。同一种花在同一个地方,也有边开边谢的。
花开也是花飞日,月亏且作月盈时。这就是人生。这就是对人生的解悟。”
——更忘不了,上个世纪80年代初,由北大哲学系鲁军先生首倡,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为发起单位,联合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海外国学、汉学家,成立了中国大陆第一家书院——“中国文化书院”,揭开了书院教育这一传统与现代交汇的教育模式。由梁漱溟、冯友兰、汤一介、鲁军诸先生延聘了国内外第一批通儒学人做书院导师,由此奠定了书院第一阶段的辉煌。您是第一批被书院延聘的导师之一。那时您风华正茂,郁郁勃发,时年54岁。本人有幸作为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有幸成为厉门关门弟子。由此,与先生结缘近四十个春秋。

您是负有使命而来的。世人给您的雅称是“厉股份”。其实,这只是一个借喻。您长长的一生,完成了一位学者从学人到通儒到通人的演化。如果不是曲解的话,您是思想家、经济学家、教育学家、诗人的复合体,是时而风雨星驰,时而漫步思索与诗意栖息的命运交响。在这几个角色之中,您的底线和红线是良知、责任和担当。您从年轻到中年的装束,由中山装到西装,到唐装,到汉服。由西学(西方经济学)到中学(儒、释为主)到人学。
在您生命的最后十几年,远观您的背影——中等的个儿,稍显臃肿的身子,碎步,蹒跚而稳健,像一个陀螺,又像一只企鹅。仰视先生,乃是恂恂一大儒;背面看,又是蔼蔼一圣僧。我暗自伤悲:“吾师垂垂老矣!”。
您博通万物,乃天纵之才。当年,文化书院中外比较文化理论研究班,鲁军先生、冯友兰先生和您构架了以比较学为哲学观和方法论的,以中外文化比较、中外文化会通为架构的教育与科研的新型态。您与通学们确定了书院宗旨: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性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并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其中铺设了15个专业:1、比较方法论;2、文化学概论;3、马克思主义文化学;4、中国文化概论;5、日本文化概论;6、西方文化概论;7、印度文化概论;8、比较哲学;9、比较文学;10、比较美学;11、比较法学;12、比较史学;13、比较宗教学;14、比较教育学;15、比较伦理学。

那是个热闹的季节,是个风流的季节,也是一页发黄的历史了。
相对于我的学长学姐们,我是年龄最轻的一位。我的同窗们更多的是研究“道”的关乎形而上的学问,如比较方法论、文化学原理、比较哲学、比较美学、比较文学、比较史学等以比较方法论和文、史、哲为核心的人文学科。我天资平平,更注重“器”的关乎实用学科和应用学科的研究。当然也有我崇生、贵命的对生命哲学的考量和选择。故而我对管理哲学、企业文化、经济管理、企业管理更是倾心倾力。我当然明白,对于形而上学的学问,那是“道”的学问,应用学科、实用学科是“器”的学问。
每个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习性和禀赋也是不同的。我更崇尚实学,力行格物致知、经世致用、知行合一。故而,几十年来,我最好的年华,主要的精力都致力于追踪先生的踪影,致力于经济学、管理学、企业文化学的研究。这只是一个方面。其实,在应用学科、实用学科的背后,潜伏着人文主义和精神人文主义的伏脉,而这更是与先生神交、心交,气脉相通的。先生所以执一不失,君御万物,也正是您在精神人文主义上通天透地。世人所认同您的在经济学上的贡献,也只是您思想、学问、情操的冰山一角。

对于企业文化学的关注和研究,念兹在兹,倾注了您的毕生心血,贯穿了您的一生,明显可以溯源您的精神源流:
1、1990年,您在为管益忻、郭廷建著《企业文化概论》(人民出版社)作的序中,重点是关注哈维·莱宾斯坦提出的“x效率”理论、“企业凝聚力”。指出企业管理思想变革的方向是转向非经济因素。
2、1998年,在为《卢作孚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序》中,除继续强调经济学中“x效率”的重要性外,重点转向了对企业家特质和创业精神的研究。将企业文化的民族化、本土化传统上延至20世纪的20年代至40年代。先生确定,“卢作孚先生创立的民生公司,有理由被认定为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内企业文化建设卓有成效的一个范例。卢作孚先生是我国近代企业文化建设的最早倡导者之一。”由此,为批驳企业文化理论外来说奠下了理论基石。
3、2010年7月11日,在给由我主编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一书的《序》中,您重点从六个方面,对当下和未来世界企业文化的现状和前瞻问题作了总体把握。
(1)认同和企业凝聚力;
(2)效率和企业管理模式;
(3)公平和企业内部矛盾的化解;
(4)处理企业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原则;
(5)继承问题;
(6)企业文化的趋同与差异。
从1998年到2010年,时间跨度14年,国家经济总量跃升到世界第二位,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经济发展、企业管理随着体量的增大,管理变革向纵深发展,呈现出更多的复杂性、巨变性、代际性,那么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民营经济代际传承的问题,国民收入差距问题,第三次分配问题,滋生新的剥削阶层、乃至剥削阶级问题,“国家富强”与“人民富裕”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所呈现的跨国公司,国际贸易中的多元文化差异与碰撞,跨文化管理问题,比较文化、比较企业文化,国家安全问题,国家文化安全,国家企业文化安全问题,都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您面前,先生以您丰富的经验和理论储备,以战略高度,全球化眼光,未来意识;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都做了集大成式的理论刷新和架构。
拜登之前的美国前政府是特朗普时代,作为财阀出身的特朗普,与作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拉开了全方位的贸易战,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合纵连横,那么,跨文化冲突、多元文化差异突出地摆在了世界决策学家、管理学家面前。这是个时代问题,是个时代课题,是21世纪的全球命题。中国的管理学家能不能认清这个问题,碰撞这个问题,把握这个问题呢?在外国神话之中,有“亚洲王之剑”的故事。作为一代大思想家,一代经济学宗师,先生早已洞察这个问题。远在1989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行至半途,而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那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远不明朗,远未确立,可是身边的亚洲五小龙已经次第崛起,一个太平洋世纪即将来临。先生就高瞻远瞩,在思考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和与之相辅相成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目标,和与管理体制相辅相成的企业文化和跨文化管理的方法和规律。
先生谆谆地告诫我:“中国企业文化的哲学基础是什么?在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中研究如何协调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为了促进经济的低碳化和坚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方式,如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企业文化建设之中?企业文化建设和消费文明建设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企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所有这些课题都是20年前不曾涉及的,或当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
再以我手头这部书稿所讨论的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说,这同样是一个新的课题。与1990年相比,改革和开放所取得的进展不可避免地使中国的企业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这是因为,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企业文化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多样性的。中国改革的深化,使改制后的中国企业无论在内部管理中还是在市场营销中都要适应新的的人际关系和新的客观环境。各国的企业都离不开本土的文化传统,而在国际市场上,各种不同的文化通过企业间的竞争和合作,文化之间的摩擦和冲突时时可见。特别是在外商进入中国国内投资建厂或中外合资办企业时,企业文化可能出现这种或那种不协调现象。至于中国资本‘走出去’之后,无论是在外投资建厂,或进行兼并重组,也会遇到类似的企业文化冲突的情况。因此,在国内,比较企业文化学的研究在现阶段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厉以宁:《比较企业文化学原理》序)。这是先生对我的嘉勉,也是对我阶段性理论研究成果的肯定。
您全面完整地回顾了新时期以来企业文化伴随着改革开放、民族复兴、经济复兴、管理变革全过程。集中解决了困惑企业家和中外企业文化研究者多年的突出问题,将这些成果上升为基本原理。“序”煌煌万言,我深深地体味,这是您对世人所做的最后的交代。
更让我感动的是,先生为了推动“比较企业文化学”尽早为学界和社会关注,在该书尚未出版发行之际,就提前一年,率先在我校校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的首期,刊载了这篇序言《关于中国企业文化的几个问题》。先生是“本刊编辑委员会主任”,但是,编委会同仁都知道,该刊一般不刊发“序”“跋”之类文章,先生一般也不在其主管的杂志上刊发自己的文章。由此可见,先生对这一填补学术空白的新兴学科的重视,先生对这一学科带头人的倾心呵护,先生无疑是新兴学科的助产妇、新生力量的伟大的保姆。
先生接过了“亚洲王之剑”。您完成了今世的使命,又将利剑传递给了后人。
暮年的冯友兰先生在《我所认识的蔡孑民先生》一文中,在谈到当年在纽约的中国留学生为蔡元培先生开的一个欢迎会时,追忆了蔡元培老校长讲的一个故事:“说是一个人的朋友得到了神仙的法术,能点石成金。这个朋友对这个人说:我能点石成金,你要多少金子,我都点给你。这个人说:我不要金子,我只要你那个手指头。全场哄然大笑。蔡先生接着说:‘诸位同学到国外留学,学一门专业知识,这是重要的,更重要的是要得到那个手指头,那就是科学方法。你们掌握了科学方法,将来回国后,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可以对中国做出贡献。’”
先生的思想学问,一部分为官民两界、雅俗两界所认同所尊崇,还有一部分将留待历史去检验,留待后人去评说。实践的画卷在铺展,理论之树还在发育、生长、繁茂。任何理论家都不可能终结真理,任何理论家都不是算命先生,您也不是算命先生。
坚守教师的本分,坚守学人的良知,坚守理论上的突破,听从实践的审判,这就是先生的心力、定力。
若有人问我,北大的精神魅力何在?我回答:科学、民主、自由;求索、为新、向上;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的抗争精神。从蔡元培先生提出“囊括大典,网络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到鲁迅先生提出“北大是常为新的”,到先生提出“只计耕耘莫问收”,这就是北大的魂,是历经百年北大人共同智慧的结晶,是北大人的骄傲与光荣,也是先生的骄傲与光荣。

家父几与先生同庚,是位普通工人,已退休多年,闲来在家看书。从邓小平同志的著作到先生的著作。在与我谈到先生著《难忘的岁月》(中国三峡出版社)一书时说:“你老师与邓小平的话都是实话、真话。他不容易呀。他的夫人在鞍山,两地分居十多年。他又被下放江西鲤鱼洲,孩子又不在身边,在那个年代,他还不忘记看书、思考,还不忘记对这个国家命运前途的忧虑和等待。”
先生生于1930年11月22日,出生于南京,原籍江苏仪征。初中就读于湖南沅陵雅礼中学,高中就读于南京金陵大学附中。1951年考取北京大学经济系,195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2005年,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1999年任北大社会科学学部首任学部主任。2005年,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今天是先生过世第三日,如何回望先生,如何定位先生,亦何言哉?亦何言哉?
呜呼先生!
哀哉先生!
大哉先生!
1978年,48岁之前的先生,志不得伸,守机待时;48岁之后的先生,“只计耕耘”,披星戴月,匆匆赶路。其实,先生是位天涯孤客,在您的繁华的背后,深埋着您的孤寂、忧思和悲悯。您的长长短短的一千多首诗词吟霄,多数是在夜深人静,泪湿枕巾,仰观星宿,谛听天籁之中泣吟而成。“四更梦醒再推敲,短长句句皆心血”。(厉以宁《踏莎行》2007年)
先生在湖南沅陵雅礼中学读初中时,曾在学生办的刊物上以“山外山”的笔名,发表过长篇小说。
龚自珍有诗云:
“未济终焉心缥缈,
百事翻从缺陷好。
吟道夕阳山外山,
古今谁免余情绕。”
2023年3月2日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