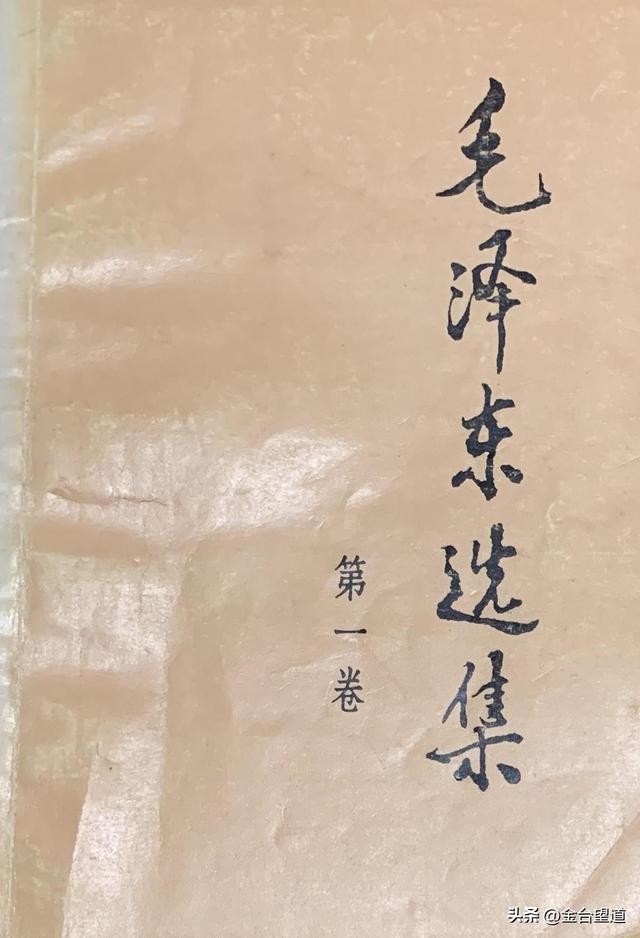就餐行为包含什么(为什么说外出就餐)
当我们走在路上,驱动我们前往餐馆的往往是饥饿感——我们渴望填饱肚子。而那些从餐馆飘出来的食物香味,以及张贴在街边墙上的食物广告,也在时刻准备着刺激即将靠近餐馆的我们。当然,有时饥饿也不是最重要的理由,比如为了社交、商谈或其他事项,餐馆也是一种去处。
因此,在《餐馆》(副标题为“一部横跨2000年的外出用餐文化史”)中,英国美食作家威廉·席特维尔找到了诸多例子,比如18世纪60年代,巴黎就有餐馆门上挂着广为流传的标语牌:“饥饿的人们,来我这儿觅食便能重拾精力。”客人的饥饿感始终是餐馆大规模产生的基础。
不过,这种饥饿感是如何产生的呢?这当然不是在寻找人为何会饿的身体结构,而是说,在人类历史上,饥饿的产生和解决大多都是在家庭里完成的,顶多外扩至家庭附近的田地、集市、作坊。如果去追问这段历史的转变,一个关键节点就是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只是通过大机器和流水线提高了效率,它还塑造了生活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家庭模式(不再是生产单元,而主要是消费单元)。许多劳动者也不得不早出晚归,在外解决温饱问题。这一前所未有的需求催生了餐馆,外出就餐就此开始盛行,影响至今。外卖的出现则进一步改变了这个模式。在例外状况出现时(如防疫期间居家隔离),家庭才会暂时重现部分生产功能(烹饪乃至种菜)。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餐馆》一书,有删节,标题为摘编者所起。
原文作者|[英]威廉·席特维尔
摘编|罗东

《餐馆》,[英]威廉·席特维尔 著,吴慈瑛 译,广东人民出版社·创美工厂,2022年3月。
藏在村庄里的传统旅店

19世纪偶然出现的美食评论家约翰·麦卡洛克,他本是一位长期出差的地质学家。
苏格兰佩思郡的泰斯河边坐落着卡伦德村,村庄以北不远处是卡兰德峭壁,地质学家约翰·麦卡洛克正是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他一边辛勤地收集、分析、记录与描述该地区的地质与矿物,一边爬到了距离地面1000英尺高的山路顶端。
在春天,研究地质就比较有难度了——在低云、薄雾与细雨的笼罩下,麦卡洛克走在欧洲蕨以及桦树与松树交织的林间,双眼难以辨别出真正的路径,只能谨慎前行。在某个缓坡上,他才发现自己正走在小溪间,而非通常的走道。他偶尔停下脚步,透过雾气观望山下的地貌,直至抵达山顶。此时,下方的视野里已无清晰可见的东西。
他在原路返回的途中折腾了数小时后,到达了卡伦德。他听说有两家旅店可以提供歇脚之处,这里便有其中一家。
这家旅店的老板名叫麦克拉迪夫人。麦卡洛克走进去后,这位女士让他先等着,并喊了一个女孩的名字:“佩吉——”她一次又一次地呼喊,对方才终于以同样敷衍的态度回答道:“马上就来——”
“作为这里的顾客,你必须要耐心。”麦卡洛克得出结论。这家旅馆确实时时刻刻考验着顾客的忍耐度。
“如果你现在周身湿透,那么直到你的衣服干了的时候,他们才会把火生起来,”他补充道,“如果泥炭不太湿的话。”麦卡洛克穿着湿透的衣服坐在燃尽了的煤堆旁等待晚餐时,想再翻起一些余烬,所以四处搜寻着拨火棍。搜寻无果后,他用雨伞取而代之。

19世纪初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苏格兰高地向旅客们展现了辽阔而阴郁的地貌、气势磅礴的山脉、永远恶劣的天气,以及令人提不起兴趣的食物。(图片来自《餐馆》)
这时佩吉过来了,用裙摆扇起了火苗,房间里瞬间充满着浓烟。麦卡洛克被呛得咳嗽,佩吉便将他带到一张桌子旁。他望眼欲穿地等待,直至女孩把食物送上来。“她先是端上了被称为羊排的羊肉与芥末,”他写道,“许久之后,才送来刀叉,然后才是盘子、一根蜡烛与食盐。”他向店家要了些胡椒,但“直至羊肉变冷后”他们才送上,外加些许面包与一杯威士忌。麦卡洛克还写道,店里所有物件杂乱地摆放在桌上是有特定作用的:“它们掩盖了麦克拉迪夫人的桌布的瑕疵。”
晚餐后,麦卡洛克又等待了许久,店家才准备好客房——里面也同样湿气弥漫,厚厚的毯子“徒有重量却不保暖”。半夜他被冻醒,才发现所有的被褥都已经滑到了地上。他试图将被褥拉回身上,但在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中,“手脚并用踢扯了一番”反而使所有东西都“乱七八糟地纠缠成一团,无论是床单还是其他物件”。
他在清晨5点起床,打算洗个手却找不到肥皂。镜子因为过于老旧而成像扭曲,他只能狼狈地刮起胡子,还不小心划伤了脸。唯一能找到的一块毛巾又湿又脏,所以他选择用窗帘把脸擦干。

《西部往事》(C'era una volta il West1968)剧照。
然后在等待早餐时,他不耐烦地走进了厨房,想找个水壶来烧点东西——最终他告诫读者们,进入厨房“并不会加快上菜速度”,因为他在烟气之中看到一只笨重的大水壶“并未放在火炉上,天知道何年何月才能把水烧开”。
他环视厨房,又看到了一些已经被火烧成灰烬的燕麦饼,并从这片狼藉中辨认出了一条鲱鱼、地上成堆的床单、几只死鸡、几块猪肉,以及一只打瞌睡的猫,一个装满土豆的罐子旁边放着一支风笛与一桶水。然后,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凹处”,他发现“两三个没穿衣服的孩子”正窥视着他。
于是他又得出结论:早餐“可能会在两个小时内准备好”。他认为读者可能“对这样的早餐不感兴趣”,所以匆匆地离开了。
古老的多样性
然而,麦卡洛克在朝着斯托诺维与斯凯岛向北进发的途中,体验到了比麦克拉迪夫人的旅馆更恶劣的留宿环境——那是一片人烟稀少的苏格兰地区,方圆100英里内“人人都对邻里情况了若指掌,无论是牛犊或是小孩的出生、自家的生意,还是妻子的下午茶”。
在偏远的苏格兰大陆最北端,即愤怒角以北44英里处,是位于北大西洋的罗纳岛。那里的所有事物古老而陈旧。
于17世纪末在欧洲爆发的鼠疫造成了大量人类的死亡,当地的人口就是充分的证明。五个家庭居住在地下洞穴中——这意味着再剧烈的海风也刮不走他们的屋墙,而屋顶则由泥炭和稻草混合搭成。
麦卡洛克发现这里的每个家庭均有六个孩子。无论父母是谁,“孩子均在家庭之间平均分配,”他写道,“如果孩子人数超过30,他们便会把多余的孩子送往附近的刘易斯岛。”
罗纳岛的岛民会种植大麦、燕麦与土豆,吃的食物包括燕麦粥、土豆、牛奶(产自哺乳期就被带到岛上的一头奶牛)与咸鱼干——用从礁岩上捡来的鱼制成。他们从未吃过新鲜的鱼肉。

《勇敢的心》(Braveheart1995)剧照。
麦卡洛克受到了氏族首领肯尼斯·麦凯吉(一位生性幽默的伙计)的用餐邀请,这位首领的大多数家庭成员都“很胖”(至少男人与小孩如此)。麦卡洛克说,他们吃得非常好,或者说,以一种类似古人的方式生活,算是过得很富足。尽管他们很多人都没有衣服穿,但食物可谓应有尽有,因此他们对自己的生活感到舒适而满足。
不过女性除外。麦卡洛克写道,他的“妻子与母亲看起来悲惨且忧郁,高地的其他妇女也通常如此”。
开朗的肯尼斯·麦凯吉将作为访客的他引进洞口——眼前是“一条悠长曲折的通道,有点像矿井的地道,但没有门,前方则通向洞穴的最深处”。在其中,他能分辨出用作床榻的区域,上面覆盖的并非稻草,而是积灰。中间坐着一位“年迈的婆婆”,她正在静静燃烧的泥炭旁照料一名婴儿。
这一幕场景有些悲凉。他感慨而委婉地评述道:“人类生活的多样性值得研究。”洞外是“永冬一般的气候”与从不停歇的“暴风雨”,地底下“一个烟味呛人的隐蔽洞穴”里,住着“一名八九十岁的失聪老妇人;妻子与孩子都衣不蔽体;这样的隐居生活漫溢着无形的孤独,仿佛一所无法逃脱的监狱”。
作为访客的麦卡洛克得到了质感粗糙且黏稠的大麦饼,跟他先前在圣基尔达吃到过的一样“又难嚼又难吃”——他曾描述道。他看着面前倒胃口的大麦饼,听着洞外呼啸的海风,咕哝道:“这烦人的风越刮越大,仿佛海潮都能被它刮退。”后来他写道:“一不留神可能会在这里耽搁了整个冬天的时间,是该考虑离开了。”于是他找借口拒绝了当地的“美味佳肴”,摆脱了这场困境。
家庭模式被工业革命改变后,
餐馆兴起了

19世纪末的伦敦。
一段时间后,麦卡洛克到达了伦敦的时尚地带——波特曼广场。他身处一间高雅的会客厅里,“周围排着二十来位女士,她们身上白色的薄纱、羽毛以及所有配饰,都像温室内的花朵一样摇曳生姿。”
他看着这番景象,又回想起那些昏暗且肮脏的地下穴居,心中不由产生了强烈的对比,于是写道:“你大概只能想象这种感官彻底混乱的情境……从漆黑的煤坑走到阳光下的瞬间,都无法比拟这般让人眩晕的视觉冲击力。”
几年后的19世纪30年代,罗纳岛的部族再次消散。也许是麦凯吉的祖母去世了,而他自己也受够了那样的生活。此后,那里便成了无人居住的荒岛。也许麦凯吉移居到了附近的刘易斯岛,然后地主为了让他去放羊和种庄稼,每年要为他花费相当于2英镑的成本提供衣着。又或许,他听说全国各城镇爆发了工业革命,因此像很多人一样跃跃欲试,想要寻求新的机遇,追求新的梦想。

《简爱》(Jane Eyre1996)剧照。
这一时期是西方文化史上的重大转折点。例如,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纺织品生产从住宅转移到了工厂,从而创造了一批就业机会,而工人们也就不得不离开原来居住的村镇。他们不再局限于当地的农耕生活,同时,也不可能长途跋涉回家吃午饭了。
从历史观点来看,他们的生活原本与农业(耕种、收割与播种的不断循环)息息相关,生存则受天气与雇主的支配。温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这也是罗纳岛岛民腌存鱼肉的原因:他们永远无法确定明天是否还能捡到鱼。
但工业革命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英国历史学家艾玛·格里芬写道,自20万年前智人作为一个亚物种出现以来,在工业时代前,人类社会的任何群体都无法“绝对、永久地保护每个成员免受饥荒的威胁。英国工业革命开辟了一条与人们以往经验的既定参照大相径庭的道路”。这种转变强烈地反映在人们的在外就餐与外出就餐的体验中——时至1840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已有大约15500名大饭店与小食坊经营者、将近38000名酒馆老板与5500名啤酒馆经营者。
确实,19世纪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家的功能。简而言之,在工业化以前的时代,家是家庭主要成员与亲戚的居所,人们通常只会在附近活动。并且在传统的乡村环境里,工作机会通常都是在村庄或附近。经济史学家乔尔·莫克将当时的家形容为“基本生产单位”。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当今完全不同,人们不只是烹饪食物,还需要种植与收割。虽然人们很少直接购买食物,但有可能用它们来交换其他物品。人们在家中以盐卤、腌制与晒干等方式保存食物;村庄里,村民在能同时容纳面包烤箱与酿造室的大房子里酿制啤酒。
但工业革命导致了这种家庭经济模式的消亡,将传统住宅中的生产活动迁至了他处。人们离家工作的同时,在其他地方展开了各类社交活动,包括饮酒等消遣项目。根据莫克的叙述:“英国的家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最显著的是,它们从生产单位变成了主要消费实体。”
破土而出的酒馆
人们在家外开展的另一项活动是教育,北安普敦郡南部相连的韦斯顿村与洛伊斯·韦登村则是很好的例子。原先,父母可以自愿带孩子到教区长的管区或家中上课,或者在夏季带孩子到圣玛丽与圣彼得教堂,坐在门廊的长椅上上课。不过在1848年,尊敬的塞缪尔·史密斯牧师与当地乡绅亨利·赫利·哈钦森上校创立了圣洛伊斯学校,接受所有的孩子入学,无论贫富贵贱。这一项变革举措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文化程度,当然,也提高了人们对生活的期望。

《雨果》(Hugo2011)剧照。
生产效率的提高缩短了原本漫长的工作时间,国家进而强制施行了公共假期制度。余暇不再是劳动者迫切需要的休息时间,而是一项独立的活动;同时,从中世纪到现代,休闲活动也发生了变化。这其中有新兴道德主义团体的功劳,他们包括福音派、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卫理公会派教徒,以及禁酒运动人士。他们开展的活动促成了饮酒时间的限制与某些娱乐项目的终结,这些项目包括公开处决(最终废除于1868年)与狩猎游戏。他们鼓励礼拜、运动与阅读。但很显然,不是每个人都认为一本好书比一次血淋淋的公开绞刑更有意思,但这些团体对社会的改变还是显著的,尤其是在伦敦这样的城市。
新闻出版业迅猛发展的同时,成千上万的工作缺口也随之出现。同期壮大的行业还包括19世纪的概念:酒店、音乐厅以及非常关键的场所——餐厅。然而,经济史学家迈克尔·鲍尔表示:“耗费人们最多时间的活动不是工作,也不是宗教仪式,而是饮酒。”在他们看来,饮酒虽然没有观看绞刑来得刺激,但也比阅读有趣多了。
尽管在18世纪后期,酗酒与暴行的情况已得到改善,但到了19世纪,杜松子酒仍然是热门饮品,同时,啤酒也加入了备选行列。在19世纪初期的英格兰与威尔士,每人每年平均喝下34加仑啤酒。工人阶级把三分之一的收入花在了啤酒上——他们认为喝酒比喝水更安全,而且酒吧比家里更温暖、更舒服。
在19世纪初期,市区酒馆的作用变得包罗万象——有些被用作工会与社团的聚会场所,有些被用作歌舞厅,还有少数被用作马车旅行售票处和马厩,例如柏罗商业街与皮卡迪利大街的酒吧。
首都马车站附近的酒店数量也在成倍增加,并且还存在大量民宿。当代地图显示伦敦西区的牛津街与考文特花园附近有许多酒店;关于他们提供的食物质量,约翰·费尔特姆在其1818年发表的书作《伦敦一览》(其中生动描述了首都的娱乐场所、邮局、教堂、监狱、美术馆与医院等)中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也许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这座都市能给予劳动者与中产阶级如此多必要与次等琐碎的生活享受。

19世纪英国禁酒运动力图终结公开处决,并鼓励人们进行礼拜与阅读。然而,饮酒仍旧是最受欢迎的业余节目。(图片来自《餐馆》)
他们经常食用的肉类是牛肉、羊肉与猪肉。费尔特姆指出:“除了在富人的餐桌上,家禽肉类很少出现;农业状况导致了家禽供不应求而价格过高。”
英国首都伦敦与巴黎一样受益于法国大革命——许多法国大厨来到了伦敦餐厅的厨房。与巴黎的同行一样,在贵族家庭数量骤减之前,他们大多数人还是其中的私厨。英国富人在品尝过法国贵族的美食后便成了这些餐厅的常客。来自法国庄园的一名原管家、原主厨为英国人带来了品质诱人且新奇的法国美食。
亚历山大·格里隆逃离法国后,在英国的一个家庭找到了工作,并于1802年在伦敦梅菲尔区的阿尔伯玛勒街开设了“格里隆酒店”。流亡的国王路易十八于1814年返回法国前曾以这家酒店作为在伦敦的据点;鉴于经营者的来历,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数十年过去后,它仍在经营,并且《布莱克指南》在“适合贵族与外宾的一流家庭酒店”部分也介绍了这家酒店。
工厂里的速食与效率
工业革命席卷而来的同时,富人一直吃得很讲究。但也许费尔特姆对伦敦的看法过于乐观了,因为社会的进步还未普及。哪怕是那些并非来自偏远落后的罗纳岛的居民,也应能看到整个社会的涓滴效应并未生效的状态。经济史学家查尔斯·费恩斯坦在其论文《悲观主义永存》中不太乐观地推测道:
历史角度的现实是,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在真正开始从自己努力创造的经济转型中受益前,忍受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辛劳,从而使自己的地位获得一点提升,又或是毫无改变。
在1770—1830年期间的几十年中,学者们确实就英国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进行了大量探讨。某些记录表明,许多工人阶级的薪资都有所提高,甚至翻了一倍;他们的平均身高也有所上升,这就表明饮食得到了改善,每餐有了更多的蛋白质;婴儿死亡率也降低了。但是,他们的身份从农民工变为时髦的城市人后,生活质量真的就提高了吗?
小麦脱粒机的发明等技术创新导致了农场工人过剩,这些工人很快就到城市与工厂中就业,当然,还有后来的铁路。先进的城市生活与有序的人力分配提高了社会对教育的认可——人们的认知逐渐提升,并意识到受过教育的人能成为更优秀的劳动者。
《城市之光》(City Lights1931)剧照。
不过,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英国各地的生活水平有所不同——19世纪初的天气异常导致了几次农作物收成不佳,战争与国际贸易的中断又引起了通货膨胀与信贷紧缩。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战争爆发的频率几乎高达和平时期的两倍。
城市里许多所谓的“新”居只不过是贫民窟。也许工人阶级的薪水是上涨了,但家庭成员也增加了;受抚养者越多,实际上意味着更少的人均社会资源。所有这些繁重的工作也理所当然会使工人们更加饥饿!一位农妇曾对维多利亚时期初的作家亨利·菲尔普斯表达过自己的观点:“田间的工作使人们吃得更多。”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其1845年的书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也做了相关记录。他走访了城镇的家家户户后,记叙道:“各处工人住所的规划与建造都很拙劣,并且是处于最坏的状况——通风不良、潮湿且不卫生。”恩格斯还提到“许多人衣衫褴褛”;关于工人们的饮食,他说:“劳动者所吃的食物本身就难以消化,完全不适合儿童。”他还写道,酒醉的父母会给孩子喝酒,甚至吸食鸦片。一天下来,“辛劳的男人从工作中解脱,筋疲力尽地回到家,看到难受、潮湿、肮脏而糟心的环境……喝酒便算是他们唯一的乐趣了,所有事情都让他们渴望麻醉自己。”
似乎每项研究都提及了工业革命时期大多数新工厂中工人生活的艰难之处。关于女工们的饮食,恩格斯发现“雇主为了节省她们吞咽的时间,提供给她们的食物都会事先切好”。
根据1833年的国会文件记录,这些服装厂——
内部有独立的房间,可供工人进行洗涤、清洁与就餐……晚上作为儿童讲堂的房间,偶尔在白天会用作她们的更衣室与食堂。但仍有许多工厂并没有清洗、更衣与做饭的场地。
制衣厂的年轻女工。“为了节省她们吞咽的时间,提供给她们的食物都会事先切好。”(图片来自《餐馆》)
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于1771年在德比郡的克罗姆福德建造了一座水力棉花纺织厂,雇佣了大量童工,还有女工和一些男工。(工业革命初期,男工经常不守纪律且酗酒成性,已不再是国内生产的主要劳动力;雇主通常认为女工与童工更好使唤,手脚更灵活,脾气更温顺。)在19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阿克赖特的儿子——小理查德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并赚到了更多的钱。他记录了这家纺织厂工人的饮食起居。
一天工作12个小时,夏季早晨7点开工,冬季早晨8点开工。厂里的机器只有晚餐时间才会停止运转。“他们的早餐很不规律”,阿克赖特写道。钟声会在八点半敲响,除了正在操控机器的工人外,其他人可以得到半个小时的用餐时间。他还说:
厂里有一间名为“食堂”的房间,其中放着各种各样的电炉与火炉,与绅士们的厨房很像;在厂里工作的母亲或妹妹(通常整个家庭就业于同一家工厂)会把早餐拿进这间房。钟声一响,会有一群男孩过来把早餐取走并拿去其他房间。
《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剧照。
厂里施行了先到先得的制度。阿克赖特说,许多工人无暇离开自己的岗位,“可能只有不足五分之一的工人有机会得到足够的食物”。他们是如何空腹工作的呢?我们仍无从得知。但鉴于阿克赖特的成功运作,也许这些工人以某种最基本的标准填饱了肚子。
应时而生的城市旅馆
工业革命时期,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为了打工而远离居所,企业看到了新的商机。实际上在18世纪中叶,英国已发展出了纵横交错的长途马车线路。1667年已出现第一批马车驿站的广告——来往伦敦与巴斯之间的“飞行线”。这两个城市的两家旅馆墙上均张贴了如下广告:
若您希望来往伦敦与巴斯或途中的任何地方,请到伦敦卢德盖特山的“敲钟野人旅馆”(Bell Savage)或巴斯的“白狮旅馆”(White Lion)。每个礼拜一、礼拜三与礼拜五可能会有一辆公共马车到达这两处;马车于早晨5点启程,整趟行程大约需要三天时间。
这样的旅途存在较多风险——临时路线上布满了树枝与坑洞,同样危险的还包括跟踪马车的拦路劫匪(男女都有)。1784年邮政马车启用后,为了提供旅途的便利,旅馆便沿路开设起来,既能提供换马与休息之处,又能为疲倦的旅者提供食物与酒水。时至18世纪中叶,每7—10英里路就会有一家旅馆。当时最热门的路线是由伦敦至达勒姆郡的大北路,即当今的A1公路。
最繁忙的旅馆是林肯郡斯坦福德镇的“乔治”(The George)旅馆。从那里启程的旅客在拿到车票后,可在两个候车室的其中一间等候对应方向的马车:一间写着“伦敦”,另一间写着“约克”。
《骗中骗》(The Sting1973)剧照。
这样的旅馆当然只会提供简单的食物,并无其他选项。旅馆的数量增长在苏格兰也尤为迅猛,特别是在1790—1840年的高地与群岛地区——许多人在阅读了同时代英国作家詹姆斯·鲍斯韦尔的小说或苏格兰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的诗作后,前往当地一睹苏格兰大自然的野性之美。同时代英国诗人威廉·华兹华斯的妹妹多萝西与这两位文人一样,为这片风景中无边无际的海洋、辽阔而阴沉的天空,以及巨大宏伟的山脉增添了浪漫主义色彩;她穿越高地,写下了怪诞的薄雾、下着暴风雨的海角、孤零零的小房屋、诡异的废墟,以及延伸至无限黑暗的土地。游客们想追随这些文豪的脚步,又或是想尽可能远离战火纷飞的内陆,而新开的旅馆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根据加拿大学者特蕾莎·麦凯的叙述,大部分这些旅馆的经营者是女性。麦凯发现了大约60位女性旅馆经营者的相关证据,她们中许多人为单身或丧偶,其中一位就是麦克拉迪夫人。在她那家乱七八糟的旅馆里,约翰·麦卡洛克度过了凄凉的一夜。
关于麦卡洛克对沿途各种生活与风景的独到见解,他是如何加以利用的呢?——他写下了一页又一页绘声绘色的散文信件寄给了朋友沃尔特爵士。这位地质学家已目睹并经历了新机器时代似乎长期存在的贫困与严重不平等现象,但他并未因愤慨而对社会的进步嗤之以鼻。
原文作者|[英]威廉·席特维尔
摘编|罗东
编辑|罗东、张婷
导语部分校对|李铭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