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飞软体风筝的地锚(放飞千种昆虫的)
作者 | 李晨阳

2014年1KITE项目成果登上《科学》封面
2010年,周欣从加拿大回到祖国,联合多位国际知名学者,共同放飞了一架“风筝”。
9年过去了,周欣的身份已从深圳国家基因库执行主任变为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而这架“风筝”仍在继续翱翔,载着1456种昆虫、3000万个基因、4.5 TB数据和100多位科学家的心血与期望。
这架“风筝”的英文缩写是“1KITE”,全称为“1000 Insect Transcriptome Evolution”(“千种昆虫转录组演化”研究项目)。
项目联盟汇集了来自10个国家近20家单位的百余名科研人员,专业背景涉及昆虫学、基因组学、分子生物学、形态学、古生物学、分类学、胚胎学以及生物信息学等方向。
这么庞大的科研项目,究竟在做什么呢?
问一个宏大的问题
周欣说:“我们想要回答的,是一个非常基础,也非常宏大的命题:昆虫是从哪里来的?现生昆虫类群之间的演化关系是怎么样的?”
“脱离了演化的框架,生物学中的一切发现都将失去意义。”著名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的这句话,数十年间被演化生物学领域的学者反复引用。
如果把“演化的框架”具象化,那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生命之树”,每个叶片代表一种或一类生物,分支的形状和相对位置,简明地重现它们的演化历程和亲缘关系。
演化树为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地图和骨干。
“果蝇你知道吧?一类重要的模式生物。”周欣向《中国科学报》解释,“基于果蝇的研究已经斩获了6项诺贝尔奖,但是这些成果究竟有多大的普适性,对人类来说又有多少借鉴意义呢?除非你把果蝇放在演化树准确的位置上,否则你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只有在演化的大框架下,人们才能知道,一种生物所具备的表型特征、基因功能、信号通路等,哪些是少数物种特有的,哪些在演化史上是保守的。
科学家们进而才能判断,特定科学问题应该选择哪种生物作为研究对象。
正如本项目发起人之一、德国柯尼希博物馆的教授Bernhard Misof所说:“我们只有在构建了可靠的昆虫系统发育关系之后,才可能开始了解昆虫的物种多样性及其在生态方面的重要性。”
“每一个类群及其具体的科学问题,都是生命之树上的一块血肉。像1KITE这样的科学项目,为昆虫研究者的工作提供了一副骨架,让具体的科学问题在上面各安其位,而不是散落一地。这对系统的研究工作非常重要。”未参与该项目的中科院动物所研究员朱朝东对《中国科学报》说。
为什么需要100多位科学家?
“这个项目开始时,没有人知道我们最终能否成功。”周欣说。
因为描绘演化的框架,的确是一项繁复浩大的工程,尤其你面对的是昆虫——世界上最大的生物类群。
全世界已知的昆虫近100万种,约占所有已知物种的2/3。
在4亿到5亿年的漫长时光中,昆虫经历过数次大灭绝的沉寂,以及沉寂过后突如其来的物种大爆发。这些都让它们的演化历程更加复杂、更加扑朔迷离。
一方面,由于特殊的身体结构等因素,演化早期的昆虫要形成化石并保留下来,比脊椎动物更加困难,在化石上留存的信息也存在局限性。
对那些已经灭绝的昆虫物种来说,可用于构建演化关系的形态特征比现生种类少了许多。
另一方面,解析古老的快速演化事件需要海量的基因数据,从1000多个昆虫物种中产生的3000万个基因,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昆虫基因数据集。
究竟怎么处理这些数据,对研究者的硬技术和软实力都提出了挑战。
“在项目的准备阶段,我们就已经认识到,当时开发的软件不足以用来分析这样的海量数据。”德国海德堡理论研究所教授Alexandros Stamatakis说。
这些数据输入到现成的软件中,电脑会直接崩溃,因此需要针对昆虫大数据研发新的算法和软件。
经过理性评估,科学家们决定将最初定位的昆虫基因组研究改为昆虫转录组研究。
与基因组测序以DNA为实验材料不同,转录组测序的研究对象是编码区DNA所能转录出来的RNA。这样就能获得含有昆虫遗传信息的编码基因序列,用于构建昆虫演化树,同时也大大减少了测序和后期分析的工作量。
即便如此,当时做一个转录组测序就要花费两三万元,这样一个投资巨大的项目,在不少国内外同行眼里,无异于天方夜谭。
研究者要面对的挑战不止于此。
由于RNA远比DNA脆弱,在一般储存条件下会很快降解,因此他们不能依靠各个研究机构库存的标本,必须到全球各地去采集最新鲜的样本。
“这项工作相当不容易。”朱朝东说,“因为一些在进化历程上占据关键位置的重要物种,要么数量很稀少,要么分布区域或生境很特殊。一般研究者很难找到,只能依靠长期开展这些类群分类学研究的专家才能获得珍贵的标本和样品。”
为此,周欣面向全世界征集合作者,寻找那些对特定昆虫类群最熟悉的研究人员。
一个又一个专家陆续加入1KITE项目联盟,有的下潜入墨西哥湾,在淡水与海水过渡的水域搜寻现生昆虫的最近外群——桨足类甲壳动物;有的到南非人迹罕至的山头寻找螳虫修目的奇特昆虫;有的则历经千辛万苦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采集到了无数学者梦寐以求的蛩蠊……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100多个科学家的原因。”周欣笑道。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白明在俄罗斯西伯利亚无人区采集到西蛩蠊属标本,为1KITE项目提供了关键类群的数据支持。白明供图
揭开4亿年的秘密
2014年11月,1KITE项目第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登上了《科学》杂志的封面,宣布构建了迄今支持度最高的昆虫高级阶元演化树,解决了一系列昆虫演化研究中的难题,同时也为昆虫学的各分支学科提供了系统关系的基本框架。目前这篇文章已被引用上千次。
从项目启动到论文发表,经过了一个漫长而坎坷的过程,光是分析收集到的数据,就花去了两年时间。
这一成果基于144个代表性昆虫物种的转录组数据,在重新构建昆虫系统发育关系的同时,还估算了昆虫不同类群的起源时间。
而他们根据RNA转录组的测序结果来构建分子树,也开辟了一种新的方法学。
数据显示,昆虫与最早的陆生植物在约4亿8千万年前同时起源,共同塑造了最早的陆生生态系统。
大约4亿年前,昆虫扇动翅膀,成了第一批会飞的地球生物,远远早于其他动物。此后昆虫独霸天空近2亿年之久。
有趣的是,昆虫之翅的出现,也与陆地上高大植物同时。
树木提供了大量有待开发的生态位,最早掌握飞翔技能的昆虫能够占有新空间,抵达新宿主,利用新食物,也能更有效率地自我保护和向外扩散,自然成了超级赢家。
“在所有现生昆虫中,有翅类超过99%。”周欣说,“可以说,翅是昆虫的演化创新,也是这个类群如此成功、如此繁盛的关键因素之一。”
那么昆虫究竟是如何起飞的,它们的翅又从何而来?这自然成了1KITE项目热切探索的命题之一。
在2019年初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论文中,他们梳理了多新翅类昆虫的演化历程,指出有翅类昆虫的祖先最早为陆生,而非来自淡水生境,翅来源于背板和侧板的特化结构。
除飞行外,昆虫与植物的演化还有过多次“神同步”:昆虫的海洋性祖先开始登陆的时候,陆地植物生态系统刚刚形成;全变态昆虫与种子植物几乎是同步出场;当被子植物开出真正意义上的花朵时,传粉蜂也闪亮登台了……
昆虫与植物之间数亿年的“相爱相杀”还表现在昆虫口器的演化上。
乍看起来,吃植物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但植物坚固的物理屏障和难以消化的化学成分,都给植食者们设下了重重阻碍。
1KITE项目2018年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另一项研究表明,4亿年前,昆虫发展出了像针一样锋利、像吸管一样便利的刺吸式口器,蚜虫、飞虱、蝽等我们今天熟知的农业害虫都得益于这项利器。
而消化植物所必需的果胶酶,最初主要存在于植物、细菌和真菌中,直到大约1亿年前,竹节虫的祖先通过水平基因转移机制,获得了可能来自肠道菌群的相关基因,使这些昆虫从此有了独立合成果胶酶的能力。
越来越多证据表明,昆虫中的许多类群都平行出现过水平基因转移,从微生物那里借来了对付植物的武器。
其中,多样性最高的昆虫类群——甲虫,也多次从真菌获得果胶酶。1KITE项目展示的这部“舌尖上的昆虫演化史”,同样异彩纷呈。
“有了如今的数据积累和数据分析方法的创新,许多以前悬而未决的问题现在得到了解答,而许多以前基于小数据量的所谓‘新发现’现在也得到了纠正。” 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Karl Kjer说。
迄今为止,1KITE项目已在多家知名期刊上发布了一系列颇受关注的成果,其中包括膜翅目、半翅目、蜚蠊目等昆虫子类群的系统发育研究。
项目所产生的转录组和基因集数据通过1KITE开放平台与全球科研人员共享。
“这些成果对世界上主要昆虫类群的研究,确实很有借鉴意义。” 朱朝东说。
明年,项目下的多数课题都将结题,这架一飞10年的“风筝”也即将收官。
“回头想想,能参与这样一个项目非常幸运。”周欣说,“未来,我们将在昆虫生命之树的框架下,理解昆虫重要性状的演化模式。在此基础上,全球科学家将共同推动关于昆虫的生态功能、危害机制、生物机理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助力农业、医学等应用与发展。”
相关论文信息:
DOI:10.1073/pnas.1817794116
DOI:10.1073/pnas.1815820115
DOI:10.1126/science.1257570
《中国科学报》 (2019-05-28 第7版 生态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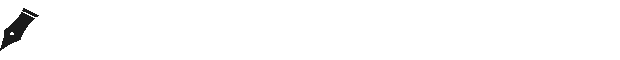

请按下方二维码3秒识别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