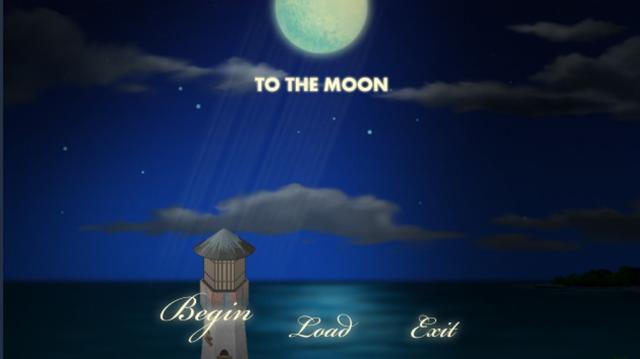喀喇昆仑精神主题馆(喀喇昆仑光影记忆)
拍摄喀喇昆仑冰川和乔戈里峰是我多年的愿望,从2008 年到2012 年,我四次进出喀喇昆仑腹地进行专题采访,苍茫雄伟的山脉,叠印着高原驼帮的身影,是我久久不能忘怀的记忆,时至今日,那叮当的驼铃还会不时在心中响起。

危机四伏的冰川王国
喀喇昆仑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山系之一,平均海拔6000 米以上,拥有8000 米以上的高峰4 座、7500 米以上的高峰15 座,主峰乔戈里峰(K2)海拔8611 米,是地球上垂直高差最大的山峰,也是世界上最难攀登的山峰。
喀喇昆仑山冰川资源丰富,被称为“冰川王国”,其中在中国境内的冰川共1759 条,最著名的有迦雪布鲁姆、乌尔多克、斯坦格尔、特拉木坎力、克亚吉尔。这些冰川深藏在喀喇昆仑的奇峰千壑中,末端汇聚着大大小小的堰塞湖,冰溶洞、冰钟乳、冰锥体、冰饰蘑菇形成冰川喀斯特景观,仿佛瑰丽诱人的“冰宫”
“天河”之路捂着胸口按快门

从距离乔戈里峰最近的苦鲁勒村启程,经过3 天的艰难行走,我们的驼队翻越海拔4820米的阿格勒达坂,进入棵勒青河。喀喇昆仑山脉中的迦雪布鲁姆、斯坦格尔、特拉木坎力冰川都发育在棵勒青河上游,拍摄乔戈里峰则要沿棵勒青河走向下游,绕进乔戈里峰登山大本营——音红滩。
棵勒青河是叶尔羌河上游的一条支流,位于喀喇昆仑山脉深处,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天河”,平均海拔4500 米,河谷两侧突兀的山峰直插云霄。
我们逆水而上,3天后,到达棵勒青河上游的第一座冰川——迦雪布鲁姆。它发源于两座海拔8000 米以上的山峰——布鲁德峰和迦雪布鲁姆Ⅱ峰,冰塔林犹如一座座金字塔。
我在驮工师傅阿尤甫的协助下,背着摄影器材,徒步沿着冰川侧碛向前沿靠近。阿尤甫就像一只昆仑羱羊,在海拔4600 米的山体上能快速奔走。翻过一米多高的冰墙,我在相对开阔的冰碛砾石堆上支起三脚架和骑士612 相机,面对碧绿如莹的冰塔,心情格外愉悦。
迦雪布鲁姆冰川末端跃动的冰舌,在终碛垄上方形成了千姿百态的冰川喀斯特景观,横卧在高耸坝体上的冰塔夹杂着黑色的砾岩,冰体表面接受阳光的辐射后,形成黑蓝两色相融的怪异形态,就像猛兽嘶鸣的大嘴,叫人惊叹。
2010 年9 月下旬,我第二次来到迦雪布鲁姆冰川脚下,一连几天都是连绵的风雪,准备离开的那个早晨,雪停云散,缭绕的云雾就像无数条柔软的绸带游弋在布鲁德峰山腰。我扛着禄莱6008AF 相机,沿着帐篷左侧的小山包快速攀向制高点。坡上雪多地滑,还未支好相机,就感觉胸口疼痛,心跳加速,呼吸特别费力,我忘了,在高海拔环境中不能过快运动,只好一边捂住胸口,一边按动着快门……
斯坦格尔冰川 冰之乐章

第二次深入喀喇昆仑腹地,我计划拍摄棵勒青河上游的斯坦格尔冰川,它的源头高处是海拔7172米的罗斯峰。我们在距斯坦格尔冰川一天路程的大石头处宿营,这块石头足有200吨,是棵勒青河里最大的一块冰川漂砾。大雪下了整整一夜,第二天一早,天气转晴,太阳在阴云里游动,时隐时现。突然,西面的山体上发出“轰隆、轰隆”震耳欲聋的响声,棵勒青河对岸陡峭的山岩上,大片雪雾飞流直下,“雪崩!”我快速掏出相机进入战备状态,之后又有7次雪崩相继滑下。
在刨蚀地貌上攀行两个小时,我们终于驻足在斯坦格尔冰川前沿,这里发育着多处冰溜景观,尤其是冰塔林中间,一排排冰溜如同琴键,且晶莹剔透,停在冰尖上的水珠在逆光之下像一颗颗无瑕的宝石闪耀着光芒,无数根冰溜融化的水滴掉在冰面上,“滴答、滴答”的响声奏出一首无序的乐章。每排冰溜后面都有一个洞穴,我钻进洞里,蜷伏着身体,如同“垂帘听政”一般,从内向外拍摄着这一奇观。
特拉木坎力冰川如愿以偿
我们继续向棵勒青河上游走,寻找让我心驰神往的特拉木坎力冰川。这座冰川发源于海拔7468米的特拉木坎力峰,直逼棵勒青河谷地,末端前沿形成了一个较大的堰塞湖。
清晨,阳光眩目,逼着眼睛直流泪水。随着海拔高度不断增加,感觉空气中的含氧量少了许多,呼吸节奏明显加快,被紫外线灼伤的黑色脸膛又多了几条刺痛难忍的裂纹,嘴唇肿得黑紫黑紫的。阿尤甫突然指着前方右侧的一排冰塔说:“特拉木坎力。”果然,冰塔前面有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的堰塞湖,一字排开的冰塔浸泡在湖里,这是特拉木坎力冰川最鲜明的特点,接下来,用GPS测定方位数据,与收集的数据完全相同。我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扯开嗓子高喊:“特拉木坎力,我来了!”
特拉木坎力不愧是中国最美丽的冰川之一,鳞次栉比的冰塔翠蓝似玉,冰体断面犹如刀削,直插波光倒影的湖中,毗邻的山体气势恢弘,崩塌的冰块掉入湖中,泛起层层涟漪,推动浮在湖面上的冰块四处游弋。当绚丽的夕阳洒在冰川背依的山体上,与脚下的冰塔一同辉映在湖中,纷呈出“湖光山色”的瑰丽景观,我用不同画幅的相机记录下了这奇异的场景。
2012年6月中旬,我第四次进入喀喇昆仑深处,计划徒步翻越特拉木坎力冰川,拍摄上游的克亚吉尔特索湖和浸泡在湖中的克亚吉尔冰川。清晨,我在湖岸滩涂选择了一块相对平整的弹丸之地支起相机,在寒风瑟瑟中等待拍摄时机。堰塞湖的湖面已被冰层覆盖,太阳渐渐爬上山巅,忽听“轰隆”一声巨响,冰川末端一块巨大的冰体崩塌落入湖中,犹如一个能量巨大的炸弹,掀起十几米高的水柱,湖面的冰层受到挤压,冰块相互簇拥着涌向岸边的滩涂,如同“海啸”一般。我抓起三脚架和相机向高处攀爬,放在湖边的摄影包被涌来的湖水冲走,像一只小船左摇右晃向湖中荡去,我跳进齐腰的水中,抓住摄影包连滚带爬回到岸边。户外鞋里灌满冰水,冰冷刺骨的雪水顺着裤腿往下流,冻得我直打寒噤,右手背上留下几条擦伤,鲜血直流。
清晨,阳光明媚,昨天被“海啸”推上岸的冰块在滩涂上,慢慢融化。忽然飞来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我两手一张,小鸟跳到我的手心,嘴巴尖长,是土黄色的,这还是我头一回在海拔4540米的喀喇昆仑看到飞禽。
为乔戈里峰拍摄标准照

四次深入喀喇昆仑拍摄,最艰难的莫过于拍摄乔戈里峰。
驼队沿棵勒青河而下,下游的河床平整宽阔,水量明显增大,纵横交错的河流形成多处“九曲十八弯”的牛轭河曲现象,驼队只能在河床边绕来绕去,过河的次数至少超过50回。两天后,我们在乔戈里峰的登山大本营——音红滩扎营。大本营坐落在穆斯塔格河河谷左侧2公里长、50米宽的红柳滩中,海拔3900米,许多石壁上镌刻着中外文字。可惜从这里是看不到乔戈里峰的。
清晨6点出发前往前沿拍摄位置,最少要走6个小时,行走路线平均海拔4800米,到处是破碎的乱石,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我扛着三脚架,随阿尤甫、阿米尔下到谷底,再攀爬倾角足有60°、长度约两公里的坡地,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脊,渴了,抓一把石头底下的残雪塞到嘴里。8小时后,终于来到乔戈里峰前沿地带
乔戈里峰在蓝天的衬映下巍然屹立,山巅旗云飘动,庄严肃穆,我情不自禁地流下热泪。16时48分,我用颤抖的右手按动快门,快门声清脆、沉重,为了这一刻,我足足等了20年。
拍摄点笼罩在阴影之中,阿米尔蜷缩着躺在地上,指指他的迷彩球鞋说:“冷得很。”我指指脚上的登山鞋:等回村把这个给你。

晚上9点半,送走最后一缕阳光。凌晨3点,丹尼尔牵着骆驼来接我,回到乔戈里峰宿营地已是凌晨5点半。
5天后,我们终于回到苦鲁勒村,村民们聚在一起迎接我们。我整理东西准备前往叶城,记得来时带了一双皮鞋放在车上,却怎么都找不到,还好翻出一双不知哪个宾馆的纸拖鞋,我脱下脚上的户外鞋送给阿米尔,穿着纸拖鞋与驮工和村民们依依惜别。
雪山脚下的驼帮

4次进入喀喇昆仑,我都是在距离乔戈里峰最近的苦鲁勒村租骆驼、聘用驮工师傅。2008年第一次进入这个高原村落时,当地只有38户人家,共计138人,都是柯尔克孜族,房屋是用石头和黄泥粘结垒起的,远看就像一个个积木,零零散散摆放在两山相夹的一块平台上,之间稀稀拉拉长着几棵柳树,平台一侧是切割百米深的河谷,相依的山体上遗存着风雨雕凿的雅丹地貌。
在新疆地区,骆驼自古以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据成书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记载,匈奴、月氏等民族所在地区出产的骆驼非常出名。汉代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西域地区的骆驼养殖业发展迅速,骆驼数量动辄以万计,丝路重镇上还有专人养殖骆驼,提供给过往旅人和商队使用。

如今,随着公路、铁路和航空运输业的发展,骆驼的地位不再那么重要,但在自然条件恶劣的喀喇昆仑地区,骆驼运输却如星星之火,萌发出新的生机。
柯尔克孜族驮工师傅对于高原极地生存有着丰富的经验,他们能用特殊的口哨指挥骆驼,熟练地在骆驼身上捆绑物资;哪里有河、哪里是峡谷、哪里有清澈的水源、哪里适合扎营,他们一清二楚;观察气象,选择行走路线,判断过河的位置,也都轻车熟路。那些和我相濡以沫的驮工向导——丹尼尔、阿尤甫、萨拉、托乎纳扎提、阿米尔、吾曼勒、帕拉哈提,以及生活在苦鲁勒村的乡亲们,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在高原极地生存的坚韧意志,人与人、人与骆驼的深厚情感,让我难以忘怀。
离别之情

清晨,我走出丹尼尔家的小土屋,天空乌云密布,呼啸的地皮风离别之情夹杂着沙土、雪粒弥漫了整个村庄。村里男女老少三十多人聚集在即将出发的驼队旁边,如同过年一般热闹。成年男子忙着捆绑物资,妇女站在一旁等待送行,小孩在人群中窜来窜去,我从衣兜中掏出糖果分给他们。
一个少妇抱着小孩坐在地上,不时抹一把泪水,她身旁还紧紧依偎着一个不到十岁的小男孩。驮工托乎纳扎提丢下手中的骆驼缰绳,拨开人群,快步走到少妇面前,在两个孩子的脸蛋上深深亲吻着,少妇站起身,用一双含情脉脉的蓝色眼睛直直望着他,我被这对小夫妻离别的深情打动了。
驼队浩浩荡荡离开村子,忽然,有摩托车的马达声由远而近,萨拉叫停驼队,向后张望,一个穿着红色衣裙的年轻女子将摩托车停在驼队旁边,走到萨拉身边,小声嘀咕了一会儿,掏出几盒“红河”香烟塞进萨拉外衣兜里。驼队继续前行,回头仍能看到一个小小的红色身影伫立在摩托车旁。我问:“羊岗子么?”萨拉笑着点点头。“羊岗子”在柯尔克孜语中就是“媳妇”的意思。
珍爱骆驼

长时间行走在石头中,骆驼腿部肌肉会坏死,驮工很注意选择宿营的时间,让骆驼适时休息。他们会迅速解开捆绑物资的绳索,卸下驮包,把骆驼牵到避风处,一边拾柴点火烧水,为骆驼制作包谷面团,一边守着骆驼不让它们卧下——经过一天的艰难行进,即刻卧下会使腿部肌肉萎缩,必须站足一定时间。每峰骆驼每天可以享用3个包谷面团,驮工会用热水烫好逐个送到骆驼嘴里。履行完这些伺候骆驼的程序,他们才定下心来,简单吃点东西,搭建帐篷。傍晚,为了防止骆驼卧下,他们又披上棉衣,点上篝火,在旁边一守就是几个小时。
驼队终于攀上山腰相对平缓的地段,丹尼尔走在驼队最前面,不时弯腰抱起从山上滚落的石头扔在一边,或是把小的石砾踢向两侧,他是害怕锋利的岩石硌痛驼蹄。
2012年6月,驼队从特拉木坎力冰川返回,由于气温回升过快,河水流量猛增,吾曼勒带领驼队准备涉水过河,它挑选了一峰体格高大的骆驼作为“先锋”,但不论吾曼勒怎样用缰绳抽打,这峰骆驼就是原地不动,不断仰头发出吼声,吾曼勒只好牵着骆驼沿着河边向下游另寻过河的位置,这峰骆驼踌躇片刻,终于迈出了前蹄。驼队安全渡河上岸,吾曼勒和帕拉哈提同时走到这峰领头骆驼旁安抚它。我不解地问吾曼勒:“骆驼在那个地方为啥不过河?”吾曼勒说:“水里石头‘吐噜、吐噜’(意思是多多的)。”他又在腰部比划着水深,说:“骆驼知道呢!”
极限生存经验

极限生存经验2008年4月,我们翻越的第一个天堑是海拔4300米的阿格勒达坂。达坂北坡风雪弥漫,气温骤降到-15℃以下。丹尼尔身披雪粒,手提粗绳,准备在骆驼身上捆绑物资,我指向天空,问:“能走吗?”他眯起眼睛,指向达坂顶部,说:“快快地走。”并用两手做了一个锥体手势,指指南边的手背说:“那边没有雪。”驼队顶着风雪,慢慢挪动沉重的脚步,雪粒打在脸上,针扎一样刺痛。

经过4个小时的艰难跋涉,终于登上4820米的阿格勒达坂山巅。为了安全,丹尼尔让我徒步下山。我踩着厚厚的积雪,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驼队后面,没走多远,雪真停了,太阳在阴云里时隐时现,气温悄然回升,果然印证了丹尼尔的说法,山这边不下雪。
拍摄迦雪布鲁姆冰川时,我疲惫不堪,执意让驮工师傅把帐篷扎在海拔4410米、距冰塔林很近的空地上,这样能捕捉到最佳拍摄时机,又能减少体力消耗。丹尼尔观察四周,对我摆摆手,学着风的呼叫声,意思是这个地方风大,扎营不好。但我还是让驮工卸下物资,他们帮我把帐篷支好,便牵着骆驼向山下走去,说这里头疼,不能睡觉。
深夜,狂风四起,帐篷被疾速的风雪吹得变了模样,几乎贴到我脸上,窗布被吹开,雪粒不断涌进来。为避免被大风吹走,我不得不匍匐在地,慢慢挪动到帐篷背后,重新系好窗布。狂风发出的撕裂声令我惊恐,无法入睡,真懊悔没听驮工的建议。
2010年5月,完成斯坦格尔冰川的拍摄,我们准备返回迦雪布鲁姆冰川末端扎营。前方,山体与冰崖之间形成狭窄的隘口,需要淌过淹没骆驼肚皮的冰河,河的西岸就是迦雪布鲁姆冰川末端陡峭的百丈冰崖。丹尼尔、阿尤甫面对紧靠河岸一侧陡峻的冰崖,一边用两手捂住嘴巴大声喊叫,一边捡起石块投向冰体,试探险情。驼队安全上岸,停在河岸滩涂的砾石上,不到5分钟,忽然传来“轰隆、轰隆”的巨响,大地仿佛在颤动,一股寒冷的雾气扑面而来,西岸的冰体不断崩塌,几千吨倒塌的冰块顷刻间封堵了河道。如果再晚几分钟过河,整个驼队可能全要葬送在这冰块之下,我由衷地佩服驮工师傅在极限地区生存中积累的丰富经验。
媒体专栏:中国国家旅游 更新时间:2015.12.31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