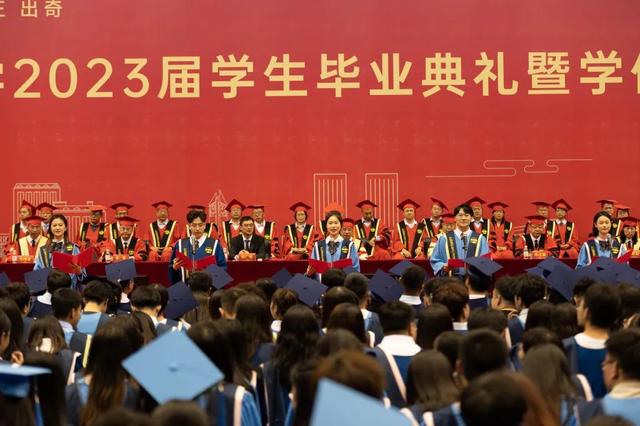北魏尊佛教为国教(规范经典武事佛法)
在阅读此文前,诚邀您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与分享,又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
引言
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较低,她们一般处于从属地位,无法主动参与社会交往活动,也很少有机会接受教育。
然而更早期的封建王朝,女性地位却不是如此,女性教育反而更加先进,出现这种现象,还要从改变中华民族的第一个少数民族中原王朝——北魏说起。
北魏由于建立于部落体制之上,在母系氏族遗风的影响下,女性社会地位较高,其社会中更有着“专以妇持门户”的社会风尚,女性也有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北魏时期的女性教育到底是怎样发展的呢?

一、一般受教者,罪孥受教者,“宫学”与家庭施教者
通过史书和墓志记载首先可以发现,北魏能够接受教育的女性总体上可以分为一般受教者和罪孥受教者两大类。
区别于一般受教者,罪孥受教者说的是有罪家族接受教育的女性,此外,北魏时期的墓志志文中还透露了失载于正史中的宫廷女教机构“宫学”。
一般受教者即除了罪孥之外的女性。一般来说,高门士族会对女性成员进行教育,以维持门户,皇室宗亲亦对女性教育较为重视,北魏孝文帝时的要臣李彪,其女
“幼而聪令,彪每奇之,教之书学,读诵经传”
《北史 · 列传 · 卷二十八》
李彪“家世寒微,少孤贫,有大志,笃学不倦”,尽管他凭借学识而身居高位,却仍为人所鄙:大中正宋弁虽与之交好,私底下宋弁却“犹以寒地处之”, 李彪为子求官时,吏部尚书郭祚也以旧第的方式处置。
在这样的情况下,除了重视培养儿子,李彪对教育女儿亦尤为看重,这不仅有其女早慧聪令的自身因素,还包含着他对于家族由寒转士的希冀,这当为“此当兴我家”之解。
此外,由于南北朝时期长期的战争,以及北魏初期的严刑峻法,不少女子以罪孥之身被没入宫中,她们当中存在幼年入宫的现象,其中一些女子还在宫廷当中接受教育,成绩学识优异者便得选拔成为女官。
如女尚书王氏讳僧男年仅六岁便由于父亲罔法而被没入宫中,但她“聪令韶朗”,故称学生惠性敏悟,日诵千言,听受训诂,一闻持晓”。这大概就是关于罪孥受教者和“宫学”最早的记载。
至于”宫学“这种教育机构为何会存在暂无详细历史可考,但大多数人认为应该与出身罪孥而手握权柄的文明太皇太后有关。
另外,宫人由于靠近皇室,向来在政治纷争中比较重要,如道武帝末年时,宫人便在清河王政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出“宫学”的设立应该与当时的政治背景有一定的关系。
宫学的教育观念在于给本是戴罪之身的女性提供教育,而在此前的中原历史当中女性接受经典教育本就存在争议,遑论罪孥出身的宫女,虽然这其中当然会有务实的因素,但是这样的观念依旧超越了性别与身份上的限制。
有关宫廷的教师,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但据可靠历史记载,李婕妤就曾担任过公主的老师一职,由此可以看出,北魏皇室成员的教育可以由嫔妃充任,与李婕妤大致同时入宫的还有王普贤,王普贤家学深厚,她的墓志铭中有言:
“妙闲草隶,雅好篇什,春登秋泛,每缉辞藻,抽情挥瀚,触韵飞瑛”
王普贤墓志铭
不论是李氏还是王普贤,她们均是在带有政治性的文化交融的背景下入宫的。
孝文帝时实行了与北方世族高门联姻的政策,这其中势必有期待这些女性能够将她们所掌握的学识观念带入皇族,移风易俗的意味在其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不论是仅仅掌握规范,还是接受过经典教育,于汉化而言便都是可资利用的要素。
皇室女性成员的教育也可由女侍中来担任。据《魏故仪同三司闾公之夫人乐安郡公主元氏墓志铭》载:
”女节茂于公宫,妇道显于邦国。永熙在运,诏除女侍中。倍风闱壸,实谐内教。“
可见,女侍中身负对宫内成员进行教育的职责,其教育对象应该就有宫内的公主。女侍中虽然也是北魏女官中的一员,但她们也与其他女官有着明显的差异。
普通女官大都由宫女选拔而来,而女侍中则一般选自皇室宗亲或豪望家族,如献文帝女常山公主、顿丘长公主以及献文帝孙太尉咸阳王元禧女元英、于忠妻王氏、前述宣武帝姨高氏都曾被选为女侍中,她们有着较高的学识,而学识则是女侍中选拔的重要标准。
除了宫廷内的女性教育,其他女性的家庭教育也不容忽视。女性家庭教育的施教者,多数情况下应该是由父母来充当,如李婕妤便是在父亲的教导下学习文化,形成了文化素养。
不过有一部分家庭由于父母的早逝,而由受过教育的其他家庭成员充当施教者,如《魏书》卷92《列女传·房爱亲妻崔氏传》就记载:
清河房爱亲妻崔氏者,同郡崔元孙之女。性严明高尚,历览书传,多所闻知。子景伯、景先,崔氏亲授经义,学行修明,并为当世名士。
二、“范妇”与“哲妇”;规范教育与经典教育
北魏女性教育中呈现出了规范教育与经典教育两个方面,其中那些遵守规范的女性,也即女性教育的目标,可以称为“范妇”,而注重研习经典者,则可称为“哲妇”。
由于女性缺少从政的渠道,持家、孝悌是社会对她们的主要要求,因而北魏时期对于女性的教育内容也多是基于礼仪规范方面。
在目前已知的北魏士族女性墓志铭中存在着很多符合史书所记《女诫》中“曲从”与“和叔妹”规范的描述。
《魏代杨州长史南梁郡太守宜阳子司马景和妻孟氏墓志》载:奉舅姑以恭孝兴名,接娣姒以谦慈作称。又如《北魏李夫人墓志》载:
夫人幼而聪悟,长弥谦顺,诸姑尚其恭和,伯姊服其孝敬。自来仪君子,四德渊茂,逮事太夫人,曲尽妇道。
《女诫》似是当时的女教教材,然而其普及度不无疑问。
另外在北魏女性的墓志中还多看到四教、四德、五训、六行、阴教等语,其中四教与四德基本为《女诫》囊括,即妇、言、容、工,六行和阴教则见于《周礼》。
时常有不同学者撰写新的类似教材,仍有内容存世的有曹魏的程晓作《女典》、荀爽的《女诫》以及蔡邕的《女训》等。
荀爽《女诫》结合经典与列女事迹来说明女性应有的具体行为,相较班诫日常的一面则多出了义理的色彩,而蔡邕的《女训》则强调女子除了仪表以外,德性更重要,仪表实是德性的展现,各有侧重。
墓志中记载当时女性学习的内容基本上是一些伦理与道德规范,除了女工这样的技巧,大致上包含了当时女性所要学习的一般内容,可以以女学、规范来概括。
除了规范以外,北魏女性也存在学习经典的现象,所谓经典,即一般而言男性学习的典籍。女子习经典自东汉以来一直是有争议的事,被认为是不守规范的,通常都会受到来自家人的压力。
《晋书·刘聪妻刘氏传》云:
刘聪妻刘氏,名娥,字丽华,伪太保殷女也。幼而聪慧,昼营女工,夜诵书籍,傅母恒止之,娥敦习弥厉。每与诸兄论经义,理趣超远,诸兄深以叹伏。
反映了女性学习经典所存在的压力,我们在此来分析一位名为薛伯徽的事例,由其志文中的“及长,于吉凶礼仪,靡不观宗焉”来看,她所学的“礼经”不是或不仅是道德与伦理规范,而有礼制之学在其中。
而像薛伯徽等人那样能够学习经典,在当时的社会中仍有着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女性学习经典存在着压抑的迹象。
在《魏直阁将军长乐冯邕妻元氏墓志》中,冯氏出嫁后因“诗刺哲妇”一反年轻时讽诵诗书的爱好,反映了北魏女性在经典学习上的困境,透露出女性学习经典与本来的规范间互相冲突的意味,女性对于经典的学习似存在着难以深入的迹象,能够达到“微解”或“粗学”的阶段已属不易。
三、武事与佛法;女性教育的两个特殊方面
除了规范教育和经典教育之外,北魏女性教育还包含——武事与佛法两个特殊的方面。晋唐之际时就已有女性参与战事,乃至展现武艺的现象。
由于军事本属男性领域,女性参与其中不仅有失规范,同时还被认为是不祥之兆。佛教则有“出家”之意,这与女性“恪守内”的规范是相抵牾的。
尽管女性掌握相关学识的现象盛行当时,但站在规范的角度,这两种特殊类型的教育对于当时的女性而言却均显特殊,接下来我们就来分析北魏女性是在什么情况下接受了这两类教育。
《魏书》卷九十二《列女传》有言:
任城国太妃孟氏,巨鹿人,尚书令、任城王澄之母。亲自巡守,不避矢石。贼不能克,卒以全城。澄以状表闻,属世宗崩,事寝。灵太后后令曰:“鸿功盛美,实宜垂之永年。”乃敕有司树碑旌美。
巨鹿在文成帝以前常与战争、叛乱牵涉,胡汉错杂,其内部和周边的形势均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是一个军事色彩比较浓重的区域,这样的环境一般意味着文化废弛,同时家族在此存续脱离不了自卫的能力,由此可见,孟氏对军事策略的娴熟极有可能是由她的家庭出身以及长期协理相关事务所致。
北魏时期,女性不仅可以接受军事教育,而且在宗教上也相对自由,太原王氏之女本是因战乱没入宫中的南朝士族成员,那时她对北魏政权不太可能有忠诚可言,因此她为劬保元恪而遁入空门学习佛法的初衷更多是源于故主与自身亦主亦友的私人关系。
结语
北魏的女性教育在汉化转型的背景下存在着力求规范的现象,但对于那些仍然处于士族化并已经进入权力核心的家族中,他们依然会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来对女性进行经典教育,期望她们能为门户的发展做出贡献。
罪孥受教者能够存在,与北魏女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除了表现出性别与身份上的突破,她们的存在也是宫中汉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表现。
北魏对于古代女性教育而言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年代,这一特殊性与北魏本身的一些政治因素,例如鲜卑的女政传统、频繁的战争与人口流动以及激进的汉化转型有关。
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北魏的女性教育有着较为宽松的环境,罪孥的教育、对女性学习经典的支持则是宽松的具体表现。
参考文献
《魏书》
《晋书》
《汉书》
《三国志》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