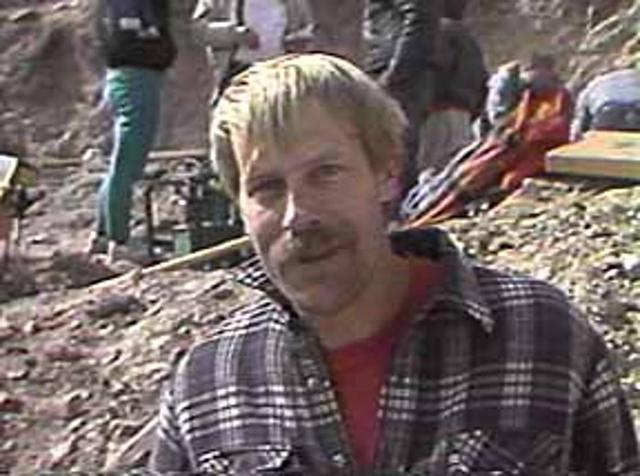巴金的寒夜人物解析(寒夜主角)
《寒夜》是巴金先生真正的代表作是当之无愧的作品之一,笔下描绘出一部囊括爱情纠葛,家庭伦理和社会问题的戏剧,不仅呈现出一部在国民统治下善良的知识分子悲剧,也把作者对于现实生活的鞭笞和对女性地位的思考完整的表达出来了。
不同年龄段的人观看这部作品总是习惯性把自己划分到具象的故事板块:如爱情占主导的读者看到的是男主汪文宣和女主曾树生早年因为在教育事业方面志同道合走到一起,让人情不自禁地幻想到一对才子佳人的爱情大戏,结果却被现实和生活折磨得不堪回首的悲剧。以家庭伦理占主导思想的看到的更是一部“婆媳大战”的当代生活现实悲剧,再或者是以职角度切入,去看一个生存在繁重工作环境中的人对上对下的唯唯诺诺和备受压迫。

作品在开始的场面中并没有叙述过汪文宣和曾树生的恋爱经验,而是一开篇就把读者带到了两人已经产生间歇的婚姻生活当中。作者只是说他们都是从上海某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因为有共同的理想——开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而走到了一起,那么在某种层面上看他们之间更多属于“合伙人”的关系,若论爱情的成分比例,似乎值得怀疑。一方面两人的外在形象有一种镜像似的反差,汪文宣矮小委琐,体弱多病而且生活在一个不富裕的单亲家庭,性格也有缺陷;而曾树生却是一个青春漂亮有活力的女人。这样不对称的结合下固然原先有爱情,也随着两人的背离而分崩离析。
当汪文宣毕业之后,进入一个半官半商的图书公司中后,以他的性格在这种死气沉沉的环境里面对繁重生活,他也会变现出勤勤恳恳的态度,微薄的收入并不能够支撑家庭开销。所以经济层面的不对称苗头开始出现,家中的开销大头由曾树生来支付,一种懦弱性格在这种夫妻关系中得的诠释。书的一开头有个非常重要的场景,汪文宣把树生惹生气了,树生夺门而出,男主并没有像传统大男子主义中那样不管不问,而是内心十分焦急想要去将树生找回来,但是这股动力并不来源他自己,而是需要母亲鼓动才胆敢去“追妻”。以致于后面找到妻子后说出“我需要你”的话来,所为儿子和丈夫的双重角色,无异于是软弱无主的形象。
这种多方面的钳制和生活的琐碎让汪文宣从一开始的理想青年沦落成了夹在母亲和妻子之间的受气包。

实际上汪文宣这么难受,是因为他一直没弄明白,家中的“两个女人”其实代表着新旧两代人,代表着相互对立的两种道德观念和文化价值取向。他的母亲执行的是极端传统的父系社会法则,“她希望恢复的,是过去婆母的威权和舒适的生活”。而曾树生与婆母争执,自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婆媳不合,而是一种“不会向她婆母低头认错”的抗争姿态。所以汪文宣是很难逆反这种代表新旧思想的矛盾。
于此同时,汪文宣的悲剧根源在很大程度上置于他本身的思想性格,因为从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变化就可以看到。不过几年时间,他就让自己从个敢于为爱情和理想向世俗挑战的青年,变成了自觉地与这种传统认同的苟且之人。比如在家庭的两阵对垒之中,他明知妻子并没有什么大错,错在母亲,可他却无原则地安慰母亲说:“妈,你不要难过,我不让她回来就是了。”这就从客观上纵容了母亲所代表的父权势力,不知不觉中将妻子一步步地从自己身边推了开去。
当然汪文宣最后的死,是出自作者的意思,作者并不忍心让他死去,又不得不让他死去。一方面在怨愤这个“老好人”,责备他不曾“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但同时又认为,汪文宣的死,除了社会的原因外,“他的母亲和他的妻子都有责任”更多的是其本人最终对旧势力所作的妥协亦有着极大的关系。在“新”与“旧”的文化冲撞之间,他选择并归靠的是“旧”的一方,正如在“生”与“死”的人生关头,他轻易地就放弃了“生”的可能一样。这种结局无异于把家庭和社会化矛盾推向了高潮,更叫直白地指责。

女主曾树生的形象在整部作品的社会环境中显然是格格不入的,作为一个传统社会中的女性,要挑起家庭开销的担子,每天上班。实际上在大部分人看她的的工作不重要,似乎只要打扮地漂漂亮亮,能说会笑,让经理主任们高兴就可以很好的得到收入和工作环境。甚至于在汪母眼中,她就是一个不安分的“花瓶”,极度的仇视和反感引来双方频繁矛盾冲突。
一方面,以传统的男权意识审视曾树生,她的所作所为、所从事的职业无疑触犯了男性社会的某些禁忌,比如“她竟然甘心做花瓶”,挑战着男性社会的权威;一方面她和汪母的冲突中丝毫不会退让,读者能够看到有关她宣誓自我权力时的大量说辞:“你管不着,那是我们自己的事!”“我老实告诉你:现在是民国二十二年,不是光绪、宣统的时代!”
实际上我们知道曾树生与婆母争执,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婆媳不合,而是一种“不会向她婆母低头认错”的抗争姿态,她虽从不主动出击,但在为人根本的立足点上,却始终不曾后退半步,因为她坚信生命是自己的,她有权选择人生的道路,有爱与不爱的自由。
她的人生无时无刻不在向社会宣誓女权,甚至用最争议的方式来结尾:对《寒夜》争议最多的,莫过于曾树生竟“抛弃”了家庭,跟着“另一个男人”走了。出走的结果是丈夫死了,婆母和儿子不知去向。但凡以传统的男性立场看问题,无论出于何种动机、也无论她与那个男人是否“关系暧昧”,其行为都是不可饶恕的,但是那又如何,她一直以来都是用逆反的形象出现是视野当中,这种结尾便是对她性格的呼应。
所以我们再次看她和汪文宣的差异对比时,汪文宣怯弱,树生贪玩,两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不合适的,也在各自说各自的悲剧。

汪母这个角色或多或少地被读者“厌恶化”了,因为她是汪文宣人生悲剧的直接影响着,也是曾树生悲情前半段的造成者。实际上看汪母自己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悲剧的代表。她年轻的时候也有自己的追求,是昆明的才女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但是因为战乱改变了她的一切。生活所迫让她开始洗手作羹汤,宁可自己强忍着疾病,也不愿意多花钱雇别人洗衣服,所以她自身很是痛苦,加上她从小接受的便是封建思想的教育,演化成为了一位充满封建伦理观念的旧式大家长。无可厚非她很爱自己的儿子,但是儿子的成长并不是一个独立人,而是她的私有物品,让儿子无条件归顺,让媳妇也无条件顺从,媳妇应对是儿子的奴隶。这些荒谬的想法时时刻刻都在加剧她和曾树生的矛盾,她希望媳妇能像媳妇,不打扮不交际不张狂,老老实实在家里孝敬婆母、相夫教子。
所以她极力想要维持的那一套以传统的男权文化等级性为内涵的行为规范,无疑具有显而易见的性别专制意味。

从三位主角的人生状态和性格分析,都告诉我们这部作品的悲剧性。汪文宣的懦弱性格主注定他不可能在这个时代安稳的活下去;汪老太太的的封建性和曾树生先进思想也产生了较量,决定她们不可能在同一屋檐下共生;曾树生的各种反叛个性也在宣誓自己的女权和独立,更加不可能持续让自己在喘不过气的家庭中生活。这些种种的不合适、不可调和,实际上是来自巴金从未间断过对于中国女性命运的关注与思考。正如某些学者指出的,巴金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将对陈旧制度和传统的押击,弘扬民主和个性解放放在首位,并始终将被生活重负压迫得沉重而乏味的家庭生活看作是一种不祥的征兆。
所以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总有一个叛逆者,一个精神上或行动上的旧家庭的叛徒,也有类似于汪文宣和汪母的重复形象,用这样的反叛者去撬动传统和封建形态,试图建立起一种觉醒的状态。这就造成了《寒夜》中各个角色都不是“完人”,各有残缺的形象,因为她们都在按自己的性格和方式生活,强行的拉到一个生存空间内,矛盾自然就产生了。当然站在读者的角度,更加喜欢那些带着正能量,宣扬乐观主题的人物角色,固然以为曾树生有这种独特的魅力,但是其结尾似乎又给读者一种有些违背道德义务的复杂和模棱两可感觉。这些一切都是必然的矛盾,也就是预示着一切都是必然的悲剧。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