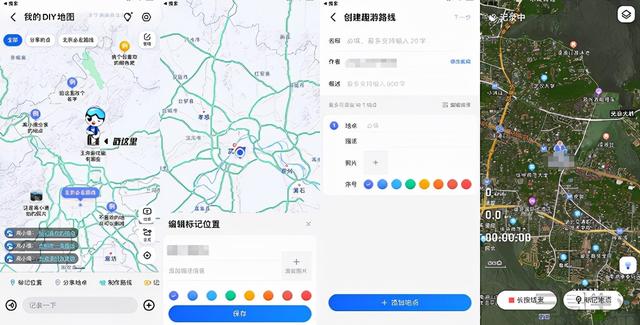冷门好看的重生古言小说(强推唯刀百辟的民国重生言情文)
推文啦,最近有大人给姑娘推荐了《当女博士重生到民国守旧家庭》,看过之后大爱,女博士重生于民国乱世,凭借智慧夹缝中生存,另辟蹊径,文笔可爱,非常喜欢的文,喜欢的大人们可千万不要错过~,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关于冷门好看的重生古言小说?跟着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冷门好看的重生古言小说
推文啦,最近有大人给姑娘推荐了《当女博士重生到民国守旧家庭》,看过之后大爱,女博士重生于民国乱世,凭借智慧夹缝中生存,另辟蹊径,文笔可爱,非常喜欢的文,喜欢的大人们可千万不要错过~
推荐书名:《当女博士重生到民国守旧家庭》
作者:唯刀百辟
关于嗑书之前的一点点剧透:女主重生于民国旧式家庭,母族被父族算计,生活岌岌可危。她小心行事,在姐妹中示弱自保(此处可参考明兰和顾廷烨),被大姑母接去香港求学,暗地利用前世学识寻退路,被物理系教授赏识,终于展现头角。而战争的开始,上海的沦陷,不同背景家族的争斗交融,将这盘故事推上高潮。
男女主的故事节奏:男主是香港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作为出生求学皆在英国的“白华”,他浪荡的坦荡,无畏亦无求。与女主相识于自己的荒唐艳事,也撞见过女主与未婚夫的私会,后在上海任职,被托付照顾女主,在城之沦陷中,于国于义的碰撞,令他看到了自己的稻草,是灵魂,是希冀,是爱,是生存的希望。很喜欢的一对CP,最合适也是最爱的人。
推荐片段:
1、相对论中的绵薄之力
楚望也凑过去看他的选课表,只见上面写着大大的七个字——“中国古代文学史”,后面又跟了丹砂书写的两个猩红的大字——重修。她抬头来看了叶文屿一眼,神情里掺杂着怀疑与敬佩。叶文屿倒是浑然不觉,好言相劝道:“香港许多学生中文都十分堪忧。中国学生都上得十分轻松,学分还很高,所以许多人都选了这门课。”“你又不是从小背四书五经、写四六文章长大的,你选它做什么?”“觉得这课十分有趣。”“和我姐姐一样有趣么。”叶文屿嘿嘿笑了,“你也选古代文学史吧,好歹拉我一把。”“……”课程表上依旧是清一色的普通力学、结构力学、复杂电路之流。在课表最末端,她看到一门将要延续一年半的课程,学分是古代文学史的两倍,名为《相对论》。她想也没想,提笔就在表上填了这门课的名字。叶文屿来不及阻止,眼见她填完,神情诡谲的问:“你确定要选?”楚望点点头。“你知不知道这门课一年半考一次,考不过只能再学一年半,及格率不到五分之一?”她摇摇头。不过也表示可以理解:两种理论提出至今,也不过才二十年与十余年时间。在这个物理学家稀缺的时代里,这算是崭新学科中最崭新的理论。“你知道这课谁来讲么?”“谁?”“我小叔。”她将所有考试时间不冲突的课程都选了一遍。打开这一学年的课本翻看了一遍:数学是解二元多次方程和算相交几何图形的角度数;电路是将复杂混联电路简化为清晰易懂的串并联……在历经百年归纳总结的后世,这些课程在高中课本里两周之内便能讲得再清晰明了不过,在这个年代却要学上一年。楚望不由得感慨:不管那一种学科,竟都是世人靠聪明才智外加经验总结而进化起来的。她唯一能勉强打起精神来听一听的,只有徐少谦的课。对于相对论,他另辟蹊径,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独到见解。这本她早已念老的学科,从徐少谦口中讲出来,却如同在听一个历久弥新的故事。开学第一堂课,他讲的第一句话,就让楚望整个人一个激灵。他说:“人类有没有可能快过似箭光阴,从远古来到现在,或是从遥远的未来,来到这个时间点,你与我身前?”她从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她学质能方程的最初,便在想:若是快过时间,那从一个时间维度,去到另一个时间维度的我,是否还是我?是不完全的我,或已是别的什么人?有那么一瞬间,她差点怀疑:徐少谦这开场白,似乎就是在向她发问似的。她发了会儿呆,直到听到徐少谦问了句:“从逻辑上来讲,穿越时空,是否可能成立,有没有人来讲一讲?”楚望回过神来时,便见徐少谦远远的,微微笑着看向自己:“Linzy,有没有兴趣来回答一下?”她略略想了想,站起来说道:“假设可以穿越,那么我回到过去,去杀掉自己母亲出生之前的外祖母,这将产生一个悖论:先有我的外祖母,然后有我。我的存在,证明了我祖母的不死。因而,我无法杀死我的祖母,也因此否定了穿越的存在。”徐少谦笑着反问道:“那么在你回到过去那个时间维度,在你到来的那一刻,已经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引起连锁变化,故而使得你无论如何都无法杀死你的外祖母。”楚望微微眯起眼睛:“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是相对的。过去能造成未来的变化,也仅是‘某一件事件’而已。”徐少谦摇头道:“不对。在你落地的那一刻,便已改变这个世界的所有未来。”她微微扬起头:“改变什么?这一秒减少更多氧气,呼出二氧化碳?这种改变只是微不足道的。这世界所有重大事件并不会因我个人而有所改变:比如因工业发展来带来的环境灾害,比如物种灭亡,比如战争。既然我带来的改变不重要,为何又会有连锁变化,来阻止我杀死自己的外祖母?如果重要,这个世界会如何修复我的存在,带来的微小改变?”这时下课铃响了,徐少谦便也没有再说下去。两人都知道两人仓促对话间,其实有颇多漏洞。再往下说,还会有许多“这个世界还是从前的世界,或者已经是别的世界”之类的问题。许多同学都起身抱怨,说第一堂课就听不懂,给这么大的下马威,以后可怎么学?徐少谦被一群带着诸多疑惑的学生拦截在门口,楚望也夹着书本准备出教室。一位大约没有怎么跟上两人思路的学生,在楚望经过时,突然没头没脑的说道:“可以称之为重大事件的战争已经发生过了。”楚望只是冲那位同学一笑,便匆匆出门。她所拥有的物理知识并没有告诉她,该如何尽绵薄之力,才能做到改变特定的某一段历史。
2、论淑女的必修课
自打那一天起,楚望除了要和亨利先生互对英文之外,还被葛太太拿小鞭子在后头逼着同谢弥雅、真真一同学跳舞,从探戈跳到伦巴,跳得楚望叫苦不迭。除了这两苦之外,从每天早晨端起早茶杯子开始,她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被框入葛太太的条条框框之内的。比如:喝茶时托杯的姿势、搅拌杯子的动作、方向、次数都是规定好了的。超过了,则视为举止不得体。再比如:冲人笑时,不能露出牙齿——自古以来笑出牙齿,那都是奴仆为了取悦主人,是取悦的、下等的笑容。上等的笑容,决不能见着一颗牙。笑不露齿,同时要笑得自然,还要笑得好看,这就非常难了。自此,葛太太又提出了一个新规矩,叫做——表情控制与管理。对于葛公馆许许多多规矩,谢弥雅自小学到大,自然心领神会。楚望压根记不住,只好寻了纸与笔,葛太太写一条,她记一条——方便回去慢慢记。葛太太也十分有耐心,有时还会指点一下她的笔误:笨鸟先飞,肯学是好事。新裁的衣服送上门来才没几天,葛太太又叫了裁缝上门来,说是要给她制冬天穿的新衣。楚望只好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阻葛太太:“我一天换五身,都能两月不重样。先等我将衣柜里的衣服都穿一遍,再做新衣服也不迟呀。”“那又如何?葛公馆的下人们又不是洗不过来,”葛太太恨其不争道,“你好好向那两个丫头学学:哪个不是上赶着来我这里求着我指点指点?姑妈只想全副心血的栽培你,多好的机会,你也不懂珍惜。如今名门闺秀们,人人都有一手绝学:真真会唱京剧,弥雅会唱歌剧,那么你呢,你会什么?”“我会弹钢琴啊。”“钢琴这东西谁不会弹?到大场合里,又不需要你像个钢琴家一样去技惊四座的表演,只要会弹几手时兴的就好了。”葛太太道,“以后到了不得不交际的场合,别人问你会什么,你说:‘我会科学实验’。还不笑死人了?”楚望吐吐舌,一溜烟跑回房去了。葛太太在后头看着,无奈笑笑,倒也随她去了,由着她开心就好。虽说一门心思想让她多学点东西,但大多数时候,她还是由着楚望放纵本性的做她喜欢的事去。但只英文、举止得体与交际舞这三样,是必须得好好学一学的,楚望倒也绝不含糊。对于另外两个丫头,葛太太的教学已经进行到了一个相当诡异的地步。某天楚望下了楼来,正准备去油麻地,经过会客厅,恍然听到这么一段对话:葛太太:“……所谓搭讪,自古以来你们都以为这必需得是男人主动的事,所以你们就无所作为,巴巴等着人来你跟前?还是说你要艳压群芳,让满屋子男人都争着抢着,为了你最好打一通架,头破血流,谁赢了谁赢得你?自然不是这个道理吧?所谓交际场合,大多对子都是搭好的。即使是随意自由的交际,你心底要有,也只有一个目标。怎样使他注意到你,放松警惕到你面前来,也只使他——而不是什么别的人到你跟前来,这便是一门学问了。”薛真真听完,突然亦真亦假的往谢弥雅怀里一摔,哎唷一声,尖声尖气的说:“公子!对不起!我弄脏了你的燕尾服!请脱下来,让我替您洗一洗……”谢弥雅将她往怀里一搂,乐得哈哈大笑。真真半躺在她怀里,问道:“像这样么?”葛太太冷冷道:“原来你在笑话,我怎么觉不出哪里幽默了?”葛太太却笑也不笑,直直往外走两步。两位丫头也噤若寒蝉的收敛了笑,安静的听着。葛太太走到一盆杜娟旁。那杜鹃开得正艳,浓烈烈的,下一刻便要艳过头,枯萎过去了。葛太太也着了一身黑色软绸旗袍,上面开着一朵朵紫色海棠花的花瓣。她朝真真斜睨过来,眉眼缓而低的往下压,只徒然留给身后两个丫头一个慢慢凋谢的笑容。笑容淡去之后,两人都怀疑刚才那个笑是否真的存在过。再去注视葛太太时,她已背对着两人在嗅那花——这不禁使人有些失落,也想去看看那花是否真的这么美,花到底是什么香味。——“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古人诚不我欺也。待两人都呆呆的,不禁向前走一步时,葛太太便又回过头来问道:“看明白了么?要让他觉得你是个美好的误会,因此打从心里想让这个误会成为现实。看物,而不是看人。这叫——醉翁之意不在酒。”在门口穿鞋的楚望,将这一切都听到看在眼里。上一世单身二十五载有余,她大惊失色:原来撩汉是这么一门超凡绝伦的技术活!但是演好了,像葛太太这样,是一门艺术;她这等面部表情匮乏的科学怪人去演,分分钟就是一个车祸现场。她啧啧舌,心道:这种赏心悦目的画面,让别人来演绎就好。她么,只适合研究卢瑟福散射公式。
3、择益事难
想到走狗似的中国巡官,想到那位少佐先生,想到可恨至极的“治外法权”;而今天为求个公道,在自己国土上,她竟然要向这昭示中国百年屈辱史的《天津条约》寻求援助。她恨极。她恨这寸土地上每一国列强,恨委曲求全腐败无能的自己的国家,恨自己没有大开的金手指,没有爆满的查克拉,不能爆衫,更没有天马流星拳可以让她拳打少佐脚踢士官,手撕各种不平等条约,再一脚踏平租界地,叫霸占中国的洋人统统滚回老家去。她太无能,能做的太少太少,所以此刻也只能站在街边委屈得眼泪鼻涕狂流。谢择益一直盯着她看。一会儿工夫,她脸上神情瞬息万变,终是没忍住笑了,“你看看你哪里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说罢倒不嫌弃她哭的难看,一伸手,动作极其自然的将她散下来的乱发理到耳朵后面。她哭的正起劲,根本没意识到他动作可疑,“本来就不是。”谢择益摸出一支烟正要点上,听她这么回答,手头动作顿了顿,点头道,“好好。正好我也不大喜欢她们。”楚望哭的难看,吸吸鼻子,突然盯着他手头的烟看。谢择益看懂她这个眼神,将刚点着的烟递给她,眼睁睁看她将烟衔在嘴上;没等她吸上一口,一伸手,又麻溜将烟抽走了。“好了。”他说,“这东西,多吸无益。”楚望仍旧盯着那支烟。他根本不理会她,将烟叼在嘴里转身就走。她泄气的蹲在路边,像个抗争失败的无产阶级工人农民一样垂头丧气。突然一瓶屈臣氏可口可乐放到了她面前。她抬头来,微微有些讶异的看着谢择益。谢择益笑道,“喝这个好过吸烟。”见她仍旧盯着自己看,又说,“只有可乐,上海买不到沙示,想喝也喝不到。”接着不大优雅的同她一块蹲到她身旁的马路牙子上,替她掀开可乐瓶盖,递给她时,笑着说:“想不想听听我的故事?”不等她回答,他接着讲了下去,“在伦敦念中学时,我曾有过一段时间十分困顿。我生于英国长于英国,长到十四岁也不大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中学以后,学校里突然多了许多肤色名字与我相似的人,大部分都是中国来英国求学的留学生。他们大多生的矮小瘦弱、不懂英国规矩、举止也显得不太有教养,故而是我的英国朋友们课间取乐欺负的对象。曾有一次,他们将一位绰号‘Looty’的中国学生扔进泥沼地里,并取笑他说:‘知道为什么吗,从前你们打了败仗,我们英国兵去了你们的圆明园,将你们皇帝母亲的爱犬带回了伦敦,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并取名为Looty。’”“父母都是中国人,却长于英国;不论对于英国还是中国,我都没有归属感。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英国人,也不想要成为中国人。但是听到那句话时,不知为什么,我既困惑又愤怒。困惑的是,为什么鸦片战争的结果是维多利亚女王收获一只狗,而不是维多利亚的情夫John Brown被送给慈禧太后当太监用?英国中学里的史学教师信誓旦旦的说:‘英国人征服大陆靠枪炮、病毒与细菌。’可是中国难道没有病菌与钢铁?英国凭什么征服世界?”“而愤怒的后果又是,我在学校打架了。帮中国人揍英国人。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做。我说你看我与他们像不像?我父母亲也是中国人。他们叫我的英文名Zoe,说,‘Zoe,他们身材矮小举止粗俗,你与他们完全不一样,你为什么要帮他们?’ ”“为什么要帮他们?我不明白那一刻的愤怒源自于哪里,很多年都不明白。甚至极度怀疑自己:我究竟属于哪一国?究竟该偏帮谁?我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存在?”“那一架打的很痛快,我头破血流,他们比我更糟。我赢了,赢了的结果是:被学校开除。”“回了香港,渐渐学了一点中文,也想明白一点事情。我祖父是个奸诈的商人,帮英国人向中国倾销鸦片,低价买入中国瓷器与茶叶贩售到英国,两边获利。他还帮巴富尔与中国道台作过翻译,以一万七千两买下当初那块盐碱沼泽地,自此上海开埠,六十多年后的今天终有了这十里洋场,他实在功不可没。谢家两辈人都在替英国人效犬马之劳,而我父亲仍旧还想叫我接着做英国人的狗。”“我并不喜欢被称为英国人。有时候我都在想,我整个人简直就像是被清政府割弃在外的香港:背靠整个大陆,却与整个中国都格格不入,独自面对着全世界。痛恨自己的中国血统,恨中国弱国无强兵,又腐朽糜烂至极,是最看不起中国的那一个,却又是最希望她首先强盛起来的那一个。”“我始终记得,我先有这个中文名字,后才有英文名。我父亲众多姨太太,给他生了一堆的孩子,只有我有中文名字。择益,是我母亲在伦敦一家公立医院想出来的,以中文音译到英文,能对上的只有一个女名,Zoe。所以自小到大,我很讨厌自己的英文名,后来才知道,这大约是一位传统中国女性的智慧。为什么是择益,而不是择易?我中文不好,却很早就懂的一句中文谚语:‘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她一早就知道,未来对我而言,择易事易,择益事难。是不是这个意思?”
4、钟意
“三小姐,你大约不知道,你来上海以前,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当我将灵魂与身躯押给殖民者时,我已经不可饶恕。所以在最好的情况下,六国调查专员会来问你这段时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与纺纱厂有关、与佐久间或是我有关。六国公使来了,也几乎证明,将殖民者与不平等条约赶出这片大陆不远。不要怕残忍,你知道自己拥有的权利与证词的份量,请为他们的罪孽加上你的一笔。”她心头一震,一股战栗传遍全身。她能明显感觉到那是一种痛与震撼并存的难以名状的感觉,让她眼泪汹涌而出,将枕套沾湿一片。她感觉他起身为她整理被子时,摸到那一片湿润后,他动作一顿,又接着说,“明天公使入港时,会开放小部分港口。公使入港时,葛太太也快到了。”她没有说话。他接着说,“回去福开森路时,见斯先生在楼下等你。若是方便,我便叫他明早过来找你。”她仍旧没有讲话。他用指腹替她刮去脸上眼泪,轻声说,“不要哭,我没什么好值得同情。”她做事向来极有目的,也从来都懂得自己想要什么。她站在陆地上,用双脚,用代步工具去争取,大部分东西似乎总能得到。可不知从何时起,全副身家置身在汹涌浪潮的一艘小船里,所有想要的,所有所求的,都像是在刻舟求剑。她动了动身体,正对仰视着他,哑着嗓子问:“谢先生,在华懋饭店时,你叫我等你一下……那时,你是否要同我说什么?”他低头静静看着她说,柔声说,“已太晚,是时候该睡觉了。”想想,又说,“往后有机会再告诉你。”她仍睁着眼睛将他看着,非得要等到他回答。他仍坐在她床头俯视着她,一动也不动。她看到那双眼睛,又回想起他看向自己的眼神,好像在看着什么极刺目的事物,必要眼睛微微眯起眼来才能看清楚。他说,“临睡前,给我一个晚安吻,可以么?”他不知何时已换上那一身漆黑军装。夜色里,白色石雕一样的轮廓与鼻梁,深陷的眼窝,睫毛里若隐若现的泪痣,极浅唇色……她打主意要好好看一看他时,几乎忘了回答。在她看到他的睫毛耷拉下来,几乎将眼中失落掩饰过去时,她缓缓支起身子,跪在床上;左手小心的扶着他的肩,将嘴唇凑上去,在他因她靠近而轻微抖动的、半垂着的眼脸上轻轻亲吻了一下。唇离开他的眼睛时,他缓缓睁开的眼睛,眼神可察觉的从不可置信一点点变成惊喜。她坐回床上,有点不敢看他。花园里的路灯光从白色纱帘倾泻进来,使得肃穆的白色病房里全是交错着的纱影。风从敞开的窗户缝隙吹进来,她短短头发顶上几根倔强的头发吹得东倒西歪。她觉得有些痒,背过身去扯开纱帘,想将窗户拉上;雨下过了,乌云散去,到这时候才隐隐有那么一点月亮的影子,但只薄薄一层;枕头被她压在膝下,背过身去时,恍然有那么一瞬,她似乎从窗户玻璃上看到两人的影子。他就坐在她身后的床头上。感觉到他冰冷手覆上自己的右脸颊时,她伸手扯纱帘的动作一愣;那动作本该十分轻柔的手掌,突然将她整个整个身子扳过去,脸正对着他。那本就不甚牢靠的纱帘,在她惊惶之下被扯脱落了,像夜里的荧光水母或者视网膜上一层薄雾,在她身后落了下来。谢择益吻了上来。轻轻碰了碰她的嘴唇之后,她听见他附在她耳边轻声问:“知道这样是什么意思么?”她愣住了。于是他又说,“那这样呢?”随即她察觉到立马覆上来的柔软的冰凉,正在慢地,慢慢地,轻柔又缓慢吻她的双唇;她呆呆的跪在被子上,他俯身下来,她与他仍旧保持一点距离,却能清楚的感受到他触碰她脸颊的手掌与指尖的温度,比他的唇冷一些。他眼睑垂下来,微微偏着头时,睫毛轻轻搔过她的脸颊的瞬间,她才突然的意识到——他在吻她!
5、苟活着相伴
谢择益点燃香烟衔在嘴上,将火机与剩余整袋香烟返给他,转身推开长廊窗户,往楼下看去时,朱尔查正从福特车上下来,仰头看着他。言桑也站到他身边,看了会儿朱尔查,说,“你照顾不好她。”“三小姐自己便能过得很好。”谢择益猛吸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以后,转头说,“斯先生什么时候的船?”“我找不到理由说服自己放弃她,”他说,“在这之前,我不会走。”谢择益哑然失笑,“我竟十分羡慕你。”两个人,一个太过执着,活在自己构筑的诗意王国里。另一个又太过清醒明白。因为这一句话,在楼下那一队英军上来之前,言桑一直定定的将他看着。看这个效忠于帝国主义的军人,在为数不多的几分钟里所做的一切。他先从军装上一袋里掏出一封信——在她生气时,他离开医院回到福开森路,吃力的写了数小时的信——叠好放在她床头。尔后从花瓶里折下一只尚还算新鲜的白兰花——他趁夜回来时,莫大的好运使他遇上了从集市赶夜回家的贩售白兰花的老太太,便将所有剩下的花都买下;几朵放在福开森路的活骨瓷碟里,另外几朵插在她病房中——其中还未开败的一朵,置于给她的信上。他的上级已经抵达三楼,面容肃穆的在病房外等着他。他仅回头看了一眼。尔后,言桑亲眼看见那个不被父亲尊重的“白华”,那个血统身份都不定的Zoe Tse——他摘下象征军人荣耀的肩章与帝国的勋章,解开军装腰带,脱下陆军军服外套。接着取下费贝达的金钥匙,动作温柔的挂在她颈上。做完这一系列动作以后,他已经一无所有了。于是单膝跪在她床前,低头亲吻她的手背。这幅画面兀地将言桑震动了,并牢牢铭刻在他心中许多年。他不忍再看下去。门外等候的军官们似乎也为这画面动容。但似乎所有人都下意识的保持安静,没人催促,也无人打扰。他转身站在墙角,点燃一支谢择益给他香烟,没有吸。灰烬在他手中慢慢抖落。谢择益毫不犹豫走出病房,将军服与简章交给他以往最为熟悉的中尉。那位中尉最后红着眼眶叫了他一声:“长官。”眼看着谢择益随那一队军人离开,于他而言似乎过了一个世纪。言桑猛的回过神,大步狂奔着追上去,在他们上车以前,用中文叫住谢择益的名字。谢择益回过头来看着他,等他发话。他回想起在华懋饭店里,他看见楚望看他时那个眼神。她那样迟钝的一个人,某一天竟也能敏锐如他,被一个人的眼神所震撼到失魂落魄……“谢先生,”言桑定定的看着他,用中文斩钉截铁的说,“我恐怕你弄错了。”所有人都疑惑的看着他。他喘口气,接着说:“就算你背负罪孽,受自己与同胞亡魂谴责一辈子,你也必须苟活下去,谢先生。因为除了你,这辈子再没人能照顾好她了。”讲完这一句话以后,他看见谢择益的神情,从不解,到动容,到震动至眼眶通红。他就这么定定看了他一阵,转身钻进车里。言桑终于松了口气。这话不是对谢择益说的,而是对他自己。他仍没有放弃她,可是他知道,他败给了谢择益。在他看见谢择益在她病床前跪下去那一瞬间,他几乎就明白了,这个白华军人,不可能放弃她。这是旁人看不到的诗。只有她,唯有她。他的无坚不摧,他的柔情似水。是他的大陆,他的心驰神往。他就是她的城池堡垒:愿为她战死沙场,也愿为她苟活着相伴到下世纪。你叫他如何放弃她。
非常喜欢的一篇文,内藏很多对大世的探讨,以及寻得世间真爱的欢喜感触。
文章中等长度,阅读18H
ps:由于后台问题,需要资源的小伙伴请后台回复“当女博士重生到民国守旧家庭”
,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