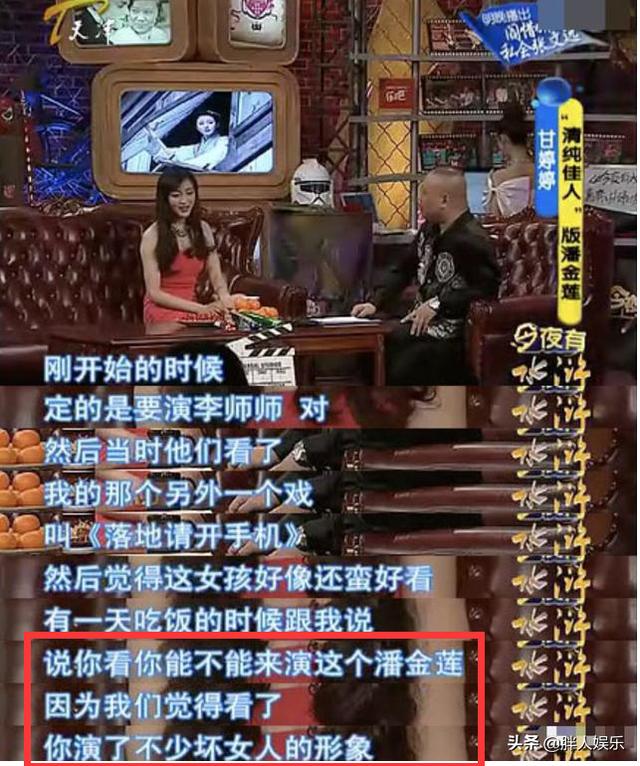桌边的风景画(风景画的室第)
列宾美术学院后面右转,一条彼得堡老旧的巷子里,那里有风景画家库茵芝的故居。彼得堡阴冷的空气里弥散着阴冷的气氛,老巷古旧的样貌中印刻着古旧的故事。在当今的彼得堡,这故事并不为城市所记起,故事的氛围,与城市的氛围相去千里。其实距离我们只差了九十余年,然而仿佛很远,想起它们,就像进入到一个穿越的故事。彼得堡老城的多数建筑至少建于百年前,稍优美的建筑便会在门口钉上铜牌,标明建造年代及设计师,一百年的与二百年的,在外观上并没有分别。老旧的彼得堡,在它的老城区,老建筑其实无所谓功能划分,可以居住,也可以当写字楼。库茵芝的居所那座小楼里楼上楼下掺杂着办公室与公寓,他住四楼。一部有着铁拉杆门和铁链子的老式电梯上上下下,那是我至今见到的唯一一个十九世纪影片里老式电梯的实物。圆形门洞,居民楼围成的巨大天井,院内的石板地翻新过,做的愈加像当今欧洲的口味。当年库茵芝在院落里走进走出,巨大作品运进运出。远远看见角落里单元楼四层的玻璃穹顶——那是他的工作室。
画室巨大。大型天窗占满半个屋顶——这便是最讲究的画室,画色彩的人讲究光线要从斜上方照到画布上。我曾到过无数画家的工作室,这样的天窗极难再遇。光线射进来。看起来油乎乎的画架,上面摆着一张中等尺寸风景画。看起来五年没洗的画笔。调色板上摊开的颜料被调的灰乎乎脏兮兮,被调到说不清是什么色相——他被人津津乐道的钴绿色的运用,原是在画布上色相对比而产生的效果,今天看见了,若是放到调色板上,跟调废的颜色不相上下。旁边摆着一支被他挤过的熟赭,瞬间一个念头想挤出来用它画两笔——曾听一位俄罗斯老画家说,从60年代学画起,俄国颜料质量越来越差,一百年前的颜料不知是什么质地。画室里陈摆着几张小幅作品,小到像巴掌大小,几张中等尺寸作品。库茵芝的真迹,多在博物馆中,现在俄罗斯的艺术品市场很少见到他的画,甚至连参考价都很难定位。有的画家有价有市,有的画家有价无市,库茵芝,无价无市。
在库茵芝入住前,这里是艺术家克拉姆斯柯依的房子。克氏在这里为人画肖像,忽然一头栽倒在地,死了。这种死法很艺术,很有英雄主义的情节感。在这个有着巨大天窗的巨大画室里,想象当年他倒在画架前,一束光线从巨大天窗外照进来,照在穿着黑色工作服的背脊,调色板上抹开的笔痕如秋叶的叶脉般。
最被国人关注的是他的经典之作《第聂伯河上的月夜》和《白桦林》,都是近两米尺寸的大型绘画,一张入藏彼得堡俄罗斯博物馆,一张入藏莫斯特特列恰可夫画廊。两张作品都很传奇。1880年,他举办一场个人展览,排着长队的观众挤进展厅,发现偌大大厅只有一张作品——月光发出荧荧绿色,照在深暗的第聂伯河河水上。一年后,即1881年,他再次举办一场个人展览,观众再次排着长长队伍挤进展厅,再次发现偌大展厅只有一张作品,这次是他的《白桦林》,同样有大面积绿色,比去年那张荧荧月光的绿色稍稍显得泛暖。那时他在38到39岁之间,库茵芝若活在今天,可能会像宋庄里的年轻艺术家一样,敢做行为艺术,敢用偏门的综合材料。当年克拉姆斯柯依专门留下《笔记》:他怕几十上百年以后作品颜色发生改变,以致观众不理解为什么当时库茵芝的月光如此吸引人。钴绿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型的颜料,没有经过时间检验。其实,钴类颜料的抗氧化性和日晒牢度都属上乘。大胆猜测,如果隋唐五代的青绿山水里的蓝色不是石青而是钴蓝,保存到现在,或许会比现在鲜亮一些。后来,在中国,钴蓝只用在青花瓷里。莫奈用钴紫描摹弥天大雾,描摹火车蒸汽,现在看,气体依然新鲜,因为颜料新鲜。我们现在看到的月光的荧荧绿色,跟130年前应该差别不大。我不知道当年他在颜料管中挤出钴绿的瞬间是否心中有数。他比梵高幸运:梵高爱用的铬黄在当时同属新型颜料,如今已被证明缺乏稳定性。
列宾说谢洛夫犹如一只灵缇,此是夸赞,不过谢洛夫的笔意稍稍笨拙——“笨拙”绝非贬义,两个字后面是古拙的视觉感,可以理解为性情使然而自然而然形成的画面效果,也可以解读为某种表现力的刻意经营。倒是库茵芝,真的像灵缇一样灵活敏锐而带着一种灵透之气。如果换成列宾那种洒脱的笔法感,或是苏里科夫像一笔笔凿在画布的谨慎,或是希施金的枝干树叶等风景元素颜料微微凸起的质感表达,也会很美,只是少了一种灵性,一种水汪汪的东西。明斯克的白俄罗斯国立美术馆藏有他一张小品,画的一缕夕阳洒在海面上,通篇的架构只有一条光芒,一片单纯的色块摆在那里。他的很多张画面有时在构成规律下解构拆分来分析略单调,然而画面效果不单调,生动,活泼,显得丰富。此是天赋,先天带出来的美感敏锐性,好像对美感很容易把握,伸手既能抓住,有时后天不一定能够习得。赵无极说好的作品应该画起来很累可看起来轻松。库茵芝的作品看起来很轻松,单纯的构成规则造就单纯的视觉感,简约而不繁琐,有谱有序,取舍精妙。有时我想象自己是作者,坐在画面前,如何能构思出这样的构图,我猜测这个过程一定很累,因为构成关系已被经营到不能再减。绘画是一种十分质朴的、用手进行的劳作。如今的艺术家很少有这样用心而富灵性的匠艺。工匠的灵魂就躲在亚麻布经纬线的缝隙里。
库茵芝的作品在俄国画家里首现装饰色彩。正真具有装饰之美的有时并非大型创作——库氏其实短小精悍的小尺寸即兴作品数量远大于大型创作。画出林间的光曙,画出海滨的礁石,画出一片团块状的云朵,画出一棵姿态扭动的树干。日后装饰色彩在俄国井喷般盛行:且不论苏联时代非主流的装饰风格与70年代后现实主义的装饰面貌,库茵芝活着,谢洛夫和弗鲁贝尔的作品已趋于装饰、象征意味。如果说谢洛夫和弗鲁贝尔的装饰性因素来源于库茵芝,其实很牵强,因为我们并不能看到源自库茵芝的直接的传承脉络,他们的造型语言来自西欧摩登主义。风格确凿来自库茵芝的是风景画家雷洛夫,他自库茵芝的工作室毕业,色块感、光线安排、几何布局,皆受自库茵芝的亲传。他恰好作于帝俄和苏联之交的《晴空万里》在苏联的宣传作用中被赋予政治象征意义。在他老师的时代,现实主义的盛行还是自觉自愿的,并没有宣传作用驱使下的政治推动力。天趣从此失落,犹如无可挽回的心情。
被剥离了生活细节、言谈举止,艺术史课题中的艺术家们,都仿佛是一枚枚照片中的脸孔,极具象征意味与符号感。其实他们都是有血有肉的,就像你的邻居,会打喷嚏,会咳嗽,急了也骂人,喝多了也吐,没有光环,不在神坛。我在俄罗斯博物馆库茵芝的大展上见过一张珍贵照片:他和化学家门捷列夫相对而坐,在下国际象棋。门捷列夫住在彼得堡大学的教学楼里,离库茵芝工作的美院很近,老哥俩或许经常聊天。在俄国的风景画史上摆一摆,必定摆出库茵芝,同时必定摆出希施金。希施金的故居距离库茵芝故居不远,瓦西里岛南端,列宾美院北边。列宾美院周围散布无数的大师旧居。库茵芝的大弟子雷洛夫的旧寓也在这里,与巡回展览画派诸名家交好的艺评家斯塔索夫的故宅也在这里。只是希施金的故居并不开放,只在门口钉着描金的大理石铭牌。他的工作室也在这里。站在楼下仰头看,不知道当年他在哪个窗扉后面抽着烟斗,虬髯蓬松。
当年希施金与库茵芝并不交好。以致希氏后来在彼得堡皇家美院(现列宾美院)没有一席之地,愤而离去。看大师们彼此交恶的时候,事件往往被解释为文化高峰不对立的现象,比方说安格尔与德拉克洛瓦、鲁迅与胡适。其实现在看他们,很多事情无非意气之争。当年希施金与库茵芝在美院各自领导一座风景工作室。库茵芝的工作室几经易手,领导者中声名赫赫的有苏联时代的莫伊谢延科、珐明,旧址就在列宾美院主楼后面,一座独立的平房,由于连带喂养写生用马的马厩,被中国留学生们称作“马房”。希施金的工作室不知道是哪一间,总之应在狭长而昏暗的走廊里,高高屋顶吊着荧然的电灯泡,因为列宾美院所有画室都如此。
画家与作品产生关系,无论经历怎样的心游的观照,经历怎样的仰观俯察、游目驰怀,画笔拿起,都只在一米的距离内,在这个距离间勾勒赋彩,凝神睇视。以致可以说,在画家的画室,作品本身愈加认清自我,哪怕以观者散漫的观看方式。悦目的表达、静观的表达、思想的表达、有意识的表达,都是画室里的事情,在画室里,悄然落脚于诗心与画意之处。心象与物象交构的天地,构造起我们的视觉的真态。画家的寓所,是作品诞生的原点,承担着每一张作品的跬积与进化,作品的归属感应是化在了绘画所在的地方。
就风景画这一绘画课题而言,从欧洲风景画史来看,田园主题,少有宏大作品。威尼斯画派的风景题材尺幅大,他们的着眼点在城市,离不开温情的生活,总是浓浓的人间情味。巴比松画派画巴黎乡下,他们的处理雕琢感尤甚,小尺寸的精妙情趣。可希施金来驾驭森林主题,真的静心屏气当成大型场景绘画来布局。如果把一棵棵树换成人物,构图线的运用并不比列宾们的大型场景简单!温情没有了,关怀世俗生活的温度没有了,同西欧相比画面的直觉感官带着一种阴冷。画画是术业有专攻的事情,造诣愈精而课题愈专。齐白石的《山水十二条屏》在保利拍卖一度被估价15亿人民币,我有时觉得他山水的开合处理像花鸟画的开合规则。如果天天思索风景课题的表现力、造型语言,往往长与此而短于彼。专攻风景的画家们人物稍显生涩,我曾见过库茵芝的肖像画,造型其实到位,只是质感、形体处理、笔法美、气质神态略微单薄,表现力差火候,跟人物画的巨匠比起来隔了几层窗户纸。希施金画林间小路,其间一双漫步的男女由波连诺夫画成。
库茵芝来自乌克兰,难怪他的作品很平静,画面充溢静谧气息。乌克兰人的性格,同俄罗斯人相比略微显静。如同很像俄语方言的乌克兰语,听起来黏黏的,音节像是比俄语低半个八度。彼得堡的口音是俄语里最好听的腔调,仿佛汉语的京片子,语音飘飘的,隐隐带出一种高冷。彼得堡是俄罗斯最华贵的城市,占据着都市第一名的位置。库茵芝的时代,华贵和首位度其实尤甚,彼时彼得堡对于欧洲而言尚有文化的向心力。俄国人总爱想象当年的文化荣光,总爱说一百年前法国人都专程跑到彼得堡看芭蕾舞。然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俄国美术史上长居彼得堡的一等一的风景画家皆不画城市。被过度谈论的四大风景画家(萨夫拉索夫、希施金、库茵芝、列维坦),其中希施金和库茵芝都是首都公民(当时的首都在彼得堡)。而希施金的着眼点在西俄罗斯的森林、郊野,库茵芝的着眼点在乌克兰的海滨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的广袤腹地。其实何止彼得堡画家,俄国风景画的大匠师们对城市题材均少有涉猎。英年早逝的天才画家瓦西里耶夫,他只活了短短的二十三年,恰似他的老师萨夫拉索夫,他的着眼点在以莫斯科郊区为圆心画出长长半径范围内的田园。俄罗斯博物馆和特列恰科夫画廊皆有瓦西里耶夫独立展厅,一张张作品连起来看,仿佛自然野景的集中展现,一种很奇异的视觉体验。我曾写过印象派城市风景课题的论文,印象派画家的生长环境和童年生活状态在资料堆里慢慢浮现,画家生长环境与作品的联系,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法国印象派诸大师皆在都市长大,不难解释为什么他们对城市主题永远充满热情。俄国一等一的风景画大师童年生活大多远离都市环境。希施金生长在鞑靼斯坦地区大镇叶布加拉,如今叶布加拉是俄联邦政府着力发展的经济区,在沙皇年代,是半原生态环境的镇子。库茵芝生长在乌克兰东南城市马里乌波尔郊区(这座城市苏联时期曾以普罗政治家日丹诺夫的姓氏命名。不久前乌克兰政府武装与民兵在此较劲,使这个城市的名字一度成新闻热点)。恰恰是长在巴黎的俄国侨民谢洛夫,爱画贵妇、绅士。
库茵芝和希施金住在首都,比邻市中心涅瓦大街的灯红酒绿,比邻纸醉金迷的闹市。他们的居所都在瓦西里岛最南端,隔涅瓦河与涅瓦大街相望。在他们生活的时代,瓦西里岛大部分区域处在城市最外围,是平民入葬的墓地所在。他们的房子的位置在繁华与冷清之间。当年被果戈里无限奖饰的涅瓦大街,被普希金极度称誉的彼得堡老城中心,对于他们,其实淡然。2007年俄罗斯博物馆举办库茵芝大展,从各地博物馆搜罗借展作品,我只见到他早期所绘几张带有教堂的街景。他盯住乌克兰郊野,列宾说他“光线有诗性”。经年的执着已成情愫,生命原点的记忆写在画布上,有种生活的烂熟之美。
俄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库茵芝的画中有诗意。诗意在各异的美学关注点和立场上,常被异化。画面美的营造,背后是抒情因素作为驱动力。库茵芝作品的美学元素,在构建的拟象中,抒情性的驱动力在此间跳跃、闪现,具有诗学的意趣和审美价值点。我们可以尝试着走进俄罗斯人诗意化的概念,这概念在中国人的视角中,模糊不清,“诗意”二字于中国文化语境,无比重要,无孔不入地渗透在文艺的各种层面。移入西方语境,诗意概念自然而然被拉伸、延长,似乎扭曲。现今俄国的文学气质与十九世纪相差极大。而有着经典文学情结的我们依旧在寻找,在感悟。这后面有一种内心审美经历的文化认同。好像进入到艺术心理学中的普遍套路,艺术性和艺术价值的感知,总是审美经历、审美认同的移情作用。好比中国人总在月亮中找到思乡的情趣。这片明亮的月光也曾在库茵芝的笔下出现,描绘的地点,恰恰是库茵芝的故乡——乌克兰。可它不过是一种巧合,欧洲文化的解读点上,月亮这个文化符号背后并没有思乡的含义,而诗意的文化立足点上,也没有中国人那种陶然忘形的表情。苏联时代乌克兰电影大师杜甫仁科的《土地》讲述主人翁瓦西里在第一辆拖拉机开进村庄之后在月夜下跳舞,花园中树影婆娑,银色的月光洒在黯淡的土地上,又是乌克兰艺术家,又是月光,又是巧合。俄国诗学没有“意境”的概念,这概念对于俄国文艺者,是一个隔膜而奇异的观念。相类似的,他们的诗学中有“象”的概念,这个字可以理解成形象,可以是视觉感,可以是画面感。俄国的田园诗人们在这个概念上悉心经营,使其形成具有巨大表现力的语言艺术手法。叶赛宁的作品是这一手法最好的范本,也是他的作品作为语言艺术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就像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语音修辞所具有的表现力,八十年前的两位年轻人,在诗学语境里,如今依然是抹不掉光彩的人物。影评家普洛夫金说苏联战争电影开炮前的平静场面总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库茵芝的静谧,对于承载与艺术品沟通交际的艺术准客体,同样是一种升华。艺术形式的思索是载体和转换器。
在瓦西里岛,在库茵芝和希施金故居周围,旧式的墙面斑驳,椴树苍老,空旷街道散落人的背影。诞生诗的地方往往不是诗。在艺术品诞生的地方,看到柏油路上的枯黄的叶子凝成灰色。不知为什么,那灰色的感觉在记忆里非常风景画,还有它离开诞生地陈列在博物馆的视觉经验。一切艺术倾向于诗,诗的艺术从回到原点开始。片段的考量带着我们接近风景画本质的原点。但这片段的组合对于每个观者是不一样的,每个人有自己的组合经验,架构起绘画中各自不同的契机。(作者:于霄牧)

于霄牧简介
于霄牧,油画家、散文作家。1989年生于山东济南。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油画硕士、艺术学博士。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年美术家协会理事。
出版文学专著《圣彼得堡·雪》(中国戏剧出版社)等。举办个人展览“艺心·家学——于平、于霄牧父子作品展(烟台站、威海站、日照站)”、“彼得的隅落——于霄牧油画作品展”、“日常的边界——于霄牧风景绘画展”等。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艺术类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文章作者的个人观点,与本站无关。其原创性、真实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原创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自行核实相关内容。文章投诉邮箱:anhduc.ph@yahoo.com